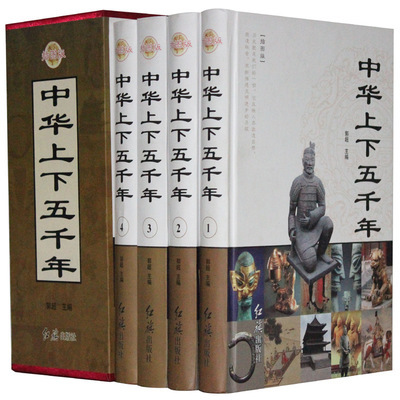中国到了给企业树碑立传的时候了吗?企业家为什么需要被记录和阅读?企业史写作有哪些原则?哪些企业史值得期待?
文 | 本刊记者 丁伟
想像——30年后,中国商业的历史图书馆里,哪些公司案例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哪些企业家成为“典型场景下的典型人物”?会是联想、海尔、华为、阿里巴巴吗?会是《蒙牛内幕》、《联想局》、《道路与梦想》、《激荡30年》吗?
未来很难预设,就像历史不能假设。中国“企业史”命题的现状是,“中国没有德鲁克那样的人来总结企业家的管理实践,一本《联想为什么》、一本《海尔中国造》,虽然和《公司的概念》或《蓝血十杰》没法比,但照样畅销无比。”几年前,一篇书评如是感慨。
30年来,中国商业图书不断更新,中国企业家也从西方企业史的读者成了本土企业史的主人公。但中国“企业史”连本身的定义、类型、游戏规则都没解决呢就开始浮躁了——几位企业家及写作者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一致认为。
“中国有那么多研究别人的书,中国人读了那么多别人是怎样干的书,但是中国太缺乏研究自己的书,研究自己应该怎样干的书。”1997年,陈惠湘的《联想为什么》开了中国企业原创与实证性研究之先河,是当年的畅销书(包括《日子》、《老照片》、《黄金时代》等)。但十年过去,陈惠湘有些失望,“现在‘广告书’太多,置身历史背景下,客观地数企业的脚印,像《联想风云》这样的路数远远不够。”
“虽然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奇迹,但对于中国的商业,居然缺乏完整的案例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2004年,吴晓波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深受刺激,于是历时4年写了《激荡30年》。他的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还跟中信出版社、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组织了“公司史创作高级研修班”,试图系统完成“中国百家标杆企业工程”。
企业史也涉及到全球话语权的问题,《中国企业家》杂志自1985年创刊以来就在记录历史,但主编牛文文并不乐观:“中国有全世界羡慕的经济,但是没有全世界羡慕的企业,最严重的是没有全世界羡慕的媒体(包括出版)。什么阻碍了中国人向世界传播商业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全球通用语言、一个话语体系来讲述‘中国梦’?”
或许,我们可以回到根本,将企业家史简略概括为“3个W和1个How”。
1.为什么(Why)需要企业史?
“我们只以逻辑来判断,在伟大的商业年代一定会有伟大的商业作品诞生。”吴晓波说,“这就存在一种必然性——有一个人找对了题材,而且那个公司正好到了叙述的时间点。”
“时候绝对到了!”陈惠湘说,企业史既要“温故”,总结过去,而“知新”是目的,指导现在的企业实践。而且“现在不做以后做更难,当事人都不在了”,趁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都还活跃在商界,整理他们的资料,做当下的真实记录,对未来肯定很有意义。
中信出版社近些年做商业图书的引进和本土作品的组织颇成规模,其社长王斌说:“我们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时点,应该有一大群真正高水平的作家队伍,真正找到一些有研究价值和案例的企业,做一些真正的梳理和规划。”
2.写什么(What)是一种价值观
《光荣与梦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一代媒体人。很多作品中都闪烁着“很多年之后……”的句子,王石干脆把他的自传叫《道路与梦想》——据说他刚开始苦思写不好,后来有人点拨,“你要拉开,把自己放到深圳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王石茅塞顿开。
也就是说,企业史应该是一个企业(家)的通史,还是通过他反映一个时代?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呈现?这目前没有定论,而且存在一定的争议。要知道,在西方常规的商业写作就是具体的公司案例和企业家传记,如《惠普之道》、《沃森父子与IBM王朝》、《艾科卡自传》、《杰克·韦尔奇自传》等。但中国更多的是营销、励志、成功发家史,“而且我们的读者决定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在短期内没办法解决”。
吴晓波认为,“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但写完《激荡30年》后,他分明有一种无力感——编年体主线往往是政治逻辑,《光荣与梦想》的脉络就是美国总统,《激荡30年》汇集了诸多商业细节,却只是匆忙素描了历史。
胡泳说,现在写企业的书与其说是史,严格地来说更多是一种记录。陈惠湘说,科学是中国的弱项,历史往往为我所用,能够记录事实就很宝贵。

“最重要的两件事儿是历史和哲学。”冯仑说,“历史让你登高望远,哲学让你看破、看穿、看透。”他师承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画卷——冯仑很想再写一本书,就叫《历史现场》。
3.怎么写(How)是一种方法论
强调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文字之美的作者有时会感到读者的反差。“中国人还不习惯写企业的方式,喜欢看《蒙牛内幕》、励志的东西,能够把里面的那些黑体字拿来就学。”吴晓波很推崇凌志军的《联想风云》(“迄今国内写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其考据之详尽、论述之细微、格局之庞大,没有别的作品比得上”),但销售并不好——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可能比“XX内幕”要大很多。
“这有大道方面的问题,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余秋雨在冯仑的新书发售会上建议说,“企业家不要把自己某一些经营的策略当作终极精神……要放下你在企业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写作时候非常重要的姿态;第二,作品带有一些文字气息,注重细节;第三,还要注意不同的节奏,不要用同一种语言从头讲到尾,这样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厌恶。”
但无论由作家还是企业家写,“历史的写手得是有意味的表达,应该来自企业、高于企业。”牛文文说,“中国的商业史、企业史,尤其是思想史,应该有‘大历史’的感觉,应该放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中国商业发展的横纵坐标系上定位来写。中国30年的商业进步如果能抓住其中一点,把这一点写透就能传承历史。”
4.底线(Where):不独立,毋宁死!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史,更缺乏独立的企业史写作者。”2003年,迟宇宙写了《海信史》,也开始了对联想的采访、考察,但三年过后,他想“确立企业史写作的行业标准”的雄心遭到了打击——联想决定,《联想局》给《联想风云》“让路”。
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冲突,企业史的创作底线值得反思:如何既获得企业的配合,又能保持写作独立。“一个写作者的创造力没得到尊重,相反有种被侮辱的感觉……”回头看,迟宇宙说“到今天我也没觉得是一个什么事儿”,但承认《联想局》有些地方需要修订,比如柳传志的国际化视角,“单写的某个人我都很满意,作为整体的结构我很不满意”。
当然,最后还可以加一个“P”:不畅销(Popular),毋宁死!(西方有个说法,“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如果一本企业史能有七分真实,卖它十万册,那就接近上品了。
总之,企业史这个行当,牵连到太多商业本身的问题。冯仑精辟地说,企业管理就像爱情,到处都是爱情教材,却到处都是不幸情史,“出一本书并不能保证能办一批好企业,垮一批企业也不能保证出一本好书,互相激励使得企业管理和出书这两个市场都繁荣。”
企业史最终是“把企业写厚、让读者读薄”,陈惠湘说,像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刘永行、任正非的自传都非常值得期待,“但王石的不期待了,牛根生的更不。”王冉猜想,如果柳传志真的写一本自传,“它的畅销程度应该超过奶酪,超过大象,超过蓝海,超过执行力,也超过韦尔奇。”
《激荡30年》跟这个时代一样,都是不成熟的作品
企业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写或者会被写成什么样
口述 | 吴晓波
“本书介绍了美国人最擅长的活动——成立和创建新的企业。”泰德罗在《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开篇明义地写道。这是一种多么自信而让人羡慕的描述方式,我也渴望用这样的语气来讲述中国企业家们的传奇。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商业到最后是冷血的,最终看到的是人性的挣扎。我别的不懂(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做了13年的经济记者),人可能专业一点好,研究一个文人、一个宗教还不如研究一个企业家,类别性比较强。
国内财经书可以分成几大类别,一类就是管理,这一类中国没有创造能力,因为没有管理思想;第二类是理财;还有一类是励志,像《谁动了我的奶酪》,我都把它称之为“洗脑”;第四类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企业史。十年来我认为有几本书是有标志意义的——《联想为什么》、《海尔中国造》、《联想风云》。
从企业家传记来讲,真正未来有价值的应该是自传。过去30年里有影响力的人,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鲁冠球都还没有作品出来。他们是否有被写的需要?我接触帮助过很多企业家出书,我认为他们是不清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写或者会被写成什么样,有的是好奇,有的是虚荣,有的则是商业或者个人名利的需要。但像柳传志、鲁冠球,有极少数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有历史感,他会想自己在历史上是怎样的。
商业写作有三种状态:第一种是独立的状态;第二种是定制,用于公司宣传(比如20周年庆典);第三种是扭曲的状态,有人出钱“御用”你。前两部分都可以,第一部分是我们要提倡的,第二部分是被忍受的,第三部分一定是不可触碰的。
蓝狮子已经完成了娃哈哈、万科、科龙、吉利、苏宁等多本公司成长史或断代史创作,到2008年底,我们将达20多本(还会有李宁、深圳、张骞、中国百年商业史[1870~1970]等)。再过两年会初见成效,三年到五年后形成规模,之后就会有标榜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至于它是否高级或者有价值,那是这群人的能力问题。
《大败局》是失败案例、公司通史,《激荡30年》则是编年体、没有主角的草民史,写完以后我怅然若失,序言的那个标题好像一个预言:“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我只能说,这本书跟这个时代一样,都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编年体很难控制,你会迷失于细节的丛林,30年30匹马你怎么骑得过来呢?而且越到眼前越看不清楚,历史学家都是远视眼,我对2006年、2007年写得就不是很满意。
我们也逐渐归结出一些心得,并将之作为创作和出版准则:一部优秀的公司史必须有自己的坐标系;尽量走进公司的档案室;没有公共研究价值的公司隐私不应该被暴露;不要试图用一本书去“终结”某家公司;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大多数的公司史都会速朽,包括我自己的能够超过3年就合格了,超过5年就了不起了。
更重要的是,一定需要口述实录!这是件又花钱又花时间的事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柳传志的口述谁来跟他访谈?唐德刚式的人太少了(编者注:唐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创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曾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做口述历史——这也是企业史很重要的方式)。
当代史真的很好玩。奥本海默基金的创始人利维写了一本《华尔街精神》,他说自己是惟一有资格研究华尔街精神状态(贪婪)的人——他在大学期间“变态心理学”得了A+。哈哈!我不认为自己写企业史有资格,我估计会被抛弃,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我之所以做《激荡三十年》,是相信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再往前拓进的话就不是我的使命,我也做不到,那需要另外一个专业的人来做。
我很喜欢的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回忆录《旁观者》中说:“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我也是。
企业史终将会回到正常状态
当企业家仍然是“毛”而不是“皮”的时候,企业史自然不能幸免
口述 | 胡泳
我个人觉得中国第一本关注企业的书就是《联想为什么》,以著名企业、著名企业家为题材,但严格来说它也不是企业史。最明显的,里面完全没有提“倪柳之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给企业做史,这些重大的东西不能遗漏。
接下来就跟我有关系,我和颜建军合写了《海尔中国造》,这应该是一部比较标准的企业史:企业从小到大分成若干层面,总结一些秘诀、规律。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商业图书的崛起”的文章,当时这一块基本没成气候,之后值得写的企业就多了——它们已经有二三十年的积累,出版社也发现了读者对于本土企业书的需求,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市场。
早期艾柯卡的传记我特别有印象,一个人用那样一种口气说那样一种经历,挺令人震撼的。吉尔德热情讴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之魂》也感染了我,在当时的社会中你根本不知道一个企业家的作用在哪里——80年代我们根本不崇拜企业家,文化启蒙里没有商业。
最容易想到、国内外都比较流行的企业史,就是记者长期跟踪一个企业,通过积累和对一把手的访谈写成一本书,比如说惠普、通用汽车,每家知名的企业都会有一个长期报道的记者。但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追求,德鲁克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他实际上是把公司作为一个样本、社会的一个组织来剖析,这里面有些东西成为管理学的基石。我去硅谷参观Google办公室时很有感触,这就是德鲁克1962年预测的未来“新社会”嘛!
《海尔中国造》其实就是这种模式。我写的不完全是企业的内部,更愿意去看企业在社会的链条中做了什么,企业里面活生生的人。
十年前我写海尔的时候,和很多“朝圣者”一样,抱着强烈的出发点: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成功秘诀,试图从战略、营销、人力资源、信息化等总结出一系列的规律。但是我如果再写海尔,一定不是这个写法——我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必然性,今天不光我作为写作者会发生变化,张瑞敏自己也会发生变化,上次他跟我说,“海尔现在处于高原期,怎么突破高原期达到新的高度”,那时候再去观察海尔,一定要用另外的观点。
在某种角度上,我是比较幸运的,有这么完美的写作对象。但我也看到企业史写作的复杂、冲突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对它的折射。有些作品写完了,就失去了价值,几乎速朽——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还不到总结的时候,或者那个企业发展的暗礁还没呈现出来;而有的企业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历史价值,有些企业家不能够成为某种符号。
有些问题不是单纯的企业史自身就能解决的。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仍然不独立,政和商是不分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企业家仍然是“毛”而不是“皮”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指望他在社会舞台上有多大的发言权;企业史自然不能幸免。
我们说“文以载道”,一篇好文章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义理就是你对这个企业背后的逻辑很清楚,比如现在海尔最大的困惑就是怎么成为一个全球运营的卓越绩效企业;考据就是尽可能地搜集各种客观的资料,这其实是记者采访的扎实度;辞章就是你最终写的东西要有可读性,如果辞不达意,不能给读者一种愉悦的体验,我觉得基本上是失职的。
最终,我觉得企业或者企业家的开放心态会决定企业史的好坏程度。西方每家公司都有优秀的作品,再过些年,中国的企业史会回到正常状态——这根本上还是依赖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什么时候他变成“皮”的一部分了,对写作者来说就更能够写出好作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