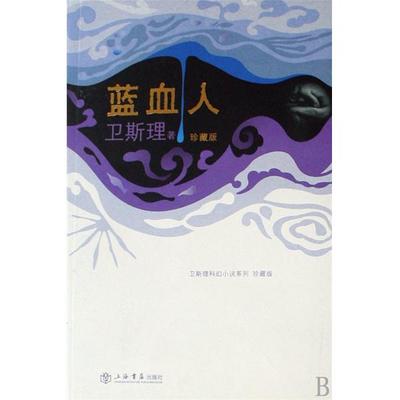IBM软件集团解决三大转型矛盾的内幕体验
文/本刊记者 程苓峰
编辑/李岷
IBM之外,世界商业史上还没有第二家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从濒死边缘回复生机。上世纪90年代初,1990-1993年IBM累计亏损168亿美元,甲骨文CEO埃里森对此戏谑讽刺,微软创始人盖茨更预言:IBM将在几年内倒闭!然而10年之后,IBM居然回转生机,并且成功转型。10年前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硬件,今天,软件和服务两个新业务贡献了七成以上的营收和利润。它在全球软件业的份额仅次于微软,IT服务则稳居第一。在刚过去的2005年,埃里森、鲍尔默、盖茨三个人都先后宣称:IBM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郭士纳在2002年退休时总结说:“IBM软件的发展历程,就是整个公司在过去10年起死回生扭转乾坤过程中的一个精彩的缩影。”IBM软件集团在1995年成立,正是IBM缩减旧业务、开辟新战线的首要尝试。这一年也恰逢郭士纳大力改革机构、同公司分部和守旧势力激烈作战的时刻。而软件集团在头两年成功做出两次大型并购,也为日后以并购为主要转型手段奠定了基调。正由于软件集团的披荆斩棘,IBM另一业务主体服务集团得以在两年后顺势独立。
2005年正值IBM软件集团成立十周年。《中国企业家》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对包括IBM软件集团执行官米尔斯、高级副总裁杜佩克、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火昆在内的10位IBM高层做了详实采访。

当我们回顾IBM软件集团十年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有三大基本矛盾(或曰命题)交织在IBM的转型年代。第一,在IBM整体管理架构突变的背景下,新生的IBM软件如何在总部与地区不同势力的冲撞中站稳脚跟、争取资源;第二,作为弱势业务,IBM软件如何突破传统业务有意无意的打压、又同时与之实现良性合作;第三,在并购中如何消解对方猜忌,有效地把外来力量整合进IBM母体。
围绕着这三个矛盾,一时之间,在IBM这个蓝色巨人体内,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和“内战”被掀起。是被我们称为“蓝血‘内战’”。
事实上,任何一个转型中的组织、任何一个意欲催生和扶植新业务的公司,可能都会面临这三大命题的拷问,这三大矛盾解决得好,组织就有可能走向新生与和谐,反之,也许就会像我们看到的太多转型失败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读者将看到IBM各路经理人在企业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修正原有的利益期望、调整自身行为、作出新的选择。他们的互不理解、交锋、冲撞以及妥协,正是转型期几大矛盾最鲜活的体现。
故事一:
“我会被换掉吗?”
为突破阻力发展软件,郭士纳在1995年任命了重臣汤普森。接下来的五年里,IBM全球20多个大区总经理只有两个在撤换大潮中幸免
周伟火昆在IBM一呆37年,就像一块活化石。1968年,他在香港加入IBM,后来转战台湾、澳大利亚、及南亚太区,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后期,他目睹了IBM在大型机时代的辉煌和在PC业的崛起,也经历了90年代初的衰败,以及接下来的10年逆转。1993年郭士纳空降前后,正是IBM史上最落魄和动荡的时候,企业上下正在大幅裁员和重置结构。不知道那时年近50的周伟火昆有没有想过离开,但他最终选择在1995年转任大中华区。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接下来5年,周伟火昆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思想改变。他险些没能挺过这场考验。
周从澳大利亚调任北京的1995年7月,正是郭士纳接连在IBM推动几件“大事”的时候。年初,郭士纳组建软件集团——这是IBM历史上第一次把一项业务独立运营——继而斥资35亿收购Lotus,表明进军软件的决心。年中,郭士纳打破地域分割,把公司按行业和业务线分成12个集团,并以此展开预算和人事安排。这意味着,IBM传统的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转变为矩阵形。以往把各个地区视为自己独立王国的区域负责人,要开始受到业务和行业领导人的制衡。
那正是郭士纳同旧官僚体制作战最激烈的时刻。反对者指责他:“这绝对行不通!”“你会毁了公司!”欧洲区总负责人甚至拦截了由郭士纳办公室向外发送的信息,欧洲区员工竟然收不到他们的董事长发给全世界员工的电子邮件。郭士纳发现后的第二天,欧洲区总裁被叫到总部问话,他说:“这些信息对我的员工不适合”。而郭士纳回应说:“你并没有什么员工,所有员工都属于IBM。”几个月后,这位欧洲区总裁离职。
“我跟总部意见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周伟火昆承认。他并没有把刚刚独立的软件业务当作首要任务,而是更关注所熟悉的PC。当时,软件仍作为硬件的附属,用户没有为软件付费的习惯。在澳大利亚时,周伟火昆就对软件研发总是超出预算印象深刻。所以他拒绝了软件部在中国区增加20名员工的要求,他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还要加人?”这引来了软件集团执行官及IBM高级副总裁汤普森的干预,“为什么你不准我们加人?”他质问周伟火昆。“软件哪里有什么生意做?”周伟火昆不服气地回答。
为此,周伟火昆承受着极大的风险。要知道郭士纳打破地域分割的原因,就是要让软件集团这样的业务部门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
1997年1月,周伟火昆作为大中华区CEO参加IBM全球高级领导会议。这在IBM是规格最高、由300位地区和行业总经理参加的年度盛会。“副总裁都坐台上,我们在下面围成圆桌。”周伟火昆回忆说。有人举手问:“大家觉得我们在中国做得怎么样?”“很好,成长50%。”负责亚太区的老板说。“Henry(周伟火昆英文名)的队伍很厉害,PC和服务器卖得很好。”硬件部门的老板接口过去。这时坐在台上的汤普森出声了,“我认为软件在中国是完全失败的!”这句赤裸裸的指责让周伟火昆的欢喜荡然无存。
就是在这一刻,周伟火昆开始警醒。当时的情形是,从1995年开始,IBM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总经理被大量撤换,那位敢于跟郭士纳顶撞的欧洲区总裁只是其中之一。及至2000年,除了大中华区和日本,全球20几个大区的总经理全部被撤换。
周伟火昆开始重新构想。他给自己的定位调整为:成为最了解中国市场的人,保证全球战略在地区的执行。接下来拟定1997年战略中,周伟火昆把软件投入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二年就把当时负责Unix服务器的“重臣”宋家瑜调到软件集团。“我自己的思想做了很大的改变,如没有这个改变,就不会把宋家瑜这么好的人放去做软件。”周伟火昆说。等到2002年退休的时候,汤普森对他说:“你已经做了很重大的改变,再不是单纯以硬件为目标的领导。”周伟火昆应该明白,能否做出这样的转变对他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但这确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对于那些1995年之前已经在地区总经理位置上做了5年、10年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支持新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做事情的老方法。不换这些人,就不能执行新的计划。”周伟火昆说。他在1995年才刚刚接手中国区,而那时候IBM在中国还很小、没有实力,所以不得不依靠总部派来的人。“这样就慢慢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开、愿意接受总部的框架,”周伟火昆感到庆幸,“那时我们才500人,要是像现在6000人,改变起来就非常困难。没有历史包袱,就越容易改变。”
这正是郭士纳在1995年决定独立运作软件集团之初就担心的问题。当时软件在IBM大型机、硬盘、网络设备、PC、服务诸业务里是最小的。而且“传统部门经常会抵制新部门……出现激烈矛盾是很普遍的现象。”郭士纳说。虽然1995年IBM就开始执行新的行业结构战略,但正如后来所呈现,地区负责人仍固守老体制,至少在3年后结构改变才被完全接受。
所以汤普森被任命为软件集团的执行官。那之前,汤普森担任过加拿大区总经理和服务器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被誉为IBM的心脏,而他自己被称为“IBM中最有思想和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同时做过地区总经理和业务负责人,所以他知道如何有效地把总部和地区协作的模式定下来。”周伟火昆说,“成立新部门,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最棒的领导派过去,表明决心。汤普森一摆出来就代表重量级,很严肃,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玩玩而已。”在IBM工作了23年的大中华区副总裁宋家瑜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当时软件只是配角,但汤普森的地位让人感到,软件在IBM不应该只是二等公民。”所以汤普森的出场吸引到了IBM内部一群有能力的人追随。
汤普森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果断的魄力给宋家瑜很深的印象,他清晰记得1998年向总部要求格外经费的情景。那时中国区准备花大力气培养独立合作伙伴,但此类计划在短期内难以见效,是一项长远投资,而中国区的预算早已用完。宋家瑜直接向汤普森求助,在几分钟通话之后,汤普森当即批下了500万美元专供经费。“果断、迅速,他有能让你愿意跟他打天下的能力。”宋家瑜说。
郭士纳不遗余力地支持汤普森。他批准了汤普森在软件集团成立才几个月就对Lotus高达35亿美元的并购。之后,作为举足轻重的业界领袖、Lotus老板曼兹想要取代汤普森。当时Lotus的规模要大于自身,而曼兹如果离去对军心的动摇,很可能导致IBM软件独立后第一次并购的失败。但郭士纳仍然拒绝了曼兹,汤普森借扶植曼兹两位副手而稳住了局面。
后来,汤普森被尊为“IBM软件之父”,2000年晋升为副董事长——这是董事会里惟一的副董事长。2002年郭士纳退休、彭明盛接任的时候,汤普森也随之离任。如果这位“影响力仅次于郭士纳”的人物留在董事会,彭明盛可能会放不开手脚。
在郭士纳支持下,汤普森在1995年中止了在操作系统上跟微软的“战争”,这引发了一直在这个战场上跟微软竞争的员工的怨恨。1997年,汤普森又退出了亏损巨大的应用软件市场,并和SAP、仁科等企业“化敌为友”。如此,IBM得以积聚力量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之间的夹层里大展拳脚。这个由数据库、系统管理等软件组成的中间件领域,在当时还不被业界重视,但到了2002年,它的市场规模达780亿美元,2006年预计攀升到1150亿。
故事二:
“我犯了什么错?”
宋家瑜后来明白了老板的布阵心机:坐在桌子两边的人彼此有矛盾,你就把他们对调一下,换个立场看问题。但“对调”仅仅是个开始
1997年的12月26日,刚过完圣诞节,总管IBM大中华区Unix服务器业务的宋家瑜心情不错。因为这两年产品卖得很好,IBM“深蓝”电脑打败国际象棋大师的品牌宣传效应异常强大,IBM服务器有“横扫天下”的威望。再过几天新财年就开始了,宋家瑜觉得完成预算没有一点问题。
周炜火昆跟他关系很近。宋家瑜早年在台湾做业务代表的时候,周伟火昆是台湾地区总经理。那个时候宋家瑜经常挨骂。在IBM二三十年的历练,两个人身上都自然流露着IBM的“蓝色”特征:气质稳重而大气,谦逊有礼。但是,他们绝不是仅有这些仁者风范而忽略了其它素质:谋略、机巧、深知人性弱点。
这天早上被叫到董事长办公室之前,没有丝毫迹象,就当被周炜火昆告知“你明年去接软件集团”的时候,宋家瑜几乎愣在那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他心里嘀咕,但没有说出来。周炜火昆是在征询他的意见:你可以拒绝,不过请认真考虑。但这已不是郭士纳来之前的那个IBM了,“尊重个人”的理念不再是拒绝老板、我行我素的护身符,“既然是大局的需要,那就最好遵从。”宋家瑜说。
那时候软件业务饱受怀疑:“一个最小的部门,到底行不行?”宋家瑜说。相反,那几年IBM服务器卖得好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软件独立之后,硬件摆脱了一定要捆绑IBM自有软件的束缚,转而向微软、甲骨文等开放,“谁的软件好,客户需要谁,我就卖谁的软件!”1997年,宋家瑜在大中华区卖出了41台最昂贵的6000型服务器,其中有40台都是搭配甲骨文和Informix数据库,只有1台是捆绑IBM自己的数据库。原因很简单。在IBM,软件一直是硬件附庸,没有主打自己的品牌,又刚独立不久,产品兼容性跟业内的领先者有差距。
负责服务器的宋家瑜和负责软件的苏珊在当时有一段经典对话。苏珊向宋家瑜抱怨:“亲爱的兄弟,你可是我最差劲的盟军,你为什么对IBM自家的软件支持这么少!”宋家瑜说:“亲爱的姐姐,我的工作手册上第一条就是要求我卖好服务器,并没有叫我卖好IBM的所有东西啊!”
但当软件集团也秉承相同的开放原则支持其它厂商的硬件时,却招到了硬件部门强烈的反击。财大气粗的硬件集团一直以正宗嫡系自居,它们依然认为软件免费附送是天经地义,而如果支持别人就是背叛!1994年到1997年,“几乎总会一周爆发一次危机”(郭士纳语)。那些愤怒的人会跳起来大叫:“你们软件在搞什么!”在总部,抗议人群甚至会到郭士纳的办公室,对“离经叛道严厉谴责”。郭士纳会委婉地劝导:“把他们看作是你们产品的一条配送渠道吧,你们的竞争对手正在这样做。”
从服务器部门调到软件部门,就像是从荣耀非凡的嫡系转入了冷清受气的偏房。所以宋家瑜几乎把周炜火昆的任命下意识地当作对自己犯错的惩罚!软件集团Lotus产品总经理刘秋美回忆起当时还禁不住放声大笑,“那时候David(宋家瑜英文名)在硬件部天天跟我们吵架,我们可吵不过他。可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我们的老板。”这下怎么办,宋家瑜该带着刘秋美们去跟昨天还和自己同一战壕的同事开吵了吗?
就在作为软件负责人第一次来到集团会议的桌子旁的时候,宋家瑜忽然意识到了老板们的真实动机。“以前你是坐在桌子那边的,现在换到了这边。现在你要用这一边的立场看问题,但你对那一边的想法又再熟悉不过了。”他说:“所以你知道两边的冲突在哪里,利益的交集在哪里。”
宋家瑜说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自己首先要帮自己,别人才会帮你。他找到了刺激硬件集团去主动推销自家软件的方法。他告诉硬件部门:你不要以为捆绑别人的软件对你自己没有坏处,要知道,如果客户选择了甲骨文数据库,那么甲骨文就对客户有了关键的影响力,客户下一次再选择硬件,就会更多的去征求甲骨文的意见。很明显,硬件跟客户只是“一锤子买卖”,而软件服务要跟客户长期接触、对客户内部更了解,因此有更大的影响力。硬件部门开始认识到:软件将会在客户关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长远而言,支持IBM软件就是支持自己!
来自硬件部门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宋家瑜对这些旧日的同事非常熟悉,“我们不会像陌生人,一上来就吵,而可以心平气和地交谈。”在服务器业务部门的三年宋家瑜成绩显著,积累下来的威信成为跟硬件部门沟通和合作的垫脚石。自从郭士纳任命汤普森领军软件集团之初,这个思路就一脉相承:汤普森正是硬件核心——服务器集团的旧日功臣。
“宋家瑜的挑战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把他是IBM一份子变成他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如果他说其它部门的人都绑手绑脚、周伟火昆对我完全没有附加值,那就是失败。”密切关注宋家瑜的周伟火昆说,“这是他的挑战,也是我的挑战。要是我听到有销售说跟其它软件公司合作比跟宋家瑜合作更好,那就要通过两种方法来解决,一是去调查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是要枪毙讲话的人,要他闭嘴。”
摆平与硬件部门的关系之后,软件业务内部的矛盾开始凸现。头几年,软件继承硬件的销售传统,由销售代表与客户全权接洽。硬件销售比较简单,搞清楚内存、速度等几样指标数据就可以谈判,机器试运行之后就交货。但软件销售复杂得多,不单是软件的性能很难用一般语言表达,而且与客户签约之后还有长期的后续服务。这样,销售过程需要后端的产品和研发人员的介入。
但IBM的客户代表在传统上形成了“非常强势”的地位,对外代表IBM,对内则代表客户,在两者间形成一道防火墙。“他们的心态,就是家里的人都不要来,最好经理都不要来烦我。所有事情都由我搞定,反正年底把业绩数字交出来就好。”干销售起家的宋家瑜对此深有感触。而如果无法应付客户,也是由销售代表来指定在什么时候、要什么人出场提供帮助,后台的支持人员,包括宋家瑜,全都成了助理。
壁垒必须打破。起初,是研发人员被“赶出”实验室,穿起西装、打上领带去拜访客户,这在销售代表和客户的联系之外重建了一条纽带。能亲自听到客户的声音,研发不会再被销售牵着鼻子走。有时候,像宋家瑜这样的区域最高管理者也会绕过销售,冲到一线跟客户建立直接的关系。“这一层其实非常难以冲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宋家瑜说,“即使是我打下来的单子,归到你销售的头上也无所谓。在大公司里做事,最忌讳里子和面子都要。我就只要里子,不要面子。”
等客户对公司内销售、产品、研发都有了解之后,转变体制就水到渠成。后来,IBM软件销售的整个过程从接触客户、分析需求到最后签约有好几个步骤,销售代表在第一个步骤负责接洽客户,把需求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接下来就引入后台的研发、产品等支持人员,共同为客户服务。如此安排就为各个岗位的职员了解其它岗位提供了便利。
逐渐,职位的轮换成为了IBM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常态。资深的员工可以申请在研发、产品、市场、销售各个职位间转换,比如现任大中华区策略与合作伙伴总经理蔡世民,中国区软件总经理林鸿昱都是如此。跟在会议桌的两边都坐过的宋家瑜一样,有不同的经验,他们就能更清晰地洞察全局。员工也可以在不同的区域轮换。在亚太、香港、大陆都呆过的大中华区Websphere总经理李永财就说:“现在我要亚太的人配合,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就行了。否则还要走程序,很麻烦。”这种非正式的纽带促成了资源的融通与关系的和谐。
故事三:
“我不能跟着他们
一起去声讨IBM”
陈致平成了柔道高手,一面把收购方IBM来的力量小心传递给被收购方,一面把后者的不解与压力化解掉。他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求得“平衡”
陈致平是一个快乐的中年人。他生在台湾,在美国软件公司Rational负责北亚区销售,主要工作的地区是在中国,也常去韩国。他是个接受多文化熏陶的人。对外他冲在第一线跟不同的企业打交道,对内跟公司研发人员保持沟通。对上跟美国老板用英语汇报,对下用北京腔交代任务,然后回到台湾的家中用闽南语跟老爸问好。你可以把这种人叫做“八面玲珑”,这就是他的工作。
2001年底的一天,陈致平被通知到公司总部参加培训,课程叫做“如何应对转变”。这种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很常见。不过陈致平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他正处在一场交战的前夕,他所接受的正是如何调整心态和如何“格斗”制胜的训练。
他也不知道,这就是IBM的传统。6年前郭士纳在做第一场并购时就说:“在正式并购战打响第一枪之前,必须在争取对方员工方面打个胜仗。”那时IBM并购Lotus,后者是一种不同于IBM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文化。就在郭士纳给Lotus的CEO打完第一个电话要求并购的一分钟之内,他精心准备的致Lotus员工的信就出现在网上,连同IBM的所有信息。于是,Lotus员工从他们熟悉的渠道认识了IBM,“两种截然对立的公司文化首次相遇了”。
郭士纳之所以如此小心谨慎地关注并购,是因为如果要想在高速发展的新产业生存,就必须快速并购,要想搭建开放全面的中间件平台,就必须大量并购。把并购称为“战争”,因为高科技行业的并购只有20%成功,最主要的失败原因则是文化冲突。正如后来在很多国家,IBM的人都被Lotus的技术人员堵在了门外。郭士纳不愿看到这样,他本来就打算借助外来力量来帮助激活IBM的老文化。
整合和碰撞是被IBM十年的并购经验所证明为不可避免的。IBM软件集团高级副总裁杜佩克说:“我们做了46次并购,如果不整合,我就要去管理46个软件公司!我手下就会有46个销售总监!这行不通。客户只需要一站服务,这意味着一个销售团队,一个付账系统。我们的员工也只需要一种薪酬结构、一种激励计划。”这些将是耗费极大精力的漫长过程。正如IBM软件集团执行官米尔斯对《中国企业家》所说,“真正的工作,是在并购的财务交易完成之后才刚刚开始。”
就在陈致平接受“变革”培训的几个月后,IBM正式收购了Rational。“第一反应是惊讶,下面的员工都一样。大家都在猜测:我会被解雇吗,我的工作还会快乐吗,原定计划会改变吗?”陈致平说。但当想到公司在之前特意安排的“变革”训练,他意识到这是一场准备已久的行动。并购宣布后的第五天,陈致平团队在北京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当时的IBM大中华区软件总经理吴宝淳,接下来是人事、以及职能部门的人员。他们面对面的回答每一个问题,任何的细节,和利益的安排。
“在我这个职位上,应该注意什么?”这是陈致平在和吴宝淳90分钟会面中“最重要也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往后的日子里,作为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陈致平将作为他团队的代言人和IBM方面接头,也将为IBM向下传达。一向“八面玲珑”的他似乎一时间敏感而又紧张,不知道怎样在“这个位置”上达到平衡。“继续日常的工作,不要有大变化。放轻松,我们保持沟通。”吴宝淳微笑着说。
某种意义上,陈致平团队是幸运的。销售和研发人员是被IBM当成是最重要的两项资产。“研发人员重要是因为他们写程序,销售人员重要是因为他们与客户打交道。这是我们决不能失去的,”杜佩克说,“其它的就不是不可或缺的了。比如我们会改变财务流程,整合进IBM的财务架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也一样。相反,如果46个市场总监全都留下来,我都没有那么多职位给他们。”正因为此,陈致平和他的团队得到尤其细心的呵护。
以大概半年为一阶段,陈致平的团队总共经历了四阶段的“流离震荡”。第一阶段是持续的惊讶,即使基本问题得到了回答,但面对IBM庞大的组织、新鲜的流程,还有不断的惊讶。接下来,惊讶会转变两条路,一个是不理解,不理解再往下就是生气。“工作效率为什么降低了?工作状态为什么跟以前差这么多?生气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陈致平说。如果在“惊讶”期间跟上级的沟通够顺畅,那就直接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试图了解你,接近你”。这需要大概半年,若走通了就是第四阶段,“开始接受你”。而那些“生气”员工可能会离开,他们的一部分会因为悉心的沟通而重回“接近”并“接受”的轨道。而这些员工走上哪条轨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致平的作为。
“最大的冲突来自对新系统的学习。”陈致平说。因为规模和结构都要庞大和复杂很多,IBM内部有着Rational员工看来异常繁杂的系统管理,而他们被要求尽快掌握。搞市场活动,Rational开一个20分钟的会就可定下来,但在IBM要走申请预算、审批、执行的流程,花很长的时间。“当他们来找我抱怨的时候,我不能跟着一起说麻烦,去声讨IBM。我必须稍微停下来,清理一下思路,选择好的角度开导他们。”陈致平说:“我的说法稍有偏差,对他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同。”
在陈致平之外,IBM辟有第二条“战线”。每一个Rational的核心员工,都被安排了一个来自IBM的“导师”,这通常是一个在IBM内部位高权重的高层,这些人将解答来自新员工的“私人”问题。所谓私人问题,“就是没办法去问老板的问题”,软件集团Lotus产品总经理刘秋美说,“比如我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升职的为什么不是我?”软件集团的高级副总裁杜佩克本身就是11个人的导师,他会经常接到这些人的电话,每几个月就一起吃顿饭。“我们会讨论,IBM是怎样的,你的兴趣在哪里,职业道路怎样规划。”杜佩克说:“这样我也能了解到,这些人是否会在IBM有未来。”
当然,陈致平这条渠道是更为实际和通畅的,他才是Rational员工最熟悉的人。他会跟吴宝淳保持密切而近距离的沟通。凡是新的情况,他都要从吴那里得到指导。当陈致平着急的想把员工从第一阶段直接带入第四阶段时,吴要他冷静,因为“如果中间没有铺垫,不但不会直接到第四,反而会像站在悬崖边一样,直接落下去”。当有员工离开的时候,陈致平难过的心情会受到安慰,“他们不会花太多的心思责怪我们这些经理人”。
其实最影响大局的,莫过于陈致平自己的心情和打算。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甚至在得知并购的第一时间就去拜访客户,问他们“被IBM收购会怎么样?”在并购后的第二季度,来自Rational的首席科学家被提为IBM“院士”,这给了陈致平一个强烈的信号:“IBM出过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3万人只有50个院士。这表示对我们极大的重视。”陈致平恰好又是跟吴宝淳和宋家瑜这些老板接触最多的人,他对IBM的老到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了解。这些高层能在软、硬件多部门轮换、历练得“非常全面和专业”的经历令他触动很大。这种“只在IBM才有的机会”让陈致平下了最后的决心。
一年多的“安抚”期过后,IBM开始对Rational做严格的业务要求,宋家瑜不断和陈致平聊更严肃的业务话题,一方面让Rational的资源为IBM其它产品线所用,一方面把Rational拉入到IBM的大平台上。被并购两年来,Rational的中国业务增长100%,此前的年增长率最高也不到40%,中兴、华为、工行、建行都新成为Rational的大客户。
“前面的问题解决了,但如果市场没做起来,员工也不会留下。所以能在外部市场上取得胜利,才能最终保证我们先前在内部所做的努力。”宋家瑜认为:也只有过了这个坎,双方才能形神兼备地真正融合在一起。
在采访中,记者“夸奖”陈致平虽然长在台湾,但谈吐却很像大陆人,谦谦气质也跟其他的IBM老员工很神似。听到“完全本土化”的评语,他一时高兴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前倾着身体说:“这个评价很高!”
不可能不赌,而且都是大赌
周伟火昆自述IBM软件集团的战略路径
采访/本刊记者 程苓峰
1994年,郭士纳花了两个月出去拜访很多人,有一家负责人就说:你们不要学人家做软件,卖给我吧。当时我们在软件市场的地位很弱,产品大部分在主机上,没有收费的习惯,应用方面也搞不出花样,每年都赔钱。但当有人要我们把软件卖给他的时候,郭士纳就知道一定有宝贝在里面。我们按兵不动差不多两年,整顿其它业务,止血。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强硬的收购,花35亿美元买Lotus。有人说太贵了,也有人说我们交了很多学费。但我们之所以做这个,是要把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放出去:我们从困境里面走过去了,现在有钱做重要的收购;而收购的是一个软件公司,这代表我们的未来。这是很重要的信号,市场也接收到了。在扩展业务之前,铺这几条路非常重要。
跟下来,我们押钱做了两件事。第一,给了一个人10亿美金,让他搞个数据库的生意出来,这个人就是米尔斯。另外一个,押注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边,做Websphere这个产品。从1994年看到互联网,我们就一直把四分之一的研发费用拨去使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互联网上运转。我们在这里是赌了几把的,不可能不赌,而且都是大赌。把方向定下来,这两个产品都是中间件。
任何战略家都会跟你讲:选择一个夹在中间的生意是很危险的。中间件这个领域会被做操作系统的人往上打你,而做应用的人会往下打你。腹背受敌。我们选了一条危险的路,不想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里面争,但必须要有一条路走出来,很难选。
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前有狙击、后有追兵,被迫选了这条路。我认为,首先你一定要选一条路,这条路是慢慢调出来的,交了很多学费。我们有一点运气,因为刚好有互联网,它让在中间层的软件整合成为必需。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商务,我们可能被人家打死。刚好有互联网出来,风不是对着我们吹,是在背后送我们一把。
接下来,要把一种新的观念推出去,一定要有一套手法。首先要有强有力的市场和公关,把这个观念有效地输送出去。1995年到1997年,我们费很多力气让别人相信,电子商务的运用里面需要一个中间层。花了7亿美元推广电子商务,让每个人一想到电子商务就想到IBM。然后就是去教育销售队伍,他们也要了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或不愿意去给客户讲,也不能成功。
方向也要清楚,我们就是对企业服务,绝不去做家庭;你不需要来偷看我们的战略文件,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定了战略后,就不会跟我们的伙伴竞争,比如SAP,比如中国4万5千家独立合作伙伴。反而我们的有些对手的战略就比较不清楚。有些做中间件的公司,突然去买一家应用软件公司,将来这两个怎么平衡,我不知道。有些为企业服务的公司,还希望到家庭娱乐方面发展,这两个有点冲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