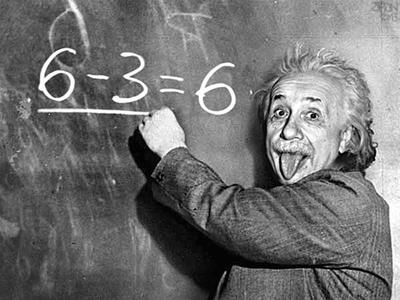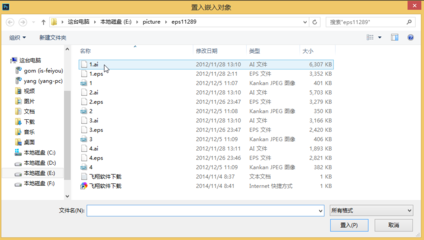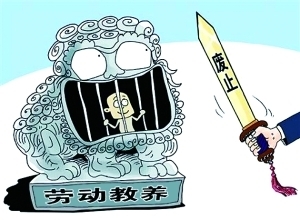无论是以任何角度考虑,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比较优势,去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必须代之以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建设作为发展的新动力

文/余南平
进入2006年,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连续发生的劳工短缺现象,让人们感到高度关注。以“轻工业高地”浙江出现的情况看,有规模优势的纺织企业目前正面临着春节后劳动力招工不足的困扰,这延续了2004年夏季以来的趋势。
面对类似这样的客观情况,作为理论研究者而言,的确希望给未来的变化方向以新的推断和对策意见。如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断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将在5年至8年之后消失”,二是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称,中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还能持续3年到5年,而著名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的亚洲首席分析师则在一份报告中称“以往中国某些地区形成的投资有利成本因素正在消失”。当然结论性推断还是理应由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做出,而有说服力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有最后10-15年开发利用机会。更有甚者,以国际视野来推断“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就是全球结束低利率时代,美国债市暴跌,金本位重新确立。这些有数据分析、严密逻辑推理的结论,既让迷信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者们感到了深深地担忧,并使习惯于依靠劳动力成本作为招商引资条件的许多地方官员感到了压力,面对于这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崇拜者的担忧与不安,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恐惧“人口红利”消失吗?我们需要非常担心由于“人口红利”消失而失去国家竞争力吗?或者说我们习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真的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惟一的可依赖优势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中国劳动力资源真实的供给情况。据我国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按修订的生育“低”与平均寿命“较低”的方案,那么在2010年至2014年间,我国仍将出现长达5年的每年出生人口数均超过2000万(2000年约为1663万)的建国后第四次出生人口数高峰期,而在2005至2024年间,我国将出现长达20年的每年15-59岁人口数均超过9亿(2000年为8.33亿)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高峰期。另外从中国城市化率提高的长期趋势看,研究同样表明:如按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202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60%,以及假设的城镇常住流迁人口增长占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常住人口总数比例的“中”方案(该比例从1995年至2000年间的42%逐渐上升到2010年至2015年间的50%、2020年的52%)与城镇常住流迁人口中的中老年人在城镇的滞留比例“中”方案计算,那么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数将达到7.95亿,比2000年增加3.36亿,其中法定劳动适龄人口数将达到5.03亿,比2000年的3.14亿增加1.89亿。而这个数字与目前的全球制造业全部岗位8000万相比的话,即使发达国家全部退出制造业,将这些岗位全部转移给中国,中国还是面对巨大的劳动力剩余压力。而在劳动力供求已经市场化的环境下,劳动力价格还是不会因为供应短缺而全面、快速上升,因此,从长期看,扩大就业,并有效地改善劳动力知识结构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其次,我们看目前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这个上升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分析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并联系分析中国近十余年的劳动力价格变化,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人均GDP上涨近三倍的过程中,中国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以农民工为标识的基础劳动力价格,在过去的十年内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沛,另一方面反映了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与农业收入过低,以致大量农村基础劳动力流入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基础劳动力价格过低,还反映在劳动保护与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许多工作岗位在没有环保成本,恶劣劳动环境,延长劳动时间,拖延劳动时间,恶意拖欠工资……等种种违法雇佣行为下维持了所谓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而这种所谓的“优势”尽管可以作为吸引投资的有利因素,但它却是以损害人的劳动尊严和实质性劳动自由权作为代价的。而恰恰是2004年后,党和政府有效的农村政策逐步落实,提高了农业收入,使得农民工在市场经济“理性选择”下,可以权衡劳动岗位。这种劳动力成本上涨,首先是“人道市场经济”的一个正确价值取向,其次它是对于过去劳动力保护与法律救济不利的一个有利的纠正。对于这种“以人为本”、“成果共享”发展观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化,我们有什么理由感到不安?难道我们还要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十几年,劳动力价格持续稳定不变的“低成本优势”高声喝彩?
再次,我们来看劳动力比较优势是否是我们惟一可以依赖的发展之路?当我们清楚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一个“人道市场经济”的历史结果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当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时,作为后发的发展国家如何摆脱已经习惯的低成本发展路径,转而向制度设计、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特别是技术进步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际比较显示,是恰当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是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公共管理,是低成本有效的社会政策……而创造的整体制度环境与由此带来的社会公民的团结与信心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不仅表现在北欧这些传统的高福利国家的现实国际竞争力上,同时在中东欧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上也同样得到印证。
最后,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后,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长期增长?对于真正的国家竞争力,早在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竞争战略研究发起人、国家竞争战略理论奠基人Michael Porter就在其大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在结合世界技术发展潮流与产业竞争格局演化的历史中,波特教授大力批判了“比较成本优势论”、“规模经济论”,并对于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需要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提出了反传统的,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从本质上看,加强国家竞争能力,保持技术先发产业的全面领先,并带动产业集群的增长一直是近二十年美国国家的全球最核心竞争战略。
以国家竞争力的“钻石理论”来看,竞争力本身是一个正和结果,如果一个国家,无论其是先发技术优势,还是后来赶超技术国家,如果其能够改善生产率,并使国家在稳定的现代制度下更加有效率和创新能力,那么在全球化技术、资本溢出、特别是国际市场扩大的情况下,竞争力优势国家将走向繁荣与富强。因此,我们要摒弃的是,国家对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偏好(重点扶持特别产业,甚至包括就业规模考虑的习惯性错误思维),而是代之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培育,特别加强公共政策对于创新性动力与机制的保护,并努力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紧密关联,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国家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才是共同决定有效竞争环境的基础。
综上所述,就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和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而言,无论是以任何角度考虑,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比较优势,以资源、土地、环境保护为代价去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必须代之以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建设作为发展的新动力。而仅就人力资本而言,中国的高学历劳动者,在今天世界范围内有着无可比拟的高性价比(本科毕业生与普通劳动力平均价格差400元,中国的博士劳动力价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2),有着绝对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我将之称为“廉智劳动力”,根据廉智劳动力理论,我们完全可以以最低的知识成本创造一定领域和行业的技术领先,如我们今天在航天领域的技术独立性和领先性。所以,如何利用这些优势?以制度的改善去引导这些人力资本转化成技术创新,带动中国经济结构有效转型,并由人力资本扩散而转化成社会资本扩大,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真正关键问题。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霍普金斯-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客座研究员)
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
文/穆光宗
人口负担比是相对次要的因素。譬如,一个值得注意的反证是:根据人口负担比50%截断的曲线,我们看到的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或称“人口红利”,编者注)落在1965-2003期间,但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55-1973年,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马上就进入了低增长期,GDP增长率为2.81%。
韩国的例子也说明了“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错位。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年到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年到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种对体制性约束的解除,1978年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本是不能想象的。中国过去20多年的几次大的发展都与体制的创新有关,第一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小平南巡,第三次是户籍制度改革。
人口的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的快速转变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不如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
只看到相对数的存在就认为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就认为中国具备了和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其他国家一样的机遇,是失之偏颇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