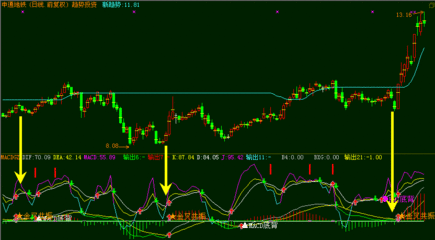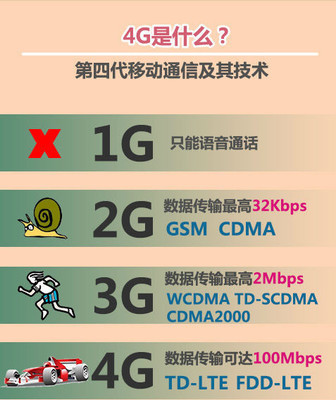在戏剧般的人生里流转,令陈久霖更加随性。不过好胜心仍在催促他东山再起
2006年3月21日下午六时,位于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着粉色衬衣、红色领带的陈久霖被戴上镣铐,走进了法庭左侧的铁围栏中。通过铁围栏后面的那道门,他将被直接送往监狱服刑。被判入狱4年3个月,罚款33.5万新元,这标志新加坡当局把陈久霖认定为中航油事件的最大责任者。离去之时,背后四十余位律师、记者、亲人、朋友、以及各利益相关方派遣的关注者,皆起身驻足、面带唏嘘。
相比于一年前东窗事发时的焦躁和惶恐,陈久霖一副历经风雨、游刃有余的姿态。“几年后见!”他向关切者颔头示意。
3月初,是陈久霖上庭前的日子。主要时间都在律师楼里准备庭辩的材料,不辞倦怠、丝丝入扣;时而会面到访的朋友,在饭桌上回忆在曾被扣押时的逸事趣闻,笑声朗朗;周末,跟妻子到教堂里听读圣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心得,谦恭默然。庭审的几天里,陈久霖有时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听审席第一排,搭拉着头,像一只败阵气馁、兀自舔伤的猎豹;不过没过多久,又抖擞精神,时而为检控官的指责而频频愤然起身,时而以顿挫有力的声调为围在身边的记者做答。
一个与他相识二十多年的同学说,陈久霖这一年多的苦和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换个人,恐怕早“自己了断”了。这位同学一直坚称陈在中航油案中应当担负相当的责任,但也说:“如此坚韧走到今天,就冲这一点,他也算个枭雄。”
狱中
2005年6月7日,新加坡当局对半年前还是“打工皇帝”的陈久霖突然逮捕。在筹足巨额保释金前,他被关押了72小时。
牢房6平方米,水泥地,没有床,有一个无遮无栏的马桶。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停水,排泄物就留在马桶里。墙壁上有一个本应是出水的按钮,可使了很大劲也按不下去。房间里维持在20度左右,但只能穿一件衣服,不能穿袜子,特别冷。
6平方米的房子要关四个人,为什么是四个?一个人太孤独,没有谁受得了;也不是两个人,怕打架,没人劝,打死了都没人知道。三个人也不行,两个欺负一个。所以要四个。就并排坐着或者睡着。
头一天在拘留所,陈久霖跟贩毒犯和抢劫犯关在一起。毒贩因为是现场被抓,只穿了个短裤和汗衫,冻得要死。一会儿头冷了,就把汗衫裹到头上来煨着,一会儿脚冷了,就把短裤拉下去绑着。毒贩还跟陈久霖谈经验,告诉他自己是怎么贩毒的。
后来从拘留所转到监狱,陈久霖受到“照顾”,一个人住一间。别人告诉他,“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怕你跟他们一起住学坏了。”可这样一来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孤独得想一头撞死”;到后来,就是什么都不想,“像狗一样活着而已”。没有室外活动,就在里面做俯卧撑。在监狱的第三天,狱方给了他一本卡耐基的书,他在“出去”之前就读完了。
陈久霖说,他刚进去监狱的时候,所有衣物都要脱光光,把身体各个部位给人看,怕藏毒品之类的。做各种动作,蹲着、起来,看身体有啥毛病。然后走过一个栏杆,一个吹风机在旁边吹,两只警犬就顺着风向闻气味。第一闻有没有毒品,第二把你的味道闻出来,一逃跑,警犬就把你追回来。
每人领一张旧毯子、一个破席子、一身薄衣。硬的东西不能带进去,怕割腕自杀。人一进房间,铁门自动合上。没有枕头,就把鞋脱下来枕着睡。吃不到中餐,成团的糙米饭,有时拌着带咖喱的白菜,没有丁点肉。三天三夜,他“减肥”三公斤。
其实,陈久霖还是受到优待的。别人洗澡就是许多人围着一个池子,抢到一盆水,往头上一浇,就走了。他可以到一个冲拖把的地方单独洗。还给他一个盆,接点水进去,白天用来喝,就不必喝马桶槽里的水,晚上用来冲厕所,不会太臭。
监狱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从外面打开,每天三个时间,早7点,中午12点,晚9点,关押的人都要站在后面,眼睛对准那个窗户。狱卒这三个时间都要过来巡查,看一双眼睛是否出现在窗户后面,因为怕你死在里面。铃声一响,就要大声喊出来:Yes Sir!以证明你还是个活物。
当陈久霖跟朋友回忆这一段时,双手趴在桌子上,眼睛瞄准前方,非常大声有力的喊出来“Yes Sir!”...真像是回到了监狱现场一般。喊完之后,同身边的人一起禁不住大笑起来。这一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大叫,确乎保有了监狱生活惟有的一点亢奋,甚至也是乐趣。
人事洗牌
曾在高堂上呼风唤雨的人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变了,环境也变了。讲起一年来的人际交往,愤慨自不必说,身陷囹圄自然遭人嫌弃。也连同家人,“承受巨大的耻辱”。

他需要以前的秘书给他找一份当年发表的文章,可秘书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短信。陈久霖纳闷,是不是手机坏了?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说话,谁知秘书竟扭头跑开。这样的对待并不少见。其他人还好理解,陈只是不明白,曾经一同打拼、朝夕相处的同事,何至于此?
这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那些在陈久霖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人,“大多半都淘汰了”,“他们素质低,太怕事”。
不过惊喜亦有之。在这一年多接触陈久霖的,都是“高层次”的大老板。有些人原来就知道陈久霖,但都到了他陷于囹圄的时候才来主动结识。据说,这些人里包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头几位华人富商。
2006年春节,印尼力宝(Lippo)集团副主席李宗(Stephen Riady)请陈久霖去他在新加坡的家里吃饭。一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单房就有几十间。李宗早年曾在香港打过7年的官司,那段时间的悲苦和彷徨,李宗都讲给陈久霖听,令他“心有戚戚焉”。
也不仅是安慰,还有开导。在陈久霖上庭前这个周日的教堂聚会上,李宗发言,大意是:一个人总要有敬畏。职员要对老板负责,后者的管教能够令前者免于松懈和灾祸;但老板自己又对谁负责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就越容易没有约束,而马失前蹄。所以越是权贵,就越要警醒自己,心存敬畏。李宗站在中间讲,陈久霖坐在人群中,埋头静听。
陈久霖还是有难解之处。那些主动来看望自己、表达支持的,以国外朋友居多。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前执行委员,一个德国石油专家,专门从德国飞来新加坡。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提出为他写书,还有台湾一个86岁的老太。这些令陈久霖念念不忘。
但反差的是,“我的同胞对我的冲击更大,踩我的是我的同胞”。陈久霖总对有些媒体把所有罪责都归到他头上而激愤,也对自己未被及时批准回家、未能见上病危母亲最后一面而不能释怀。有些人说陈久霖应该自杀以谢罪,他觉得自己不为私利、全心进取、犯的只是技术层面的错误,何至于此?!面对攻击,他有时甚至会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对于自杀,刚开始他回应,“自杀并不等于承担责任”。稍后知道,在基督教义里,自杀是一种罪过;在新加坡,自杀要受法律制裁。再到后来看得开了,“挫折是对未来的祝福”,他对自己说:“人一生,哪能没有挫折?”
关于未来。陈久霖想要写书,也有很多人想为他写书,这也许会在监狱里完成。据说,已经有至少6个大公司邀请他,既有国有、民营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石油行业,也有非石油的。有一家还想在他入狱之前就先签订雇佣协议,另一家中国民企开价年薪600万人民币。“用他们的话讲,”陈久霖说:“我主要还是不走运。”
命运啊!
关于“不走运”,另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在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久霖不就成英雄了吗?……这就是命。
历经挫折的人,都很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在去问陈久霖,你有没有信宗教?他呵呵一笑。“不能说完全信,但感觉中,冥冥之中还是有主宰的力量。”
陈17岁那年,陈妈妈给他算过一次命。说大概43岁左右会受到挫折,但终究会过去。陈久霖61年出生,2004年正好43岁。后来陈久霖自己再没有算过命。到今年初,有个朋友给陈久霖推荐一个软件,那是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圈的一个推测命运的系统。把名字和生辰输入进去,结果是:2004、2005两年倒霉。
2004年9月,中航油新加坡办公室鱼池里的风水鱼全死光了,一个不剩。很多人说这不是个好兆头。可能也是巧合,陈久霖说。
事发之时,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新加坡采访,又去了一趟陈久霖的湖北老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陈久霖相信风水,但风水没有帮上他。“其实不是这样”,陈久霖说,是之前没有相信风水,之后才有所反思。
2005年中,陈久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博士请他去基督教会。教友知道他的败落和经历,包括李宗,都尽力开导,期望他得到“主耶稣”的帮助。现在,陈久霖和夫人每周星期天早晨都会去新加坡亚历山大路上的教会,读圣经、唱颂歌、与“弟兄姐妹”分享。
不过王博士说,陈久霖还在路上,并未能诚心接受主。因为他虽然常来,表明内心有需求,但一边听经,一边还时常掏出手机来接发不断的短信,表明一刻也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王博士非常理解。毕竟,一个官司在身的人,一个出身寒家、从无到有在异国他乡打下江山的强人,让内在的自己的力量屈服于外在的“主”的力量,总要比常人艰难得多。
知其不可为而为
推究于“不幸运”或者“命”,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滑稽不过的行为。陈久霖面对着15项指控,自己认罪了其中6条。白纸黑字,怎么能够归咎于“命”呢?
其实陈久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法律上做开脱,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反思在那场“天人交战”中因何败阵。在3月上庭前夕的辞职信上,他用到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的话。在庭上,辩护律师也用到“他不是点火者,而是反被火伤的救火者”,这样带有强烈逻辑辩证色彩的总结。
3月14日晚,陈久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同学,浙江某医药公司老板蔡先生特地飞来新加坡,参加第二天的庭审。蔡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是出于对过程的关注、情感上支持,而结局早已料到:陈久霖会被判刑大概四、五年,没有悬念。果不其然,陈被判刑四年三个月。
不过明知大局已定,陈久霖仍然倾尽全力、争取充分的时间来为己开脱。本来要在2月进行的开庭辩护推迟到3月,本来“雷打不动”的3月8日推迟到15日,而15日到17日连续三天开庭,辩护仍没有结局,直到21日才最终落判。这跟前四位被控方都在一天内快速结案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庭上,陈久霖还常常愤然起身,意图不要借助律师,而自己用略显迟钝的英语直接对检控方的指责还击。
据说,若非环境所迫,陈久霖还倾向于并不立刻认罪,或者被判后继续上诉。如果上诉高等法院将能有长达5个月时间庭辩,“至少可以把事情原委说得更清楚”。之前不久,新加坡本地富商邱德拔的两个女儿因为隐瞒股票案被控,邱花了200万新币请新加坡最好的律师,两个女儿无罪释放。陈曾跟身边人说,可惜他出不起200万。
上庭前夕,陈久霖约见《中国企业家》记者,郑重的表明,他跟搞垮巴林银行的里森是不同性质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里森是具体操作者,而我是宏观管理者。操作者的责任要大于宏观管理者。第二,里森有严重的欺诈,私开账户,我没有。第三,里森在事发后逃跑,而我主动配合调查。第四,事发后里森转移了所有个人资产,而我对个人资产毫发未动。第五,里森有个人的意图和利益,隐藏了个人账户,而我敢打保票,没有个人利益。第六,巴林银行亏损14亿美元,倒闭;而中航油亏损4.8亿,成功重组。重组能够成功,离不开我为公司奠定下的发展基础。”
陈久霖最后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如此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