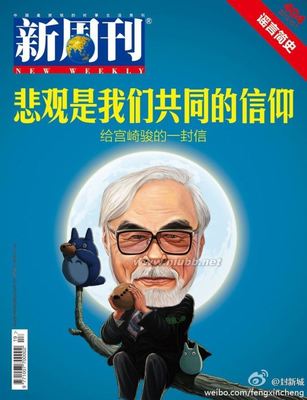从GE中国董事长到波音中国总裁,王建民走出了一条华人领导全球公司的道路
文/本刊记者 丁伟
这一天原本是杰克·韦尔奇的新书《赢》出版。
美国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9点,韦尔奇要上CNN宣传他的新书。当时正是北京时间晚上,当天通用电气(GE)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医疗技术园,时任GE中国董事长的王建民陪GE副董事长、北京副市长参加了典礼。吃完晚饭不到9点,王建民打电话给太太,“打开CNN,我回家要看Jack。”但等他一进门,太太说,“你看不到Jack了。”
“9·11”成了历史的转折点。那年底韦尔奇退休了,伊梅尔特在9月7日接的班。而从安然、世通事件到波音前后两位CEO菲尔·康迪特的政府合同丑闻、哈里·斯通塞弗的性丑闻,华尔街经历着多事之秋。“9·11”还最直接地使全球航空业陷入低谷,波音、空客的日子都很难过。
但没想到,这些商业变故都间接地影响了远在中国的王建民。韦尔奇退休后,王建民也从GE中国提前退休。一年后,2002年11月19日,58岁的王建民被任命为波音中国总裁,从多元化的“大象”转到了飞行的“大象”,希望以在GE工作了20年的经验和1990年起回国的本地智慧,“缩小波音因文化差异在大陆市场面临的竞争阻力”,并在2020年(中国达到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的全球化品牌”。
像其制造的737飞机一样,波音也难免遭遇气流颠簸。2005年3月,斯通塞弗因婚外恋辞职了。7月,詹姆斯·迈克纳尼出任波音新的董事长兼CEO。王建民对他可不陌生,迈克纳尼曾任GE亚太区总裁,是GE(除了韦尔奇)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迈克纳尼是韦尔奇的三位候选人之一,在伊梅尔特胜出后去当了3M的董事长。
此等缘份让人感慨。王建民笑着说,“真的是巧合,所以说,你绝对不能做坏事,因为以后你以前的老板还是会找到你的!”他的大笑很有感染力。
GE印记
当1980年王建民进入GE时,GE在1981年迎来韦尔奇的时代。他见证了GE一系列重大的变革,虽然刚开始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对韦尔奇的作法也不理解。待至90年代后期,他任GE中国董事长,直接上司就是韦尔奇。1999年韦尔奇参加上海“财富全球论坛”,也是他去接的机。
GE在王建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波音回忆GE时,他还热情地向本刊记者推荐前GE副总裁拉里·博西迪写的《执行》,“韦尔奇讲得很好,做的跟写的(自传)差不多,但执行的是博西迪。他们说话很实际,伟大是很多件小事成功逐渐变成的。”
像很多高管一样,王建民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管理的。他大学读的是电气工程,毕业后只想做一个有成就的工程师,后来才转做公司管理,并且先后执掌了两家美国最一流公司在中国的事务。他谦虚地说,“我的雄心没那么大,我也没想到会做到今天这一步”,但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性格使然。
王建民1944年生于福建,5岁离开上海——“我还记得上海的幼儿园”,在香港读小学,12岁到印尼读中学,19岁去美国读大学。三地的文化不同,“但各种文化中对善恶的认识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个人很容易相处,这对沟通很关键。”
他先是在雅加达一家做进出口的家族企业,之后到圣路易斯的爱默生电气工作了9年9个月。本来干满十年,即便离开公司也会付养老金,但他觉得前途不大,没等最后三个月,就以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和三项专利去了GE。王建民说,“你要找一家能够让你进步而不是有玻璃屋顶的企业。我逐步改变是因为见识不一样,GE给我机会有很广的见识。”
1990年,王建民被GE医疗系统部派往北京筹建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公司。这也是他第一次回国。当时家人和他开玩笑,“公司真的没人才,派你到中国去,你的中文都忘记了。”后来王建民到波音后,这段经历也成了航空业的一个花絮:那时候飞北京必须经东京,只能从美国西海岸起飞,现在从纽约或从芝加哥都可以直飞北京,而且乘坐的是波音747。
在GE,王建民最难忘的还是领导层跟员工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去总部开会,之前他只在中国见过一次韦尔奇。韦尔奇第一眼看见他就说,你的孩子上中学了吧?这让他很感动。王建民家里有很多GE的照片,其中就有韦尔奇和他儿子的合影。
再次成为他老板的迈克纳尼,是王建民接触的第一个了解东方概念的西方人。当他从GE马来西亚调任中国时,迈克纳尼不单面试他,还游说他太太一定跟着来中国。“他跟杰克一样,对业绩要求非常高,但是对个人又非常关心。”因此,当迈克纳尼出任波音CEO时,王建民的第一反应就是告诉太太。
“一个人很难在做老板的同时跟员工交朋友,这也是我们跟老板交朋友比较难的事”,王建民很高兴以前的部下还当他是朋友,尤其是可能有优惠——GE是波音的引擎供应商。“一个人在哪座城市能够称为家呢?其实多数城市是一样的,朋友多,亲戚多,感觉就是家。我在GE的记忆就是跟我一起发展的人,我能培养出一批人才,这是最美好的记忆。”
至于管理心得,王建民总结:一是执行和结果,二是广度和深度。国内的企业家他欣赏柳传志(他俩在GE克劳顿培训村是同学),认为他是强调流程管理的典范。
“很多企业的策略都是一样的,成功不成功在乎执行,执行不执行在乎领导人才,领导人家服不服在乎是否以身作则。”王建民说,迈克纳尼在波音亲自负责培养人才和领导力,其它的事都交给别人了,其人才标准是“又红又专”,即价值观加业绩。王建民带回国内的领导力培训课程,是波音在美国以外第一个。
从西雅图到北京有多远

58岁来到波音,王建民不仅进入了全球化的行业——航空制造业,做起了中美贸易最大宗商品——飞机这门蕴含着异乎寻常的政治性质的大生意,还卷入了波音与空中客车这场美国与欧洲积怨已久的竞争——空中争霸战。
波音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到波音诞生的1916年,创始人威廉·波音聘用了生于北京的王助设计飞机。后来波音宣称“跟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起乘坐空军一号进入中国”。2002年12月,基辛格、骆家辉等在北京参加了波音与中国合作30周年庆祝活动,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艾伦·穆拉利不失时机地介绍了刚刚上任的波音中国第一任华人总裁王建民。
如果哪一家美国公司是实施本地化的最佳选择,那可能是波音,王建民说。他熟谙中美文化,“美国人的笑话我听得懂,中国人的笑话我也听得懂,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享受。”深受“9·11”打击的波音正需要一位新“机长”——从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空客在中国捷报频传,但波音付之阙如。
刚到波音时,王建民还有些不适应,波音似乎效率不高,太过保守,不像GE讲究speed(速度),但这正是航空业的特点——safe(安全)第一。跟GE不同,波音是“飞行的大象”,它要变向又不能停下来,既重量级也要跳舞,这是一种新的挑战。而飞机这门生意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说了算。比如飞机生产是波音总部的事,他的责任是把采购、组装、培训等跟中国合作好。比如飞机销售属于地理工业政治领域,常与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高超的公关技巧,波音最高兴听到“中美贸易逆差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多买波音飞机”。
他不肯透露做政府关系在GE和波音的区别,“飞机这个行业你光讲出来不行,必须干好……有好事大家都高兴,高兴的时候谈什么都比较容易,政治因素在市场往上时影响小,客户更看重效率跟成本……我们应该跟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多打交道。”
鉴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2010年世博会,波音和空客在中国战略市场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它们在2006年前后都拿到了150架飞机的创记录订单。像其它制造业一样,航空业也以技术和工作转移取悦市场。
中国是787梦想飞机的启动用户,波音最希望2008年787能挂着中国国旗,载着全世界的人来北京看奥运会。从西雅图(波音总部)到北京有多远?王建民说,“实际的路途是一个航班的距离,但具体的路途必须要同心,有共同的目标,做真的好的伙伴。”
在王建民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好几个飞机模型,其中就有波音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共同设计的新型国产支线飞机ARJ21。波音还第一次在美国以外做747-400可改货机的生产和取证,“前50架订单都在中国,这是实际的事,但是不能(像空客把组装厂搬到中国)排到新闻的首页。”该项目在总部的“绿色房间”是否会出彩?那儿挂满了照片和图表,标示波音高层经理的事业进展。王建民拍了拍记者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我62岁了。”
做了这一行以后,王建民再乘坐飞机,懂得哪些地方不一样,感觉“坐波音飞机太美好了”,尤其是787,速度感跟飞行感是“addictive experience(会上瘾的体验)”。随着飞行继续,他将稳坐驾驶舱,看是否已经达到巡航高度,或还需要爬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