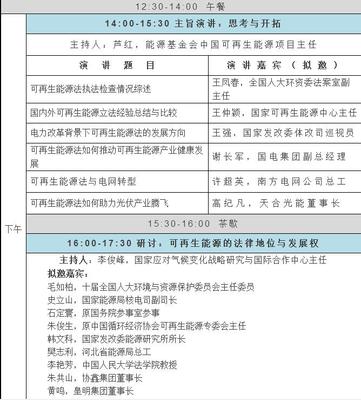历史让中国商业的传承在时间上有了一个物理断层,那些曾经的商业理念和精神能被延续下来吗?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在做这个叫做“世家”栏目的日子里,最经常遇到的疑问就是:“中国还有世家吗?”正如天津买办世家后人、作家林希所言,世家必须是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起到过重要影响的这么一个家族。这个影响不是一代人的影响,而是好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延续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中国,符合“世家”概念的家族应该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让商业的传承有了一个时间上的物理断层。我们在寻找世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所谓世家的后代们,他们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情感联系上,都已经离他们的祖辈很远了(记者不止一次接触到世家后代的遗产纷争,所谓遗产可能也不过是几间老屋而已),更不要说将祖先在工商领域的名声、地位和作为继承下来了。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老一辈工商业者们并没有被遗忘,最直接的答案是,他们的商业理念和精神被保存了下来。
在寻找中断百年的世家记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在在中国工商业界流行的一些所谓时髦的理念,比如国际化、去家族化、慈善、社会责任、贵族化生活等,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商业前辈们早已经身体力行过了,只不过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休克,让他们成为一部没有结尾的断代史。今天,历史奇特的复活不过是续写。
在梳理世家的精神遗产中,我们发现有两点对现在中国的商界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一是早在70年前商业前辈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家族化企业的反思,他们在“去家族化”的努力和智慧,对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建立起了工商界“士魂商才”的新形象——无论在技术层面的商业才能上,或形而上的商业伦理上,相比徽商、晋商这样的古代商帮文化,他们都有超越性的理解。他们实际上在一个乱世里以“商”的面目承担了传统中“士”的责任和理想。
“去家族化”的努力
大儿子卢国维,武汉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二儿子卢国纪,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女卢晓蓉,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孙子卢晓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孙子卢铿,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这是卢氏商业世家的一份名单。但是必须了解,卢作孚的后人并不是典型,而是一个例外——在中国大陆,像卢家这样至今以群体的方式活跃在商界的世家是绝无仅有的。在所有大陆的采访对象里,几乎只有卢家的后人生活在现代化的住宅里——大儿子卢国维在北京的住处正是孙子卢铿开发的楼盘。他们的精神给人感觉元气比较充足,没有“遗老”的感觉。不过,卢家后代如今的活跃,也许是卢作孚预料不到,可能也不想看到的。卢家的后人承认,卢作孚生前从来无意让子女学习相关专业来接班。事实上,卢作孚留下的大量文章能够证明一点:卢作孚是非常反对将现代企业家族化的。
卢作孚认为,中国社会的“两重集团生活”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第一重集团生活是家庭生活,第二重集团生活以家庭味基础形成的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这“两重集团生活”或“两重依赖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封建关系和宗法关系。所以,卢作孚非常反对,也从来不在民生公司加插自己的亲眷朋友担任职务,他试图以民生公司为样本,建立中国人的“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像西方那样超越家庭,超越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工商时代的集团生活组织”。这种集团生活不是以依赖家庭、亲朋关系为核心,而是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这种集团生活的标准,不是家庭、家族之间或者派别之间的角斗,而是促进于企业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味精大王”吴蕴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和卢作孚相似。他生前规定成立基金会管理自己的所有投资资产,子女只有在教育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可申请使用,其余大部分用于社会公益和再生产。只不过,他的这个愿望因为时代的断层而被消解了。解放后,吴蕴初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国家有关部门交托给上海图书馆管理。吴蕴初的女儿吴志莲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前几年还去上海图书馆查询过,对方的答复是,这笔财产已经花掉了相当一部分,而且没有能够提供明细的支出记录。
这种“去家族化”的做法是对中国商业传统的一种逆反。从明清商帮以来,中国商人一向习惯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包括血缘、地缘关系,把这些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这个转化整合的过程相当严密和慎重,以至于中国古代商帮文化中有“家族即宗教”的说法。乔家大院、常家庄园那些工整压抑的高墙和祠堂就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商业家族的社会功能——以社会功能而言,中国的亲族组织相当于西方近代各教派的组织。
这是中国商业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方式。清末民初,中国新型的资本家中仍然有很多走的是这条路。荣氏家族便是以兄弟关系为轴心建立的。据1928年统计,在荣氏集团的19个企业中,共有总理、协理职位54个,其中荣氏血亲占了31个,姻亲占了14个,占总数的83.5%。荣氏集团还十分注重地缘关系,1920年荣氏集团共有职员957名,其中无锡同乡就有617人。
这种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启动的时候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利是弊?
一方面,韦伯曾认为,新教伦理的一大成就就是把亲族的束缚打破,使家和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人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系,没有事业功能,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家族生活和资本的人格格格不入:一个是自然经济,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传统儒家文化,一个是科学民主;一个是一元专制,一个是自私和自治。
另一方面,即使在韦伯称道的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世界,仍然不乏企业和家族关系的结合。18世纪初期的英国钢铁工业几乎全在教友派的控制下,而其中最重要的企业家都和创业的达比(DARBY)家族有亲族关系,包括儿子、族人、女婿、连襟。直到今天,历史最悠久、最强大的家族企业仍然来自西方。在对血缘地缘网络进行整合的过程当中,这些亲族和同乡伙计事实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事业功能”。中国家族商业的伙计制度可能正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前世分身。
有趣的是,工商世家文化在中国大陆衰落,在海外却以茁壮的方式成长着——荣家、唐家(唐英年家族)的后代都肩负家族振兴的荣誉感在商界和政界发展。新加坡学者林孝胜先生评价说:“帮权和家族企业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两根栋梁。”一个人在商业世界里要有所成就,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安定、自由。时代变局中的工商业者们,曾经因为战乱无法获得安定的社会环境,在1949年以后又一度无法获得经营的、人身的双重自由,这种生存状态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现实:中国即使有工商世家,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士魂商才
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几年前,为了替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申报一个农业项目,我曾经在他们制作得很精美的项目规划报告里附上了祖父所著《乡村建设》的全文,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希望可以为这份申请报告提供一点历史佐证。没想到事后传下话来,农业部的一位领导看完这套材料后最感兴趣的反而是我祖父的文章。他说,想不到三十年代就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想做的事!”
从辛亥革命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变局里的实业家们经历了时代的一次心理整合,他们的意识创新、技术创新、伦理创新,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佐证,而有强烈的时代认同。
现在我们常说,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前人就开始有了“决胜于商战”的国际意识:国力的竞争中,比军事竞争更重要的,是经济领域的竞争,必须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夺市场,进行商业竞争。打仗、搞运动,搞不出GDP,搞不出国际地位。卢作孚写到:“今天以前用军事的方法求得全国统一,直到今天没有统一,则这种方法已可证明无效了,至少应作一度新的试验,求一种新的方法,这新的方法是从四个运动(指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使中国现代化。”
这种意识的觉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亡所引发的危机感。辛亥革命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却启蒙了一个民族的国际化商业意识。上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由医转文,试图从思想商拯救国民。一个叫做范旭东的湖南人也在日本弃兵投商,试图走工业救国的道路。这个人后来建立起了中国首家制盐企业久大精盐厂,结束了中国人一日三餐都是进口“洋盐”的状况,并且成为中国的重化工之父。传说他的转向是因为冈山第二高等学堂的校长酒井的一句话:“俟军学成,中国早亡矣。”范旭东于是改入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
除了意识,民族资本家们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可能更加叫人惊讶。卢作孚几乎算是同辈中最擅长思考的企业家,现在我们发现,他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很多想法竟然和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理论不谋而合。他的“四个运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当代管理学流行的“标竿理论”和“蛙跳式发展”有相通之处。他认为革命与建设必须相辅相成,“先要有好的建设,然后有快的破坏”,这也可以作为社会改革“博弈成本”理论的一个例子。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卢作孚就提出不能把人当作单纯的“经济人”,而应是“社会人”,应该在管理中充分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效率的道德基础。这些观点是西方行为科学的基本观点——西方行为科学在三四十年代才形成,而卢作孚在三十年代就已经付诸实践了。
这些前瞻性的创新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那个年代的西化——重视西学,在设备、技术、人才、管理、资金上都充分吸收西方的影响。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中国工商界新出现的“海归派”担任了主角。在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尤其商业世家,有相当一部分有海外的教育背景,他们自信、直率,他们挑起的“西装马褂之争”是以和传统的冲突为代价的。无锡唐家的儿子唐星海从麻省理工归国后开始介入父亲唐保谦的纺织事业,他花钱购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在工厂里废除工头制度,注重人才资源的培养,他甚至借钱把工厂开到了上海。这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使唐星海一度和父亲、叔叔的关系闹得很僵。但是1932年,唐家庆丰纱厂的盈利超过同城荣家,达到创厂历史的最高水平。
更重要的是伦理创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企业家在商业伦理上已经有了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使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实业界出现了一个与文化界密切来往、融合的趋势。邹韬奋和卢作孚、吴蕴初和章乃器、范旭东和胡适……这些人物关系都是可以写书的。

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序列中,“士、农、工、商”,商人重利轻义,是四民之末。明清时期,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商”的社会地位有向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升和融合的趋势。到了三十年代,工商业者无论在知识水平、道德规范、责任承担上,都已经成为仅次于“士”的社会阶层,“士”和“商”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他们已经以“商”的面目承担了传统文化中“士”的一部分责任:改造社会、思考国民性,甚至是服务社会公益。
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极其必循的道路》中这样写到:“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魅力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应,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
今天,你能相信以上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字出自一个商人之手吗?就是这个人,1921年站在四川泸州的忠山上,和好友恽代英分手。恽代英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则坚持要用事业启蒙心智、造福人民。
余英时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中不止一次谈到这种融合和殊途同归:“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对于自己投身的商业抱有一种自傲的心理。在他们的创业和经营中,都多少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动机——挣钱的目的已经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世俗的欲望,也包括财富带来的权力和声誉、因能使无数人就业和家乡经济繁荣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