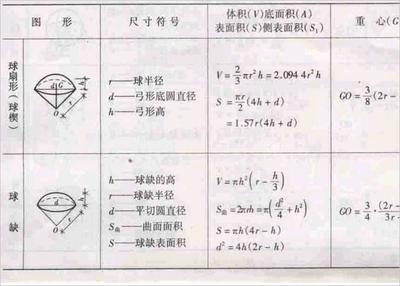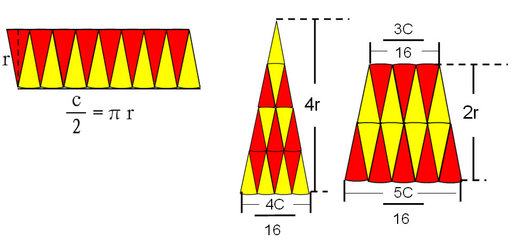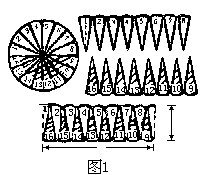“在每个时代,他都能够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迅速地找到应对方法,不断调整自己。他做人就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资耀华是谁?
作为银行家,他的才干、眼光和业绩有资格获得各方一致的高度评价。他的老板、金融巨子陈光甫说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而共产党给他的盖棺定论是“对共和国有襄赞之功”。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年龄、能力、声望都处于巅峰状态的银行家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向学者的转型——他潜心研究货币史。在如此的生死疲劳、命运跌宕中,委屈和尴尬都是可以被预料的。但是,在他92岁时写就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后半生的经历却不作思考、匆匆略过,保持着习惯性的沉默。
前半生的意气风发和后半生的适时沉默同样意味深长。有人说《人民日报》和回忆录里的资耀华是两个人。事实上,在资耀华这一代人的辉煌和沉默背后,到底是平静还是沟壑?这实在是个谜。
“他算不上什么世间异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在每个时代,他都能够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迅速地找到应对方法,不断调整自己。他做人就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2006年9月29日,资耀华长女、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对《中国企业家》说。

天津的银行家生活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业,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在中国,这三种近代事业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端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上海。中国人介入现代银行业务肇始于以上海洞庭席家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买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界形成了宁波路和外滩对峙的局面——外滩外资银行密集,宁波路则汇集了大量的华资银行。这是中国民营金融业的上升期,陈光甫、李铭、徐新六、张公权这样的第一代银行家正是意气风发,比陈光甫小19岁的资耀华这样的第二代,也正是这个时候出道的。1928年8月,陈光甫任命28岁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毕业生资耀华担任上海银行调查部主任。
“但他真正成为一个银行家还是在天津的15年。”资中筠说,“1935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调任天津分行经理。尤其头两年,抗战还没开始,他算得上意气风发。”
尽管都有租界文化,但天津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城市。按照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的说法,“想研究天津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的时候天津就不发达,每当天津发达的时候北京就不发达?”那个时代的天津处于发达时期,是华北金融中心,现在的解放路金融街还依稀留着当年的风貌。不过,这个城市的气质、氛围和上海却大不一样。上海是洋场文化,按照天津作家林希先生的说法,天津是码头文化,比较市井,没那么精致。一个拉洋车的工人,今天要是有个煎饼果子吃,就决不会出工。煎饼果子边走边吃,上海排骨年糕坐下来品。
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检查人的孙曜东曾经回忆那个年代上海银行家们的生活方式:交往盐商、讲究吃喝,甚至吃出八大菜系,连狮子头都分剁出来的和切出来的,剁的不如切的好吃;和政界来往密切,1941年甚至发生长达数周的军统和76号银行界大血案;和黑道也有交道,银行的人被抓了,总裁还要指望杜月笙去摆平,因为他和戴笠关系非同一般。
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资耀华一家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生活很简单:家里的房子是向“北四行”租的,所以租金便宜,是英租界五大道成都道上的一栋假三层小楼,“也就是鲁迅故居那样的格局”。身为银行家,但是他从来不理私财,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闻不问,他去世的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他很少在家吃饭,应酬特别多,但他不是美食家,根本不挑食。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碟,辣椒酱加豆豉和大蒜,所有东西都蘸这个吃。他更不是一个政客,结婚的时候妻子曾经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绝不做官。
虽然不碰政治,但是作为银行家,要吸纳存款、业务往来,必须面对人脉问题。何况,当年的天津是个非常复杂的码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旧的北洋系不存在了,这时候,它的经济、教育都快速发展。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军阀、前清官僚、八旗子弟、南方移民纷纷在天津设厂办工业,要么就在英租界、现在的五大道附近买房子。整个天津三教九流,成了北京的后花园,按照冯承柏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始终笼罩在首都阴影下的城市”。
资耀华的办法是参加青年会、联青社这样的团体——很多成员都是厂长、经理。另外,他还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留美学生。对于当年的这个交际圈子,资中筠仍然很有印象:“父亲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只和我父亲有业务上的来往,场面上的朋友,另外一种是能够跟家里头也来往的。对这种朋友,我母亲有自己的选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有书卷气的人家。当时这些家庭,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交际圈子,大家平时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一定上门拜访。”
圈子里的企业家很多。宋斐卿,东亚毛纺厂厂长,生产的抵羊牌毛线能够和英国的蜜蜂牌毛线竞争。他的工厂和上海银行有业务往来,资耀华也有工厂的一些股份,每年年终,资家都会收到很多抵羊牌毛线。朱纪圣,仁力地毯厂厂长,美国留学生,他和资耀华一样,都是仁社成员。他的女儿比资中筠大两岁、高一班,是耀华中学同学,跟着同一个老师学钢琴,特别要好。化学工业大亨范旭东则是资耀华当时最好的朋友,两家人经常来往,上海银行也曾为永利碱厂发放贷款。
一代人的事业和痛
在上海的银行界人士沈建中看来,资耀华是很能够代表那一代华人银行家的气质、风度和成就的——在很多方面,他们能够“开风气之先”。
当然,这些都是资耀华百年之后,他阅读资氏的回忆录和著作的心得。在更早的那些年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资耀华为何人。几年前,沈建中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个说法:“我国征信业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话叫他很不平,也不以为然,因为“早在三十年代,上海就有征信所,而资耀华正是发起人和主要创办者”。当时,各家银行鉴于历来相互保密,不利于防范风险,合资建立了征信机构。资氏便是最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还操办了研究刊物《金融经济情况简报》。沈建中后来这样评价这个机构的意义:“……足见征信所之开支不为无益,从前外人对华人极为轻视,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资耀华在一生70年的银行金融生涯中,都特别注重对信息的搜集处理。甚至到了晚年,他惟一的业余爱好还是看大量的报纸杂志。这一点,从他一开始进入银行界,担任上海银行调查部主任的时候就开始了。按照孙曜东的回忆,这实际上是个经济调查部门,是陈光甫的“脑外之脑”:一方面调查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行情等;一方面搜集上海一些巨富商户如荣家、刘家、郭家的资料,在还没有与他们发生业务往来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管理办法,甚至领导人的个人性格。
一个活到了1996年的老银行家,却成为一个只能被后人从纸上认识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女儿。资中筠承认,自己到2005年负责重新编辑出版父亲的自传《世纪足音》时才真正用心仔细阅读。结果,从这本书里,她重新了解了那个沉默、严肃、忙碌的父亲,发现原来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人。
比如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资耀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考察,正好赶上罗斯福在位,他马上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除了学习之外,他专门考察罗斯福新政是怎么回事。“当时刚好是美国经济衰退后刚刚复苏的节骨眼上,他正好在现场,就没放过这个机会,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回来。作为一个学者,要是我早知道他这些,我可以向他学习很多东西。”身为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感到非常惋惜。
再比如说,抗战胜利之后,日本刚刚投降,资耀华作为华北金融界代表被请到重庆访问。资中筠对于父亲这次经历的记忆是:“我只记得他回来以后失望得不得了,大病一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带回来十万法币现钞。”这两大箱子现款,后来发挥了巨大的效用。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还没有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也还没有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如果能够在这个短暂时期用好这笔现款,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
“当时法币短缺,只是非常短时期的现象,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安排的当与不当,结果大相径庭。父亲此举显示了他的非凡的敏锐,为后世银行家们如何争取时间上的优势及产品上面的优势,上了生动的一课,体现了他在关键时刻的智慧和魄力。”资中筠说。
最令资中筠惊讶的恐怕还是父亲当年的交际圈子。在她儿时的印象当中,父亲是个晚上9点以前必定回家的人,家里常常串门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几个人家,几乎没有做官的,更谈不上权贵了。可是在父亲的回忆录里,她发现父亲原来和那么多达官贵人都是同学、熟人、老朋友,甚至是他的晚辈: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有壬、熊希龄、张公权、荣毅仁……比较有意思的是董浩云。上世纪四十年代,资耀华去美国哈佛大学考察的时候和董浩云同船同房间,当时董浩云劝他买船——战争刚刚结束,大量军舰要退役贱卖,董浩云作为一个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和巨大利益。资耀华说我没钱,董又劝:那让银行出钱买。资又回答说:我没权决定,需要董事会通过。
事实上,资耀华作为“军师”追随陈光甫数十年,一直到解放以后,陈身在香港的时候才被任命为上海银行总经理。这被认为是和他的实力相符的职位。沈建中从银行界老人那里打听到的说法则是:陈虽然爱才,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但是他重用在身边的都是相对“听话”的平庸之才。
1949年以后,资耀华带头建议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来银行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资耀华担任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他个人率先放弃了自己的定息。在从天津调到北京任职时,大批的书籍捐给了天津图书馆,家中稍值钱的也都捐了。他的妻子说他是“交公有瘾”。
资中筠分析说:“我觉得他解放以后有一个想法:一切的包袱都在于有产。他本来就不追求财富,现在财富成了一种罪恶,他就更不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他在解放初期特别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这不是主义不主义的问题。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对于新政权寄予的希望很大。”
这种希望是什么时候归于沉默的,已经并不重要了。但是沉默的对面并不是资耀华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父亲一生遭遇最大的挫折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对于他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如此。”
这一代人的机遇本来是非常好的,比如资耀华,一个湖南大山里的小孩,有机会留学,吸收海外最先进的东西,回国以后又能学以致用,对本土情况作深入调查,又遇上一个能用他的陈光甫。他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上海银行的会议纪要里,有他精心编制的五年纲要。他说,“经济很重要,治国齐家平天下都要靠经济。开工厂、做生意也要经济。中国现在就是缺乏经济。”可是日本人一来,他所有发展中国民营金融事业的想法都得搁浅。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资耀华在天津收到的总行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他所能做的只是守住上海银行的资产,在压制的情况下把损失减到最少。
资中筠记得,那是一家人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回家经常没有好脸色,有时候还拍桌子、摔东西,又一次发作的时候对女儿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将来一定不要干银行,什么人都要敷衍,简直不是人干的!”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以为又有了实现抱负的机会,可是又遭遇了第二次打击:他们想做的事业,宋子文都要插一手,官僚资本已经开始压制他们了。资耀华最好的朋友范旭东就死在1945年的重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这四人,分别是官方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资耀华的另一个好朋友卢作孚在重庆自杀身亡,这可能对他又是一个打击。不过他活到了最后,甚至只差一年半就能看到香港回归。他的晚年是这样的:他聋了,妻子盲了,他有时候从窗外的藤椅上站起来,塞给妻子一块饼干。就这样,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