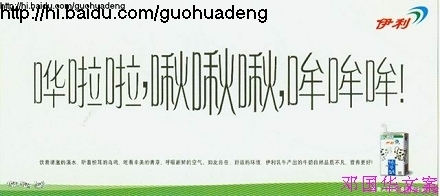刘爱国认为,郑俊怀案验证了“中国企业家们的一个大毛病——很多人都是出了事才想找顾问,没出事前他绝不想和你商量”
郑俊怀,伊利集团原董事长,2004年12月被捕。2005年12月31日,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入狱6年。2006年5月19日,内蒙古高院维持原判
2004年12月17日,唐万新被捕的当天,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等5名伊利高管被内蒙古检察院带走。12月19日,郑俊怀等被刑事拘留。该日下午,内蒙古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爱国接到一位操本地口音的妇女的电话。“是刘爱国吗?”“是。”“是律师吗?”“是。”“我是郑俊怀的爱人。老郑被拘留的时候留话给秘书,想请你做他的律师。”刘爱国回答“让我考虑考虑”,让她下午6点再打来。
6点整,电话铃响起。对方很着急,刘爱国说“行吧”。刘的朋友劝他,这案子“涉水太深”,最好不接。“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刘说。最后,按照朋友的建议,刘爱国找了一位北京的律师一起来做——他当年的战友李京生。见到郑俊怀后,刘爱国才知道郑听说过他曾代理的一个案子,对他有印象。
案子的关键
2005年1月8日,包头看守所。刘爱国和李京生第一次会见郑俊怀。会见室里,两个律师面朝打开的带铁栏杆的窗户站立,窗外则是被铐在栏杆上的郑俊怀。因为个子矮,郑铐着的手高高举起。这种方式并不是针对郑俊怀,而是该看守所的惯例。鉴于当时气温在零下20多度,刘爱国请在场的检察官允许郑进入会见室。

郑俊怀很激动,话语滔滔不绝。“他觉得自己很冤枉,说这个事当初是市里让我这么干的。”刘爱国对《中国企业家》说。这句话是郑俊怀以后与律师交谈甚至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主旋律。刘爱国说,1999年,牛根生等一批伊利骨干出走,为了保持管理层稳定,呼市政府希望能够把管理层持股作为激励手段,对此,市政府“提出过建议,也形成过决议”,并且这也是1999年至2003年呼市政府一贯的想法,2002年的启元公司即为其产物。“但是,”刘爱国对郑俊怀说,“市政府并没有针对立鑫公司(郑俊怀成立华世以购买其所持伊利股份)做批示,也没有说让你成立华世。不能用这一句话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住,别说检察官,从我这儿也说不过去。法律对你的行为怎么评价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人(郑俊怀)比较固执,”刘爱国对《中国企业家》说,“成功的企业家可能都这样。你说的时候他不说话,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一套。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跟他把案子的关键在什么地方说清楚。”
在刘爱国和李京生看来,“案子的关键”即郑俊怀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因而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按照刘爱国的说法,从一开始,有关“主体资格”的问题就存在:郑俊怀的拘留证上盖的是内蒙古公安厅的章,而按道理,如果郑涉嫌挪用公款,上面的章应该来自检察院反贪局。“这说明他们(检察院)当时也没准儿。”如果不是“挪用公款”而是“挪用资金”,郑的判决很可能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兼缓刑。
刘爱国说,很可能在检察院讯问时郑俊怀透露了这个于己有利的“关键”,于是有了检察院补充侦查之后由呼和浩特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出具的《郑俊怀同志有关情况说明》。在二审辩护时,律师指出:“一审判决引用地方党委文件中的‘提名推荐’和刑法所说的‘委派’不是一个概念。提名推荐是建议性的、参考性的,对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而委派是到委任、派遣,是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直接任命某人到一个非国有单位,在授权的权限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根据刑法规定,委派者应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一审判决认定的进行提名推荐的党委不是法定的委派主体。”同时,刘爱国论证了从1999年开始,国有股在伊利公司既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也不处于相对控股地位,伊利公司不是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也不是国有相对控股企业,“尽管地方党委将伊利公司列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并对其领导人员进行管理,也无法改变伊利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的法律事实。”
二审期间,刘爱国等就郑俊怀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向最高人民法院去函求证。刘爱国说,最高院的答复是,因为没有看到全部证据,只能批转给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最好是自治区高院把全部案卷拿到最高院来请示。“这也等于解决了二审的同志们的后顾之忧,说公道话的时候不至于有什么负担:这是最高院的意思。”刘爱国说。但是,二审时自治区高院并未请示,而且刘爱国等希望的二审开庭审理也未能实现。“匆匆忙忙就判决了。虽然提倡二审开庭率达到多少多少,但是一个(案子)不开,你也不能说它违法。”
隐情
刘爱国说,2005年12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某公司找到郑俊怀,提出购买启元公司(伊利高管持股)的1000多万股伊利股票,保证交易完成可以让郑俊怀“出去”。“我一再告诫他,”刘爱国对《中国企业家》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的。案子已经提交到法院,正在审判过程当中,哪个领导说这个事免了就没事了?”刘爱国的建议是“什么都别签”。郑俊怀没有听。刘爱国说,签字的时候看守对郑俊怀说:“好像你上次跟你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么?”“就这么提醒他,他都不听。他认为就是花钱免灾。”刘爱国对《中国企业家》说。时值伊利“股权分置改革”,据刘说,那个公司的出价就是当初这些高管的实际出资,而且,“就连这个钱到现在也没给”。
刘爱国的律师费(20万元)目前也未拿到。刘说,出事后,郑俊怀的工资、奖金、分红都被冻结了;郑俊怀被收审后,呼市政府曾指示每月给郑的家属发放5000元生活费,几个月后亦被停止;郑的两个孩子在国外上学,学费是蒙牛的牛根生等人凑的。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郑俊怀向律师解释了当初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或者向私人借钱受让立鑫公司持有的伊利股票:购买立鑫公司转让的伊利股票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公司的控制权不旁落,用自己的钱(包括向私人借钱)买容易让人说闲话——后分给别人,人家会觉得这是你的东西,不好意思要。用公司的贷款买,股份就是大家的。“如果郑俊怀要借钱,”刘爱国对《中国企业家》说,“就像庭审的时候杨桂琴(伊利原副董事长)所说:别说郑总了,我作为伊利的副总,到哪儿借不来1500万?”
刘爱国认为郑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他差就差在操作上。你先开个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将来谁否认都不行。没有决议也要有个纪要,纪要没有记录总得有。他就没考虑这个。”当时伊利公司聘有证券方面的律师,同时还有法律事务所(属于企业法律事务所试点),但郑俊怀没有找他们商量。“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大毛病。很多人都是出了事才找顾问,没出事以前他绝不跟你商量。”类似的意见可以在李经纬的辩护律师邱代伦那里听到:“李经纬就是一个买保险的问题,(当初)开个董事会就行了,到时候把记录找出来就没事了。法律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个手续问题,该履行的手续一定要履行完毕。”
刘爱国称自己曾经经手9个经济犯罪案件,做的都是无罪辩护,其中8个辩护成功。当他接手郑俊怀案时,一度认为希望比较大。“即使一审不行,二审也能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估计错误,我没想到干预这么深。我觉得老郑这个人,对呼市这么大贡献,犯了法,没说的,否则大部分领导应该巴不得我做无罪辩护。没想到有些东西咱们法院的同志也顶不住。”刘爱国说,这个案子“非常奇怪”:“我们并没有查阅这个案子的所有案卷。我们知道这个材料到了检察院,我们申请调取,只有一份调过来了,其他一概没有给我们。到伊利公司去查,也拿不到。”在二审辩护词中,刘爱国和李京生写道:“在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后,上诉人的辩护律师曾就收集、调取证据一事向一审法院正式提出书面申请;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也就调取证据一事向法庭提出正式书面申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仅对于上诉人的申请置若罔闻,就连上诉人的辩护律师当庭提交的证据在判决书中也只字不提。不仅如此……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将案件的主要证据和全部证据目录移交给一审法院,甚至连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也没有移交,而一审法院对此却视而不见。”
与流传的“未以金信信托一事起诉郑俊怀体现了当地政府对他的宽大”说法不同,刘爱国说,事实上郑俊怀出事前半年,证监会一直在查此事,最后没有结果。在刘看来,郑俊怀在位期间,“不会看人眼色行事”,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对政府的一些活动赞助不甚积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张。
郑俊怀入狱后,刘爱国去见过他,较之审判前,郑变得“很平静了”,只是“至今也对这个判决不服气”。不知道他有时会不会想起自己在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的情景。庭审前,刘爱国曾叮嘱他说几个要点:搞华世公司不是为了个人;如果是为了个人,我就不会用公司贷款;简单回顾一下过去,直到今天,问心无愧。“这么大的企业家,到时候有点儿风度。”刘嘱咐郑。“没想到他一说到第三点,越说越激动,带着哭腔,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我就注视着他,这时候我(心里)说打住吧。最后他看见我了,结束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