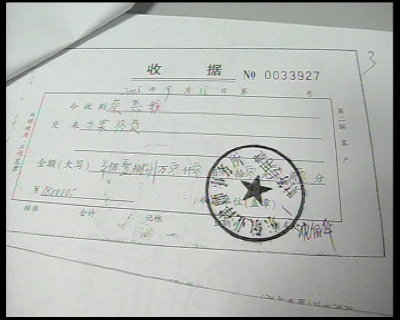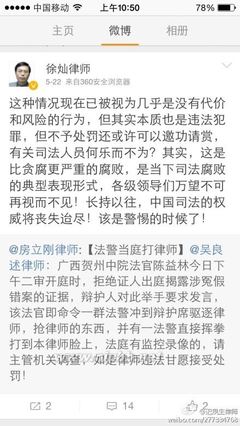“现阶段,中国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有一个特点,舍命不舍财。这有时是导致其落难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
杨斌,欧亚实业原董事长,2002年10月被捕。2003年7月14日,因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入狱18年。2003年9月7日,辽宁省高院维持原判
杨斌案
2003年5月,杨斌案开庭前一个多月,田文昌接受了他的委托。此前的半年时间里,欧亚实业的人及其说项者不断地被田婉拒。
田不愿意接的原因是案子“敏感”。2002年,因为代理刘涌案,田文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人家以为我尽找敏感案子做,实际上很多都是不小心陷进去了。全国各地太多的敏感案子都从我手里过过,很多都是我不接才转到别处去的。刘涌案也是接了以后才知道这么麻烦。”
杨斌方面的努力有了结果,时距刘涌一审被判死刑刚好一年。田不愿意透露该案律师费的具体数目,但表示与外界盛传的“160万”相去甚远。
这一次田仍然低估了案件的敏感程度。时值“非典”(其时孙大午的辩护律师许志永和张星水即将赴徐水艰难地取证),田文昌及其同事进驻荷兰村。很快,田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里,且“一两天换一个酒店”,以避开“上百个中外记者的围追堵截”。
杨斌给田文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接触的企业家里,没几个比得上杨斌。”因为“非典”,田与杨的见面都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看守所位于辽宁本溪,楼房很破旧,而关押杨斌的房间装修得很漂亮,因为荷兰使馆的人要来看他。
田曾多次会见过杨斌,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杨斌烟瘾极大,田文昌清楚记得他曾一连抽掉四包香烟,而完成这件罕见的事杨斌只需要点一次火。后来,杨斌向田文昌提出要在法庭上抽烟,理由是自己有病,不抽烟“可能导致庭审进行不下去”。“我知道肯定不能准许,”田文昌说,“但是还得转达啊。”
这件事或许能印证杨斌留给田文昌的印象之一:很自信。在田文昌眼里,杨斌“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煽动力极强”。田对杨的总体评价是:一个缺陷型天才。“他有时候像个小孩儿,一笑,傻乎乎的,甚至在法庭上也如此。”据说,看守所新关进来一个16岁的小伙子,杨斌与之龃龉,继而相搏,把小伙子揍了一顿。其时杨斌40岁。
杨斌被指控的罪名之一是虚假出资。一审法庭辨论中,田文昌指出,“在控方所举出的证据当中,并没有可以反映被告投入资金的总额与注册资金总额之间差额的数字。荷兰村项目的资金含量是有目共睹的、人所共知的,这些项目资金从何而来?投入的总量是多少?大家记得在法庭调查中我问过杨斌,大家都听到了杨斌的回答。按照他的说法,他投入资金的总量,远远大于注册资金。现在我没有调查,我没有充分的条件去详细调查这些数字,但是我至少可以提出来,控方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杨斌投入的资金总量小于他的注册资金总量。荷兰村项目当时的评估值是三十几亿人民币,那么,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他是虚假出资?”
法院的判决采纳了田文昌的辩护意见,没有认定对杨斌虚假出资罪的指控,但改变为“虚报注册资本罪”。在二审中,田文昌对此提出异议:从形式上看,虽然不能否定公司在注册时确有不实的成份,但“实际在荷兰村运营的资金超过了7个亿”,即“实际注入的资金额大于注册资金的金额”,这一事实说明被告没有虚报的必要性,因而也没有“虚报的主观故意”。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司项目运营良好,这种注册行为并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相反,却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的东北方拔地而起。”
“设立注册资本金制度本来是为了打击皮包公司,保护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的规定也有副作用。”田文昌说,“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情况,而受到追究的并非多数。可以借鉴国外用破产来控制企业,破产一次就很难抬头了。”
杨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从该案证人的身份及证词中可见一斑,能够“占用”上千亩农地与此有关。“当然,”田文昌在辩护词中写道:“这并不表明辩护人认为这种做法合法,但是,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做法是有原因的,不应该构成刑事违法。”
田文昌认为自己充分地表达了辩护意见,法庭效果很好,尽到了辩护人的职责。2003年9月7日,杨斌被二审判决入狱18年。判决后,田与杨见过一面,杨对田的辩护表示满意。“就是声音太小。”杨斌说。“开玩笑,”田文昌对《中国企业家》说,“我跟人吵架啊?我是在跟人讲道理。心平气和地探讨是我的风格,但当事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杨斌案二审之前20天,刘涌由死刑改判为死缓。4个月后,刘涌再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怎么看企业家
1992年,河北承德企业家商禄被指控贪污诈骗判处18年有期徒刑,田文昌为其作无罪辩护成功;1993年,黑龙江企业承包人朱佩金被控巨额贪污诈骗行贿,田文昌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朱无罪释放。其时田文昌代理大邱庄被害人家属控告禹作敏已是第三年,禹被判刑入狱,田文昌虽然没有出庭,但功不可没。

田文昌因此名声鹊起。“这都是别人不愿意啃的硬骨头。”田文昌说。当年商禄已经60多岁,财力和精力都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田鼓励他一定要打下去:“你不打我帮你打。”“案子做到一定程度,什么利益呀,风险呀,名声啊,都忘了,只剩下一个信念: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这才能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比当事人还投入。”
商禄和朱佩金都是遭人陷害,时至今日,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田为此并不认为中国企业家所处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善。“20几年来,我们的法制环境、司法水平有提高,但离我们希望的公正化水平还差得远。”
尽管为企业家辩护给田文昌带来了名声,田对企业家阶层也十分关注,但他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阶层中的某些人。“我是学者,跟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我接触到的企业家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谈话,常常让我有一种以实对虚的感觉,而对方却视我的实在为呆气。”商禄留给田的印象比较好,但已经去世了。“突然案件昭雪了,却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一直没起来。”
“现阶段,中国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有一个特点,舍命不舍财。这有时是导致其落难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被拘捕前,顾雏军曾三次到京都律师事务所找田文昌,希望田能够到证监会为之缓颊。“他想得很天真。当时调查已近尾声,别说我不是官员,我就是官员也做不到。”田劝顾雏军破财免灾,勇于放弃经济利益,尽快通过重组来缓解形势,但是顾未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隆身上。田曾向其高层建议加快重组挽回影响,未果。唐万新被捕后,唐万里来到事务所,欲聘田文昌为辩护律师。田文昌跟唐万里讲,这个事还是要综合处理,要跟重组结合,重组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犯罪责任的承担。“假如不通过重组及时挽回影响,单纯的辩护作用就会小得多。”此事再无下文。
“不舍财”当然也包括律师费。很多人舍不得花钱请律师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结果“一旦出事往往人财两空甚至招致灭顶之灾”。“也不仅仅是律师费,”田文昌说,“比如一些债务,能还的赶紧还了,一些该舍的利益要勇于舍弃,也能相应地减轻责任。不到最后一刻他们都舍不得。我试图说服这些人,很少有成功的。”
企业家不懂法律,但有些人却自信到固执的程度,田文昌十几年前就有体会。当时他曾劝说一些南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家通过产权界定明确企业性质:“在集体所有制的概念里,没有具体的财产关系体现,死后又不能继承,所有权关系是模糊的,在经营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侵占的嫌疑。如果明确产权,哪怕90%贡献给社会,只剩下10%是明确属于你个人的,也是一种名正言顺的所有权,可以避免后患。”被劝说者往往指着挂在墙上的与领导人的合影笑田多虑。“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固执而出事,”田文昌说,“一旦出了事,什么照片都不管用。”
田文昌最难容忍的是某些企业家在看守所里还指挥律师。“有的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又没有信息,还自以为高明地指挥律师干这干那,不能逆着他。”遇此情况,如果不能说服当事人改变态度,田文昌就会与之解除委托关系。田常常告诫律师,盲目遵从就是害你的当事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