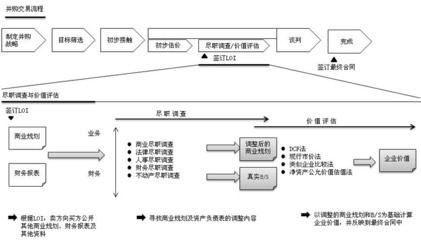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企业家阶层长期面临的商业压力。这两起极端的案例是企业家阶层经受沉重压力的一个残酷写照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2005年元月1日,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从四层楼跳下死亡,年仅52岁;时隔两天,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金花股份(600080)副董事长徐凯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杀,终年56岁。
就在我们的相关调查结束之际,又传出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于1月13日跳楼自杀。因为消息封锁甚严,所以未能及时见报。而1月3日《运城日报》对赵恩龙自杀的解释是“因晨练不慎发生意外”。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 “1980年以来中国约有1200位企业家自杀”的说法——与其他身份的自杀者一样,这是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忽略的一群人。
1993年3月9日,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方宏跳楼自杀;同年,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割腕弃世;1997年7月28日,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举枪自尽;2003年9月7日,黄河集团老总乔金岭上吊身亡……
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一书探讨了自杀。他指出,人类的处境就像西绪福斯一样,不停地把巨石推到山顶,看着它滚下去,然后重新来过,周而复始。尽管生活有时候的确“不值得再经历下去”或者无法再继续,加缪还是对西绪福斯式的生存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赞扬。现实问题是,哲学并不能或者并不完全能阻止人类的自杀。
年仅29岁的冯永明在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他所恐惧或者厌恶的生存状况是他所在的阶层时刻都要面对的。无须专家指点,我们轻易可以想象,为什么企业家们比普通人更焦虑。
冯永明的遗书可以解释赵恩龙的死。而所患疾病(抑郁症)与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方宏相同的徐凯证明,此种疾病导致自杀并非鲜见。
为什么企业家会觉得看似成功的生活“不值得再经历”?以下两个个案能给出的也只是两个答案。今人悲观的是,即使他们能够复生,我们是不是已经找到说服他们放弃自杀的理由?
徐凯
那个近于封闭的世界
变化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今年元月1号或3号我记不清了,我在端立门门口拉了一个客人,当时身穿黑色风衣,内穿一套黑蓝色西装,浅色衬衣,有领带,好像背了一个包。他上车后坐在我的后面。他自称是金花企业集团的副总,有上亿资产,在枫叶园有一套别墅。他说在感情上得不到真爱,在他身边的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他由于工作的原因住在宾馆,感到很孤独,没有意思。”
这位西安市李姓女出租车司机运载的客人就是徐凯。李姓司机在1月13日写给金花集团的说明(字迹歪扭、别字多)中记述了这次偶遇。徐凯与李姓司机谈到了自杀的方式,“跳楼、跳河、上吊”,司机说“都不好”。“你不相信我,过几天你在报纸上都会看到。”徐凯说。
1月8日晚,李姓司机打开报纸,看到了徐凯已于几天前自杀的消息。
从端立门到徐凯下车的南新街如果不堵车,只有3、4分钟车程。如果不是内心世界某种程度的崩溃,一个集团公司的副总、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毫无保留地倾述吗?
1月4日下午5时许,正在福建与家人度假的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从电话里听到了这个让他震惊的消息。2004年12月10日,吴一坚的生日,徐凯还发来信息表示祝福。徐凯的生日是12月12日,所以当时未在西安的吴一坚嘱咐集团总工张培合(徐多年的朋友)给徐“过过生日”。事实上,张培合已经提前三天跟徐凯预约了过生日的事。“进入2004年以来,他对这些约请没了兴趣,所以我提前三天约好他,约的其他人也都是一些好朋友。”张培合与徐凯相交16年,他进入金花集团就是徐凯推荐的。
在当天的生日宴会上,徐凯表现出近来常见的精神恍惚:发呆,注意力不集中,对别人的祝贺、敬酒视而不见。
2004年10月,徐凯从广州回到西安,这是吴一坚与徐凯最后一次见面。“他变化很大,老是那种非常恍惚的状态。”吴一坚说。他与徐凯一起共事20多年,徐凯自杀后,吴曾对徐的前一任妻子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你们还长。”但是2004年非常忙,徐凯在广州基本不管理公司事务,吴徐二人“交流就非常少了”。而实际上,徐凯是吴一坚岳父的朋友,比吴“大了一辈儿”,二人在一起时也很少谈到家庭、情感等话题。
吴一坚说,以前的徐凯非常能说,“天南地北”,某次在公司早上升旗时讲话,由于时间过长,致使某女员工当场昏倒(长时间站立且未吃早饭)。2004年后,徐凯“完全变了一个人”。张培合对徐的评价是“口才好”,且学识渊博,喜欢历史,对红军长征中的大小战役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能从中东讲到欧洲,再讲到非洲”,“朋友有什么重大场合(比如子女结婚之类)都要请他去致辞”。
张培合说,2004年以来,徐凯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动辄唉声叹气,不习惯说话,“封闭自己”。
疾病
吴一坚与张培合都证实,徐凯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张培合与徐凯出差,徐要起夜多次,弄得张也休息不好,“都不敢跟他一起住”。“而且他还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张培合说,“参加一个宴会,徐要多次上厕所,但又尿不出来,疼,非常痛苦”。徐曾对张说:”他的腿也抽筋,疼得受不了”。徐凯还患有高血压,张的描述是:“血压一高眼睛都睁不开。”
2004年12月24日,徐凯住进医院。吴一坚让集团办公室主任给徐凯提供尽量好的医疗条件。“当时他住的病房非常大,他还不愿意,跟大夫说要是有小一点的就换掉吧,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吴一坚说,当时一天的病房费用大概是500多元。据此,吴说:“徐总对公司还是很有感情的。”
12月31日,徐凯的病情报告出来。除了已知的高血压、前列腺炎,还查出糖尿病Ⅱ型、乙型肝炎和严重的抑郁症等。张培合说,出于对徐凯的关怀,医生对他隐瞒了抑郁症。
“他当时就哭了。”张培合说,与徐凯相交16年,他从来没见过徐凯流眼泪。当时几个朋友劝了两个小时徐凯才安静下来。“一个人有一种病就很可怕了,何况得五六种?他有一个朋友就是糖尿病Ⅱ型,要不断注射胰岛素,他知道那很痛苦。这些病对一个男人的生理功能损害也很大。”张培合还分析说,徐凯肯定也想到了社会上对乙型肝炎的歧视。“很多人都说这么有钱怎么还自杀?他们不知道有的病是钱治不了的,病人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
张培合说,徐凯平时爱面子,很多话都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包括朋友说。在临终前对出租汽车司机的告白中,徐没有提到自己的疾病,“爱面子”当是原因一种。
酒店生涯和抑郁症
“抑郁症”,指着公司刚下发的《保健知识讲座》(抑郁症专题),张培合说,“徐总完全符合这上面描述的症状。”在《讲座》里,谈到抑郁症的表现为“情绪低落、目光呆滞、思维联想缓慢、应答迟钝”等。而造成徐凯抑郁症的原因不止是多种疾病。
10多年来,徐凯大多时间都住在酒店里。
徐凯生前结过三次婚,但是连吴一坚、张培合都不知道徐的第一次婚姻。出现在徐凯追悼会上的吴的第一任妻子及其儿子甚至孙子,让吴、张等人感到惊讶。
徐的最后一任妻子与徐一起生活的时间最短,前后不过一年。“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张培合说,“一个48年(生)的,一个76年的,沟通上肯定有障碍。”
吴一坚说,徐凯的朋友看似很多,但真正能深谈的很少。“而对朋友,他又不愿意说自己的痛苦。”张培合说。2004年12月31日,金花集团员工联欢,吴一坚曾想着跟徐凯聚聚,“好好谈一谈”,但是最终被事情岔开。
长年的酒店生涯中,徐凯的私生活多次受到非议。吴一坚时有耳闻,也曾打电话委婉地劝说徐凯。“但我们毕竟不是一代人,有些话也不太好说。”
“一个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就怕孤独,”张培合说,“人不怕没钱、没车没房子,就怕孤独。孤独就恐惧,就空虚。他长年住酒店,没有家的概念,晚上就希望我们陪他出去,吃个饭,喝个茶,聊一聊。”进入2004年,一向主动给张培合打电话的徐凯再无此举,而且别人也很难再约请到他。
或者,徐凯未对出租车司机讲述自己的病情,还因为疾病对他的打击不如孤独严重。
“2004年10月徐总回到西安后,跟第二任妻子处得还挺好。但是后来她又把他告上了法庭。”吴一坚回忆说。第二任妻子的诉讼起因是“徐凯与之离婚时隐瞒了在金花集团的20%股份”。
徐凯没有留下遗书。“这也符合抑郁症的特点,”张培合说,“他哪里还能想得到写遗书呢?”
对于徐凯的股份,金花集团的态度是,愿意把它留在公司和要求公司回购都可以,但要由律师出面签署一个协议。吴一坚说,目前家属对于股份的分配不能达成一致。这种情形,徐凯生前可能已经无暇想及。
赵恩龙:“他太可怜了”
债主临门,工厂被法院查封,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因赵恩龙的离去划上了句号。
1995年,赵恩龙的生意兴隆,为故去的父母重立了墓碑,规格在村里当属很高。如今,他就埋在父母墓边,大大的一堆黄土,几只变了色的香蕉,没有碑,一挂纸幡在冬天的风中摇动。
赵墓所在的山西闻喜阳隅乡东杜村距西安四个多小时车程,但赵恩龙自杀引起的风波远比徐凯严重,其公司高层没有人愿意出面再谈论此事。按照鑫龙公司领导通讯录的电话号码反复拨打,始终都是无人接听。鑫龙公司负责地产的领导解志刚(原工商银行运城分行副行长)未等记者说明来意即挂断电话,再不接听,其办公所在地已人去楼空。晚间,有一人回了电话:“一天打鑫龙公司的电话干什么?”记者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领导,只得猜测。“你怎么知道我姓柴?我们公司没有问题,具体情况163(网易)网上都有。”他可能是柴福星,赵恩龙的姐夫。但网易关于赵恩龙的报道都显示鑫龙集团出了大问题。
尽管同在运城,又同是闻喜人,但是比起2003年遭枪杀的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赵恩龙在运城的名气要小得多。尽管如此,赵也还是当地的“名人”。“欠钱跳楼的那个?也不知道他是有钱还是没钱,”运城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说,“人家都是钱塌(亏欠)得越多越不怕,欠银行的钱谁自杀呢?”
司机的话与此前媒体的说法相仿:赵恩龙不仅欠银行的钱,而且还以个人名义向亲朋好友借款甚多,当地警方透露说,赵恩龙对朋友很义气,但他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无法面对自己的朋友,生活圈没有了,这是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立于1998年的鑫龙公司在短短几年间即成为“跨行业、跨区域、多品种的科、工、贸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涉及生物、医药、地产、金属、旅游等行业。2004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鑫龙集团涉及电解铝和房地产两大行业,全部触到了国家紧缩银根的风头之上,其贷款总额已超过其总资产。据公开报道,赵恩龙自杀后,鑫龙集团以及下属公司已涉及债务诉讼11起,涉案标的超过两个亿。其中最大的一笔诉讼原告方为某银行,涉案标的1.8亿元。
赵生前曾与某银行达成一项口头协议:赵先筹措资金归还一部分贷款,然后银行结算后再向赵发放。结果赵筹来的钱一去无回。
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对银行的信用怀疑已久(他本人曾在徐水农业银行任职,负责信贷)。“那时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孙说,“实际上也不是具体哪个人失信,是上面不让再贷,具体办事的做不了主。” 赵恩龙是从印刷厂、火锅城起步的,他死后,很多人对他管理大型集团的能力表示了怀疑。运城市政府一位官员说,赵恩龙远没有李海仓的魄力和能力。孙大午也对赵恩龙的企业状态有疑问:“他做那么大是为了什么呢?是谁让他做那么大的?最早是谁把钱贷给他的?这都是问题。”据悉,分别为鑫龙集团提供贷款担保的企业多达五六家。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女士对赵恩龙的自杀也表示不解:“他可以申请破产啊。但是不知道他的资产是不是都已经抵押出去了。”
“他是个好人。”东杜村一位“看着赵恩龙长大的”老人说:“这娃娃从小就面善,发了财给村里铺了油(沥青)路,给学校捐了款。前年‘非典’还给村里拉回来一车药。”老人说,村里人有了难处到城里去找赵恩龙,“没有空着手回来的。”
“他太可怜了。”赵恩龙“三七”刚过,提起往事,他的姐姐赵金凤忍不住又泪流满面。“他对谁都好,东郭先生。”赵金凤回忆,赵恩龙当年初中毕业就去了建筑公司,后来调到运城建委,期间上了四年电大。赵“不爱当官”,并为此曾被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认为当官受拘束,贵贱不当。”赵金凤说。她的说法得到了运城市政府一位官员的证实:赵与运城市工商联、政协没有什么联系,可能是“对官场看清了”。赵恩龙给赵金凤留下的印象是“太累了”,经常“没白没黑”地工作。“地地道道一个好人,没人说他的坏话。平时温温柔柔的,一般不暴躁。他常说做生意难用人难。现在人思想意识不好,不管老板死活,不能有难同当。实际上他心里也有气,(自杀)也是气的。”赵恩龙不经常回东杜村,2004年清明节回村里给父母上坟,曾对赵金凤感叹“人不好用”。赵金凤说,自杀前几天,赵恩龙曾把柴福星(赵金凤的丈夫)叫去,递给他一根烟,说:“你先回去种你的地,过两天我也回去。”“他(柴福星)没听懂是啥意思。”
赵金凤也不知道,赵恩龙所谓的“不好用”的人是企业里的还是在企业之外。她只知道,“他太难了”。赵金凤说,赵恩龙看重人情,但是在集团安置人,自己人都不给权力。而据媒体报道,鑫龙集团高层很多都来自政府、金融机构等部门。
“这(自杀)是负责任的做法。”孙大午评论说。“他真不该走这步路,”赵金凤说,“好像他一命能帮多少人。”
赵恩龙的遗像摆在赵金凤隔壁的房子里,看上去严肃甚至有些冷漠。屋子里冷冷清清,除了供桌别无它物,与村头的那座坟茔一样,都显示出匆忙甚至草率。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帮”了自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