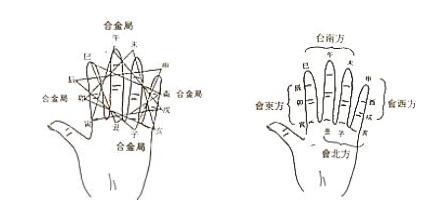这一轮的重型化是不是“有点走了岔路”?是不是“片面重型化”?在民间企业的重型化企图已经在宏观调控中遭遇重挫的时候,一场关于重型化的争论突然出现。这一回,争论的主角是中国两位教父级的学者吴敬琏和厉以宁——但凡劳动这两位泰斗学者共同发言的政经问题,必定是个大问题。
这个讨论,似乎来晚了一点。中国企业大规模的重型化,在三四年前萌芽,在两年多前启动,在一年前嘎然遇挫。2004年2月《中国企业家》推出“民企重型化”封面报道时(顺便说一句,“重型化”这个名词经本刊“发明”,逐渐成为通用说法),企业家们对“由轻到重”的产业升级路线深信不疑,对“在中国为全球生产”的产业大转移趋势深信不疑,对进入钢铁、铝业、化工、汽车这些非命脉行业的准入壁垒的坚固性半信半疑——那个时候,好像只有他们所要进入行业的商业对手在低调动员政府力量,学术界并没有怎么关注。等到政府调控措施横空出世,学术界也只是在讨论经济是否过热、用什么样的方式调控更好,几乎没有涉及到重型化。现在,2005 年初,调控措施已见成效,重型化冲动得到遏止,重型化企业个个鼻青脸肿,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是商业问题的问题,又被作为事关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呢?
显然,这场讨论的参与者都不认为重型化仅仅是个商业问题和企业行为。它关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向,关乎一些高深经济理论的真假,所以值得提醒和警惕。
尽管晚了点,尽管针对的是政府,相信企业界还是非常欢迎这样的讨论的。“谁能告诉我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钢铁?世界到底需要多少钢铁?”复星集团郭广昌在2004年底的发问,代表着企业界一种普遍的迷茫和不甘。从刚刚公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看,现在连军工、金融这样更加命脉的行业都对民间资本公开准入了,那些去年在钢铁、铝业、汽车上因准入遇挫的民间企业,岂不更加“意难平”?
2005年初,带着企业界的迷茫,《中国企业家》派记者到韩国,探访那里的重型化先行者。在韩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协助下,我们广泛拜访了韩国重工企业、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发现:
一、重型化是韩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依然列于世界第十二大经济体的重要原因。韩国学界认为,是韩国的钢铁、电力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后来全球领先的造船、汽车和重化工业,“你的笑容背后有我们坚强支撑”,浦项制铁的这句宣传词,形象地反应了重型化对韩国的重要;

二、韩国工业“由轻到重”的成功的重型化过程,是在政府强有力的策划、支持、推动下完成的。连企业界也承认,由于涉及资金、土地、外贸等宏观资源,假如没有政府的鼓励支持,企业很难靠自己力量实现重型化;
三、重型化伴随民营化,重型化主要由民间企业承担,并且不断升级。70年代第一次重型化时主要是政府支持现代、大宇等民间企业实现的,在金融危机后,少数几家国有重工企业全部民营化,在民营化过程中实现第二次重型化。如,浦项制铁与国际资本对接、韩国电力卖给了民企斗山集团。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2001年前后由民企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重型化,实际上也是“民营化的第二次重型化”,中央政府对这一轮重型化起初基本是被动的、后来是不认同的。与5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重型化不同,中央政府并没有事先预料到、也就没有主动规划过这一轮重型化。实际上,由于20年国进民退的整体经济改革,中央政府对工业包括重工业领域的投资,也已有心无力。目前困扰中国的电力紧张,与中央政府7年前停止对电力领域的投资有直接关系。
失去中央政府的规划力与引导力,的确就缺了事先的全局性讨论,但并不等于这一轮重型化就是盲目的,片面的,粗放的。这一轮重型化,到底有没有现实的需求?中国原有以国企为主的重工业,能否满足这样的需求?重型化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商业冲动?为什么江浙、广东发达地区重型化冲动更强烈?民营企业搞重型化,与国企比,是不是更粗放、低水平、高消耗?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讨论。
不过,这样的讨论,应该更多听取企业界的声音,应该多看看其他经济体走过的道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