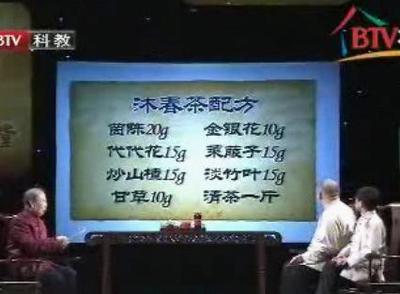他们家族的历史、个人的性格和城市的气质、命运胶着在一起,形成百年谋生立业的特殊体验和人生感悟,为我们触摸北京这个城市提供了官、商、民三个角度的个人切片
文/本刊见习记者 雷晓宇
所谓“老北京”,不是一个知识概念,而是一个人文概念。司马迁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这种悠久岁月在北京人身上沉淀下来的趣味、道德、礼俗、亲朋之道,甚至毛病和陋习,就是“老北京”,就是世家风范。
通过豆汁和糖葫芦感受到的北京只能是割裂的、片段的。北京的文化,首先在人,而不是物。这三位老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北京”,他们在北京的世家传承短的200多年,长的600年。他们就是所谓“留下来的人”,他们家族的历史、个人的性格和城市的气质、命运胶着在一起,形成百年谋生立业的特殊体验和人生感悟,为我们触摸北京这个城市提供了官、商、民三个角度的个人切片。
马旭初:600年世家胜景和大孤独
马旭初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说:“这是我初中的时候。你看,脸庞儿也不发愁,长得还凑合吧?”
照片上的少年是北京兴隆木厂的马二少爷、营造马家第14代传人。他头发梳得光亮整齐,西装笔挺贴身,对着镜头微微笑着。这个时候,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正是马家和马旭初的流年胜景。
马家的祖上叫马天禄,是河北深州的木匠。永乐年间兴建北京城,从此就在帝都扎根了。马家干木匠活代代相传,到了马旭初的祖父马辉堂这一代,已经是京城的木厂营造大家。当时北京从事古建的八大柜八大木匠铺子,都是马家的,其中最大的就是兴隆木厂,专门修皇家园林,颐和园、故宫、北海、承德避暑山庄,北京这四大世界文明遗产,都是马家经手修起来的。“挣皇上家钱挣了600年”,要说赔本买卖也做过,光绪年间就赔了20万两银子。那时候朝廷已经穷得连汉白玉栏杆都砌不起了。祖父一边冲着皇上的恩典把活干完,一边有自己的主意——“八国联军来了一挨打,我祖父想,得学洋玩意儿,大刀不管事,得洋枪洋炮。和《茶馆》里面写的一样,他也想办实业。”
马家显然比《茶馆》里的王利发成功多了。除了木厂生意之外,祖父马辉堂还拥有十几家企业,“以前前门大街全聚德往前的那一块全是马家的,得有百十好几家店”:木厂、自来水公司、有轨电车公司、药店、五金行、电灯公司、北京饭店……用马旭初的话说,就是“一般的买卖都有”。那时候马家有钱到什么程度?“什么数不知道,反正不愁吃不愁花。”马旭初当时年纪小,对钱还不上心。但是马家木厂的徒弟邓九安说了:“你知道马家有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从户部(就是现在的历史博物馆)用车拉银子,接连不断地拉到西四的柜上,得拉一天一夜。”

这么庞大的生意,马旭初说很简单,“靠的就是人治,要相信人”。祖父马辉堂“是个纯粹儒教加佛教的人”,治家治业,他都推崇言传身教。他为人朴素,一辈子穿布衣布鞋布袜子,一点不奢华;挣钱救济穷人,开粥厂开学校,舍棉衣舍棺材;他甚至雇了一个中国厨子和一个外国厨子,就是不让子女上外头吃饭,特别是租界里头,怕学坏。他没念过书,教育子女的都是一些朴素道理:有钱的是左手金右手银,没钱的是左手打狗饼右手打狗棒,人一辈子,两把指甲来,两把指甲走。
在马辉堂的坚持下,儿孙辈都上的洋学堂,成了知识分子,不再是手艺人。马旭初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建筑系,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也干了一辈子古建。现在有人劝他:“这些黄琉璃瓦基本上都是您家祖上修的,您把它保护起来,上对得起老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话没错,可是现在北京的古建保护叫老爷子生气:“这里任何一块砖头都比你年纪大,怎么能够胡来?让我做顾问,我是八百里寒路自带干粮自带水,别使车接我,我不摆那个谱,摆的是能耐,不是天桥的把式。我拄着拐棍还能走。谁也别跟着我。”
年轻的时候,马旭初曾经梦想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和太太一起去起士林那样的西餐厅,跳跳舞,听听爵士乐,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眼下,他82岁了,一个人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旧板楼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天像在蹲监狱”,这是马旭初不为人道的小寂寞。没能护下少年时候的那个老北京,这才是他的大孤独——自己祖宗修的房子一点一点变了样,“现在外地人来北京,下了飞机,得打一小时车来故宫,才知道自己是在北京。”
马延玉:故纸堆上坐
马延玉比马旭初小上十几岁,得管他叫叔。虽说同姓,又是世交,其实他们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马延玉是前清内务大臣绍英的孙子,说起来,以前马家还是给他们官家干活的。解放后,马延玉家从大宅子迁到小院子,又从小院子迁到马厩,马旭初来帮他们修整房子,就这么结下的交情。
马延玉现在有两套房子。一个是朝阳小街新鲜胡同的拆迁房,给了儿子和老伴。他自己在管庄花800块钱又租了一个一居室,平时一个人住这里,周末偶尔回市区一趟。
一走进他的房子,就闻到一股旧书的隐约霉味。房间里没法两个人并排走,要转身也费劲——全堆的是纸箱子,箱子里面都是文革之后马延玉领回来的宝贝:祖上的家谱和家书。粗粗一数,就得有20几个箱子,具体有多少,马延玉自己也不清楚。马延玉从北京摩托车厂退休以后,这些年就一直在鼓捣这些东西,整理资料,研究自己的家族历史。一本一本地看,一样一样地把玩,可东西实在是多,就算这样,也有好些箱子干脆就从没打开过,只知道是纸,不知道纸上写的什么。
马延玉打开抽屉,给记者看一个小信封:是启功先生去世时候的治丧讣告通知。再普通不过了,白信封,黑字印刷落款,圆珠笔的字。“我们和启功也能说上话,他的追悼会我也去参加了。他和我爷爷一样,也是个胆小的老头。”说完,他又翻箱倒柜地拿出一摞有些褪色的红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有四开大小,两个臂长——这是他祖父绍英1925年去世时张贴的讣告通知,里面光是逝者的职务名号就写了整整两开纸:光禄大夫、太保、前总管内务府大臣、高等实业学堂监督、钦差出使各国考查政治大臣……后面落款的子孙名号又是满满一张纸。和启功的讣告一比,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就是老舍所说的“北京人失落的排场”。
不过,讣告上并没有马延玉的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这辈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传说中的显赫祖父,电视剧《走向共和》开播的时候,还有同事给马延玉打电话:老马,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爷爷啦。马延玉就乐,那不是我爷爷,那是演员。
按马延玉的说法,这样东西是他怎么也不会拿去卖的宝贝。还有一样,就是庆亲王奕匡力当年和绍英家结亲的喜礼簿。整整一本,谁来过了,送了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有趣的是,当年的很多政敌也一起来道贺:贝勒和军阀、遗老和商号掌柜。“那不管,该做的应酬还是得做,”马延玉指着礼簿那一栏,笑着说:“你看,光茶叶就收了150包,十斤一包,就是1500斤茶叶,一辈子也喝不完。”
其实现在马延玉看着先人们的笔迹,多少也有隔着年头看戏的感觉。他和我们一样,对于那个大时代的奢华感到陌生和好奇,看的是个稀奇热闹,而不是沉默的往事。除了小时候被逼着学了一点国画和书法,他受的教育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不会说满文。马延玉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败了,父亲是老实的教书先生,实在对付不过去了,就卖一两样东西。当年的大府邸还在,但已经不是马延玉家的,他们一家人就住在以前养马的马厩里,“还是比好多老百姓强,毕竟也有好几间房子呢”马延玉说起来非常知足,他没有经历家族的全盛时期,也就不会像马旭初那样心有千千结。只有一次,小时候在院子里放风筝,线断了,风筝飘到隔壁的大宅子里去。小孩子去捡风筝,这才第一眼看到过去自己祖宗住的地方。“真是漂亮,住了一个什么大官。”马延玉形容不出什么,说的都是老实话。他比较犯愁的是,这些旧书旧纸旧事到底怎么处理:扔了吧可惜,卖了吧也卖不出大价钱,放在家里吧,也没有别的人感兴趣,自己一个人,看到哪辈子才能看完呢?
马国琦:熏出来的本事
巧的是,这三个老人都姓马,而且把北京的汉、满、回三大族占全了。马国琦是回族人,他的“户部街马记月盛斋”就开在前门楼子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
老店的户部街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天安门广场。1775年,马家的祖辈马庆瑞就在那开了第一家月盛斋,三进的院子,前店后厂,用宫里的方子做酱牛肉、酱羊肉,慢慢做出了名,宫里人反过来要找他买肉吃。65岁的马国琦时刻记得把家族的历史挂在嘴边:“先有月盛斋,后有美利坚,我们比美国还早生一年呢。”现在马国琦的小店墙上贴了一张清朝时候的北京地图,还做了标记—从小店现在的胡同,到创始年代的户部街,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
前门这一块,一直是北京繁华的商业区。《都门杂咏》记载:“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马国琦说,如今这一块的格局和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祖父那时候比,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一样是人多,一样是靠手艺吃饭。祖上传给他的除了“月盛斋”这块牌子,就是一身酱肉的本事——老北京叫“熏出来的本事”。
马国琦的父亲马玉那辈,兄弟四个一起接掌月盛斋,一个管账,一个管进货,一个管店,一个管锅。只有马玉有守锅的本事,从14岁到68岁,就没离开过锅。酱肉这个手艺,外人都以为是靠酱汁的秘方,其实“靠的是守锅的经验,10斤的肉块和3斤的肉块怎么让它们一块熟,不能小的都煮飞了,大的还是生的。”父亲马玉酱肉是一把好手,只要他出马,一天就能卖上至少三锅肉。可是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长年站着干活,静脉曲张,腿老肿着;对着炉子熏了一辈子,熏出肺积水,最后医生抽出来一看,哪里是水,都是油。
马国琦真正开始做肉开店,是52岁的时候。1992年,马国琦从国营单位退休,自己在丰台找了个地儿,干起祖传的买卖。几乎是每天一锅肉,卖得很不错。老爷子马玉不放心,过来看,尝了一口肉,就急了:“你就这么干?要这么干就别干了。”原来,马国琦把煮肉的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老爷子倔,觉得这不地道,硬是在店里待了3礼拜。这3礼拜里,店里的肉从开始的一天一锅,卖到了两天三锅,最后卖到了一天两锅。
“东西是给识货的人做的,兢兢业业,就怕砸了祖宗的牌子。”马国琦有老派手艺人的自负。好几十年前,梁实秋的女儿写:“月盛斋的肉香,隔着棉帘儿就直往鼻子眼里钻。”现在,经常有客人打100块钱的车,来吃20块钱的肉。当一个好厨子遇见了好食客,那是惺惺相惜。所以,马国琦的老伴、儿子、媳妇全家都在这个不起眼的门脸里边驻扎下来,准备把200年的家业再干下去。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底层世家才能够完成它的物质传承。在马旭初和马延玉那里,世家的命运已经彻底成为了一种记忆,没有下一章可写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