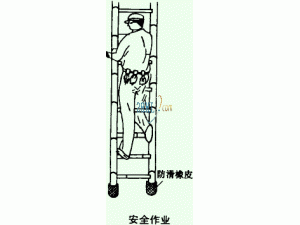大多数时候,企业家个体命运的多舛是因为这个个体纠结了太多的体制性矛盾
顾雏军已被正式批捕,他将为一系列的公司违法操作付出代价。但反省不应该跟随法律的节奏进退。
要求理智看待顾雏军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口水仗中,民众的愤怒经过长时间发酵,直指任何一个已经或将被置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该为类似于顾雏军之类的企业家说句话了。
这并非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于我国企业家资源的珍惜。
大多数时候,个体命运的多舛是因为这个个体纠结了太多的体制性矛盾。具体到顾雏军事件,他的个人命运正好与中国社会现阶段所有重大而敏感的政经命题缠绕在一起。
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顾雏军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
但顾雏军本人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也正是顾雏军的脆弱之处。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顾雏军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他一度拥有的保护并非根深蒂固。他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所以,从根本上说,顾雏军对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
如果我们以为那些受过现代自由经济思想熏陶的经济学家都是瞎了眼,那就是犯了大错。当周其仁一再强调“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当张维迎大声疾呼保护私人产权,他们显然不是因为区区红包出卖自己的良心。他们只不过是看到了,在社会转轨期,在产权结构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张维迎曾提出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张维迎在为企业家辩护的时候,真正希望实现的是,在这个社会尽量实行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保障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保护中国社会本已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令人遗憾的是,本应是一场严肃的讨论,最后演化为口水横飞、涕泪交流的社会闹剧。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市场经济迄今已转轨了一百多年,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被斥为依附者群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一现象的成因。
李鸿章的智囊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今天顾雏军所遭遇的一切责骂,盛宣怀几乎一一尝遍,如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在掌控的所有企业中任用私人,又如私自涂改账册,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就是十个盛宣怀也不顶事。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答案很明显。就是因为答案太过明显,我们反而无法正视,因为一个明显的答案加上100多年解不开的难题,让人不愿轻易触及。于是,争论的主题只能一再简化,就事论事,就人论人,成为义气之争。
为了不再起义气之争,回过来说盛宣怀。盛宣怀身后几起几落,进入民国以后,盛家家产被抄没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期,罪名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因为盛宣怀是引起清末大乱的铁路收归国有与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江苏,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地重新认识,起于上世纪80年代,距离盛宣怀辞世70余年。
顾雏军与盛宣怀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将惩罚交给法律,将深入的反省留给自己,才是避免中国企业家悲剧的正道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