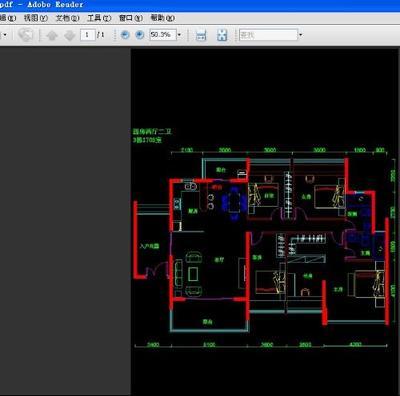“这一群沿着我的足迹走过的人们,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常态的生活当中去。惟有理想、信念、毅力是千年风蚀不掉的存在”
文/本刊记者 边杰
公元2005年10月26日上午,天气晴朗。甘肃敦煌机场由于一行30来人队伍的到来,变得煞是热闹起来。看他们的装束是一副要出门远行的样子,甚至还有人打出了“玄奘之路体验之旅”的条幅。
看着这些热闹的人们,我的内心渐起波澜。1376年前(公元629年)的8月的一个黄昏,我身裹长袍,斜挎褡裢,躲过了卫兵的盘查,离开了长安城。当我回头看着暮色苍茫中的长安城时,心中充满着惆怅,那里曾经是我遍访高僧、研习佛法的地方。但为了到佛国圣地去朝拜,在那兰陀研习佛法,核实汉译佛经和佛陀箴言的差异(现世各种盗版书籍横行,唐已有之啊),在得不到通行证的情况下,我只好置皇帝的敕令于不顾,冒险上路,去往西天。
我叫玄奘,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国的一名普通僧人。当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为了这个朴素的想法,我花费了十七年的时间,当然,这中间少不了一些小小的插曲:忍饥挨饿、爬雪山、过沙漠、遇盗贼,九死一生……不过,这些都已随风尘而去了。
“玄奘的脚步已被风尘掩盖了一千三百多年,但其魅力却历久而弥新,吸引着无数的勇者紧跟圣贤的脚步,重走玄奘之路。人们不仅仅是为了重走地理意义上的一段路,更是为了走向一条走近圣贤、感悟心灵的体验之路。”组织者把这段话通过视频、互联网、纸张等各种介质不断传播。现在,在手机、GPS、步话机、登山靴、补给车辆等的装备下,他们要走上跟我相同的一段路了。
10月27日:寂寞锁阳城
从长安出发,在经过天水、兰州、凉州(今武威)后,我达到了瓜州境内。到瓜州后,与我同行的数十人因路途畏难而却步,但这妨碍不了我西行的步伐。
有意思的是,这一行30来人也有人开始“却步”,那个身份为万通董事局主席的地产商人冯仑,从北京到达敦煌住了一宿之后,选择了匆匆离开,他的理由是“不想受如此的摧残”。事实上,他是“俗务缠身”,还没有摆脱了尘世的牵挂,因为第二天他要去面见商务部官员。同样的,先前答应来西行的商人,包括建业的胡葆森、复星的郭广昌、网通的田溯宁等人,也是因为要跟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见面,而取消了西行。
一行人从敦煌乘车2小时后到达安西塔尔寺遗址。现世中的庙宇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个土垒的塔还在,高十五米,在这片戈壁荒野中显得有几分巍峨,依旧在风中述说着千年的忧伤。当年我曾在此讲经一月有余,并物色到了马匹和一个叫石盘陀的向导。
塔尔寺遗址是这行人的出发地,当地众多官员赶来为他们送行。简短的出发仪式开始后,活动的组织者、一个叫曲向东的小伙子把众人的手机给没收了,众人开始沿着我的足迹西行。
从塔尔寺往西,穿过一片红柳林,约一箭之遥的地方便是瓜州古城——锁阳城的东门。在瓜州城内,我受到了刺史独孤达的礼遇,州吏李昌不惜撕毁朝廷捉拿我的牒文。在深秋的一个寒夜里,我骑着马,带着石盘陀出北门,往西北方向走去。当我深夜潜行,逃离大唐西陲最后一座城市时,心有余悸。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和瓜州的官吏们玩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在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我趁防备不严时离开,而非官吏们故意放走的。即使有朝一日朝廷追查,这样的理由也能搪塞过去。现世的作家周国平走到此地说,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唐代,边郡首领便宜行事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不无道理。
如今的锁阳城像塔尔寺一样,破败不堪,满眼是风蚀后的土城墙和房屋遗址,还有顽强生长着的一丛丛红柳。在唐代,这里曾经是西部边境上的一颗明珠,锁阳城里住着上万的居民,时间让这里变得物是人非,后人们只能从戏剧里想像“薛仁贵征西坚守锁阳城的故事”中感受历史的沧桑。
一行人中的延藏法师说:“废弃的锁阳古城固然美丽,但更让人觉得世事无常。今天我们虽然在此凭吊前人,也许明天就有可能被后人凭吊。”世事的轮回大抵如此。
出锁阳城是一片长着骆驼刺和红柳的沙丘,而后进入一片面积很广的雅丹地貌,外型千姿百态,疏勒河改道的痕迹依稀可见。当年这里是古垦区,疏勒河浇灌着这里约50万亩的农田,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还能看见儿童戏水的身影,一片唐时的田园风光。
离塔尔寺约16公里是他们的宿营地大墓子母阙。当年这里曾是一片坟地,30多顶帐篷下是沉睡了千百年的灵魂。
曾经登顶珠峰的万科董事长王石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说这段历程跟登珠峰是没法比的,登珠峰是对体力的考验,而这次走的戈壁沙滩更多是心灵的荒漠,“徒步走在跟外界隔离的环境里,夜里每个人睡在帐篷里,早上起来感到外面还有一个经济腾飞的真实世界,我们在精神层面应反思我们的灵魂能否跟上我们的脚步。”

10月28日:行者的童年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沙漠里的太阳也如是,这也是催旅人上路的信号。但这些西行的人们并没着急赶路,在收拾帐篷、吃完早餐、合影留念后,将近10点来钟时,他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30公里外的八龙墩。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先坐一段汽车再步行,张维迎、王石、张明正等人选择了全程30公里徒步。
这段路程现在看起来徒步是有些艰难,在经过一段戈壁、雅丹地貌后,是红柳丛生的盐碱地,长着很多的骆驼刺。张维迎在戈壁滩上租了老乡的一匹马走了一段之后,发现周围只剩下自己一人,他只好对着对讲机呼叫,幸亏他附近有一个同行的小伙子听到呼叫找到了他,两人凭借着GPS,慢慢向营地走去。在离营地还有三公里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一辆路过的警车把他们两人送到了营地。
这算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吧,谈不上有什么危险。但我在这里却遇到了生死考验。
离他们八龙墩营地不远处是残存一线流水的葫芦河。这里是唐代的边境,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偷渡的方式。向导石盘陀是胡人,他对地形和这里的防卫体系十分熟悉,知道如何绕过他们而不被发现,对他我还是很放心。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天半夜,我和石盘陀渡过了葫芦河,绕过了玉门关,再溜过前面的五座烽火台就安全出境了。
在默诵了一段经文后,我便睡着了。不久,我就被一阵响声所惊醒,睁眼一看,石盘陀提着把刀正蹑手蹑脚地朝我走来。忽然,他犹豫了下来,又转身回去了。天亮时分,石盘陀央求我不要再走了,他担心靠近烽火台时万一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我让石盘陀自己回家,但石盘陀又担心我被擒拿后,把他供了出来。我向石盘陀发誓不会供出他来之后,石盘陀走了。不过,他给我留下了一匹识途的老马。
在我当年宿营的地方,西行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主题是童年。作家周国平讲述了自己上小学时挨同学欺负的往事,张维迎谈自己窑洞里的童年时光,“体验之旅”的东道主、甘肃著名企业家李振民讲从小挨饿受欺负而发愤图强的故事……在40多年前的那段时光里,这个国家的历史凝结着很多人困难的童年。
人生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呀!每个人在成年之后追求各种各样的成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最能打动自己的还是童年的记忆——因为它纯真。
10月29日:孤独的烽燧
从八龙墩前往白墩子路过现在的安西县城。这个小城街道宽阔,但无任何特色,偶尔有一辆车驰过,路面行人很少。这不是当年我呆过的安西。这一行人在县城吃完午饭后,乘车来到离县城5公里左右的地方开始徒步。
这里不像前两日那般荒凉,因为紧挨着312国道。国道修在古驿道旁,彼处有一座已坍塌的窑洞。这是当年那个叫林则徐的官员贬谪新疆伊犁时,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已部分坍塌,洞里污秽不堪。
一行人穿过古驿道,爬过几座小山坡,在日落时分到达了白墩子。白墩子古称光显驿,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唐代、清代又加以重修。现在依稀可见残存的地基、墙壁、土砖。白墩子下有一池泉水,周围长满芦苇,这是在戈壁里不多见的情形。
石盘陀离开我之后,我孤身一人在戈壁里艰难行走,不辨东西,只能顺着地上的堆堆白骨和骆驼粪前行。酷热、饥饿和疲劳让我精神恍惚,眼前出现了千军万马向我奔来,后人说这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白墩子是我从葫芦河出关后所过的第二个烽火台,我在附近的沙沟里隐藏了很久,到了傍晚去烽火台下取水。正当我往水袋里灌水时,一箭射来,差点射中我的膝盖,紧接着第二箭又飞了过来。我连忙大喊:“我是京城长安来的僧人,请不要放箭!”守关的校尉王祥是个佛教徒,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招待了我,让我在烽燧中睡了一夜,第二天赠给我一些水和食物,并指点我绕过第二、第三烽火台,直接到第四座烽火台。
晚上一行人围着篝火,齐声唱起歌来,也有一女子绕着篝火跳起舞来。这些在城市里来的各色成功人士们,仿佛恢复了童真,兴奋地唱着、叫着。王石讲起了笑话,张维迎用地道的陕北话唱《三十里铺》民歌,那个叫延藏的法师领着大家一起祈求: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毒品,也没有犯罪。
也有人吟诵起“帐前明月光,地上鞋一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姑娘。”这是红尘里的情思和烦恼,跟我这个出家人没有关系,我只希望前行能够顺利,早日抵达我心目中的圣地——那兰陀。
望着热闹的人们,回看残存千年的白墩子,我心生感慨:白墩子是孤独的,当年我也是孤独一人。热闹的是拥有现代文明的人群,孤独的是千年的足迹和残存的历史碎片。
10月30日:千年的叹息
有水、有草的戈壁是个入梦的好地方,帐篷里甚至传出轻微的鼾声。天明后,这些西行的人再徒步20公里就结束了他们的旅程了。
从白墩子出发,沿着一条千年的古道,经过戈壁、丘陵,就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红柳园。王石依然背着重重的行囊,因为马上要去南极旅行,他把此次的徒步也当成了拉练。或许是因为身体的疲惫,或许是因为对自然的审美疲劳,每个人的话都不多,只管低头走路。
集合、留影、庆祝、闭幕仪式……这些西行的人们在热闹中开始了我的旅程,并在热闹中结束,他们乘车返回了敦煌,返回了灯火辉煌的现代文明。他们的终点,其实是我苦难历程的起点。
我径自到了第四烽火台,由于第一烽火台校尉王祥的关系,我结识了他的同族人王伯陇。王伯陇送给我盛满水的大皮囊以及麦饼,他提醒我要当心第五座烽火台,因为那位校尉不敬佛,难以通融。王伯陇建议我绕道西面二百里外的野马泉。
我在沙漠里很快迷了路,更糟糕的是,我失手把水袋掉了,所有的水都渗进了黄沙之中。在莫延贺碛的八百里沙漠之中,处在迷茫绝望中的我只好转身往回走。但走了十多里路后,我想起了自己曾发过的誓:“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于是我毅然回转。在四夜五天的时间里,我和马都滴水未进,几乎渴死。幸亏那匹老马驮着我,找到了水源,才保住了性命,走出了茫茫沙漠。后人形容这一段是我“超凡入圣”的决定性过程。
晚上在敦煌一间小饭馆里,西行的人们在此聚餐、讨论,每个人都发表了对与我同行这100多公里路程的感受。归纳起来,人们从毅力、精神、信念等方面表达了对我的尊敬,并结合了一些现世的情形。
王石说,他的感受是“拿得起放得下,让你的灵魂跟上你的脚步”;学者周国平说,走玄奘的路,悟自己的道;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齐大庆说,今天中国真正的企业家有种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经历了一个企业初创、成长、壮大整个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难得,而且这个过程是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有非常强的直觉和信念;博华紫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保刚说,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有点理想主义之外,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玄奘法师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具有坚韧毅力的执行者。
徒步走了一天后返回北京的《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在电话里说,信念对一个人十分重要,玄奘法师就是抱着去西天取真经的信念走完了这条路;另外,人要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去冒险,这一点在创业型的企业家和玄奘法师身上表现得一致。
来自台湾的趋势科技的董事长张明正似乎很开心,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的路,对自己能坚持下来感到非常自豪。他在饭馆里给众人表演魔术,空手变百元大钱。他有一个好消息发布,在徒步结束时他接到电话,公司在他外出的这四天里股市市值涨了13亿元人民币。
一千多年过去了,人类的文明在战争、灾难中坎坷发展,现在只是在通讯、交通、基因等方面比前人有所突破,但贫穷与灾难、信仰与人文的缺失依然困扰着芸芸众生。虽然有理想的人们也在呼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重振大唐盛世的繁华,但这不是几个人走一段路就能解决的问题。
喧嚣即将过去。这段距离,是地图上的几厘米,飞机上的几小时,却是我的九死一生,昭华数年。这一群沿着我的足迹走过的人们,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常态的生活当中去:张维迎要参加北大MBA学员的开学典礼;王石12月份去南极,继续他的登山运动;张明正将在魔术中发展着他的趋势科技……商人们又将面临纷繁复杂的商业,文人们又将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人性的光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惟有信念长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