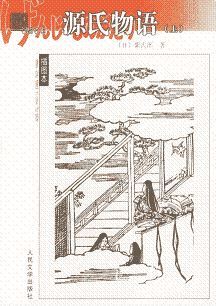当一个台湾出生、香港执教的明星教授戏剧性地高调挑起争论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社会过去20年赖以发展的共识,原来是这么脆弱
一场重要的争论正以奇怪的方式在进行,学者和大众深深卷入,而争论涉及到的两个主角却一直保持着缄默。
这场争论,关系到两个20年没有公开争论过的大问题:一是国有经济的民间化问题,也即所谓“国退民进”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二是创业型企业家的“定价”问题,是“保姆”还是“之父”?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争论。正因为重大,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张维迎、周其仁以极大的勇气先后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任何不同与朗咸平的观点,现在在网上都会招致一边倒的骂声;好象反对朗咸平,就是人民公敌。
这种道德化了的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压力,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很盛行;改革开放后只有在涉及日本、台湾、股市等高度情绪化话题才会偶然出现。
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张扬,是20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崛起的不二法门。在过去20年间,尤其是小平南巡以后的十几年,这一点从来没有引起大的公开的争论(拜小平“不争论”之赐),也几乎成为中国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家的共识。现在,当一个台湾出生、香港执教的明星教授突然戏剧性地高调挑起争论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社会过去20年赖以发展的共识,原来是这么脆弱。

为什么两个主角—政府和企业家都不说话?
弱势的企业家不敢说话,但政府应该说话的。郎教授以替国家代言的道德高点出现,他的两个质疑,又只有政府才能回答:中国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对是错应不应该进行?作为大股东的政府怎么给企业家定价?矛头是指向了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业型企业家),但其实有决定权的,是政府。能够对这两点质疑作出回答的,也只有政府。
20年来,政府和企业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发展同盟”。政府把资源向企业家集中,企业家得到一个中国过去前所未有的机遇发挥自己的企业家天赋。二者合力,企业、经济搞上去了,企业家(张瑞敏等)得到了中国社会以前不可能给商人的社会荣誉,政府作为股东获得税利作为社会管理者创造了就业,皆大欢喜。这种关系,表面看起来,与西方经济中股东与企业经理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才有“保姆”说。
但是,这种同盟潜伏着一个极大的隐忧:海尔、TCL、春兰,这样的企业在创办时,政府和企业家并没有像西方惯常的那样签定一个明确的协议。也许是双方当时都没有现在这样清晰的权利意识,也许当时根本没有那样的政策环境与手段,也许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企业后来能做那么大,总之,“原罪”就这样埋下了。现在企业做大了,企业家快退休了,整个社会的权利(产权)意识强化了,问题陡然出现:怎么给企业家定价?
即使没有这场争论,问题也存在,也会解决。实际上,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不争论”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原罪”难题。TCL和联想是典范:政府利用企业上市的机会,在给企业定价的同时也给企业家们定了价,无论名义是管理层或团队或员工或工会,股权比例大概都在15%左右—这也是现在在中国从头创办一个新企业时投资人给管理层安排股权的普遍“行情”。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并没有这样幸运。同样是家电企业,倪润峰就惨淡出局,陶建幸改制被叫停,陈伟荣早已离开自己创办的企业。家电之外,玉溪褚时健健力宝李经纬获罪,三九赵新先长城王之到点退休。—同样是著名企业的创始人,命运如此悬殊,怎么能让人心平气和!
创始人在全世界的企业界,都是共同现象。西方很多大企业现在的名字中,还含有创始人的名字,比如HP、高盛、丰田等等。《中国企业家》一直在大力提倡中国的“企业创始人”文化,曾经推出过《中国企业创始人价值评估》等报道。
这一代企业家是中国艰难崛起岁月的英雄。他们提供了我们最初温饱生活的所有的生活用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股权回报上是“失语的一代”。在他们之后创办的企业,拜他们所赐,几乎不再存在股权“说不清”的问题。年近退休,他们这样的人将成为消失的一代。中国社会即便假装看不到他们的贡献与尴尬,让他们抱憾退休或获罪,也最多影响到他们的企业。以后的企业家决不会再走他们的老路。
但历史将记住中国这个快速小康国度的失语与无情。而郎教授等的外来者由于没有和我们一起走过那段艰苦岁月,是不会因此感到任何内疚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