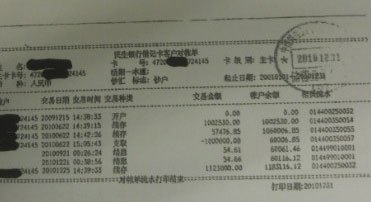我当然知道公司治理是怎麽回事。公司太需要每天一次、周日两次被进行监督了。当然,我也知道每个对我们公司投资 152.34 美元的人都是企业的主人。
但是......现在我们难道不该对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嚷嚷几句吗?
我刚参加过这样一次会议。作为一种民主的体现,会议是令人鼓舞的。换句话说,它鼓舞我从会议中逃出来,重新投入工作。
一开始和往常一样,一群年老并好斗的人们走上讲台,抱怨公司没有准备饼干。似乎过去的股东大会不仅有饼干吃,还有蛋糕,有时甚至还有小叁文治来就咖啡、茶和软饮料。反正他们是这麽说的。真是好时光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你知道那一套把戏。先是董事长起立发言,接下来总裁用一些好看的图表来展示公司的战略。不管讲的多麽精彩,听众仍然是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这不是他们来的目的。“我们刚要就董事的人选提问,”公司法律顾问说,“这时候却有人插了进来,我们不得不放弃企图,真是令人苦恼。”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封投资者来信的编辑。她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是以浓重的特兰西瓦尼亚口音表达出来,同时还扯到很多其它问题,直到听众难以忍受,嘘声四起。她谈起当“最低收入的员工”要求看她的证件时她有多气愤。她叫喊着说,“为什麽我们需要这麽多的安全措施呢?”然后,她对一些企业高管发表了侮辱性的言论,这些人则试图在台上露出亲切的微笑。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 75 岁的绅士,他非常谨慎、优雅,容易动感情。“我从 1958 年 2 月 23 日起就一直参加公司的年会,”他一边深思一边说,“那是一个星期四,从那时起我已经在共涉及 1.6 万亿资产的 198 次单独的年会上提过 543 个问题......”等等等等。这位先生还站起来好几次,就其他数字性证据补充发言。我敢肯定他是个优秀的驾驶者。
时间在流逝,要紧的事情一件都没干成。除了......这能算是......要紧的事情吗?
另一位投资者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公司计划将绞床部门剥离出去!”他气愤地叫嚷着。有人问他的消息来自何方时,他回答,“我记不清了,”然后便坐下了。听众哗然。局面正在逐步失控。
一个五短身材的女士走到麦克风前,开始朗读关于历史上美国企业管理人员渎职行为的报纸文章。有人觉得有趣,有人则不然。后来,一群吵闹的股东站起来,开始冲她叫喊,要求她坐下。他们似乎认识她。也许他们在其它年会上见过她?
“我没有代理人!”那位从特兰西瓦尼亚来的女士喊道,这引起了许多同样有被忽视感觉的人们的附和。法律顾问试图维持秩序,但失败了。
这时一群打着手势、抱怨连连的乌合之众开始去拿干草叉、棍棒和火把,争夺麦克风。他们这会儿想说什麽? 极权主义专治下的企业投资?核战争?大烟商?收购与剥离?性?毒品?对上司的恭维?上面所有这些话题?还是另有什麽新鲜事?房间里的噪音水平在不断上升,人们的面颊开始变得粉红,继而转为通红。
当一个满面通红的家伙从我的耳畔经过走向台上时,我已经准备离开。董事长、总裁及法律顾问都在那里各显其能,但是听众们却没有什麽可做的事情。当一群骑着单轮脚踏车的小矮个儿突然出现在前厅,开始沿着走廊跳来跳去,质问企业的管理费用是否与其历史正常水平相当时,我悄悄地站起来,从人群里挤出了大门。
当我离开时,我看到讲台上的人们站了起来。董事长大叫“回来!回来!”并用一只激光笔吓唬听众们。总裁也站了起来,两手叉腰,像个流氓一样大笑着。法律顾问躲在桌子后边默默祈祷,他的工作日志顶在头上。我并不责怪他。勇敢的要素之一就是判断力,尤其是在法律规定的事情上。
明年......你知道吗?我认为他们应该提供饼干。有时能吃块饼干是很不错的事。那当然不会有什麽坏处,不是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