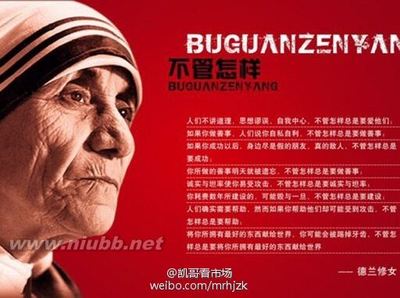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交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交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性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性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性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炸弹。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www.aihuau.com|1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交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证券化的抵押债务卖给表外工具,就不再面临任何风险。作为有权决定给谁贷款的施贷方,银行却不再与贷款方有任何联系,也不担心他们是否还得起这笔贷款。与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传统角色相比,这种模式下的银行家们积极进行着风险分散。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没有风险的风险”,同时还能攫取巨额增值利润。当这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真相大白时,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傻。例如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对银行进行常规审查时,总被它们账面上显示的良好财务状况唬住,全然不知其与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充斥着次贷风险。让问题更严重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将表外工具发行的商业票据定级为“高度安全”。它们认为,既然债务是有保障的(并且因此被多元化)且与房地产挂钩,那么就不会崩溃。它们笃信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跌,至少不会在全国普遍下跌。从金融角度来说,银行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极佳状态。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个季度中,某些大型银行的净资产收益超过了30%,这在银行界实属罕见。在那一时期,全球顶尖货币经理们囊括了这一收益的一半。为何监管者和评级机构从未质疑银行家在没有耍诈(表外风险敞口、危险的融资杠杆)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成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种金融法则与美国大学评级体系非常类似。每年,各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都关注着各大学的评级结果。首先要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平均分数,以判断该学校的总体水平。这听起来似乎挺严谨,除了一件事—很多学校呈递的都不是完整的成绩单。它们轻轻松松地抹去了一些特殊学生群体的成绩—运动员、少数族裔,或者一些有缺陷的人。这样一来,光鲜亮丽却误导人的成绩单就诞生了。意图可能是良好的—告诉那些普通中产家庭的白人学生考取这个学校的成绩要求。然而这完全是虚假的,对那些遵循规则提供准确和完整测试结果的机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从这点说起,次贷事件听起来就不陌生了。由于全球化网络的紧密联系,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会陷入困境。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部,但却拥有大量买进的评级很高但最终可疑的美国商业票据。欧洲的金融监管机构,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对于所辖银行旗下那些坏账累累的表外金融工具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都因为美国证券化债务的牵连而暴露于高风险中。通常人们认为高度安全的资金突然饱受质疑,严重的信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次贷引发的危机一大恐怖之处在于:尽管中央银行努力采取措施以逆转局势,发达国家的信用市场却仍在收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哮喘病人,进入肺部的空气持续消散,喘息中的经济也渐渐窒息,急需氧气供应。如同预期一样,各国政界都抓狂地搜寻快速救市的良方。2008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税收刺激计划,意在遏制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整体经济混乱局势;一些政治家建议将抵押贷款利率“冻结”5年;由美联储开道,很多中央银行都积极响应,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前瞻性地首先着力解决了紧急问题—数百万美国家庭即将流离失所,需要政府救助。他们同样也深知整个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因此,无论国会如何焦虑绝望,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氧,喘息着的经济已由甜菜红变成深蓝色。逐渐清楚的是财政和货币疗法已不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完全就是对于金融架构的信任危机。这一关键性问题其实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就酝酿已久。这个问题就是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对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信心的丧失。国际金融策划师哈拉尔德8226;马尔姆格伦曾经给这些有价证券,包括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一种抵押债务的保险单),以及一系列的信用衍生品,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信得过资产”。如果把全球经济的信用配置比做血液流动,那这些证券代表的就是其中最核心的动脉。而次贷危机引起的信心丧失,造成了这条动脉的严重血栓。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在风险评估和企业资本配置中,证券化如何演绎了其不可或缺的罪恶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金融操作,它作为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经济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危害了全球经济生产力。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市场的削弱让人大跌眼镜。这是因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买家的“罢工”。这使全球交易者对手中持有债务工具颇为不安,这些证券的价值只能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定,这些机构由于通常依赖数学模型,而不是对资产信誉直接验证,其评级成功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这场信任危机立刻给全球经济的信用市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金融体系赖以存活的输氧管道几乎完全堵塞了。马尔姆格伦用更多的细节描述了那种形势:“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量客户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包括公共和私人的养老基金、当地政府的财政主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及资产管理人、信托机构,甚至对冲基金……然而唯一能衡量这些证券的风险和价值的途径只有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在监管限制的指导下,很多买家,特别是养老基金,一贯追随评级机构的标准。2007年春天,一场慢动作的火车脱轨事故却正在发生。每况愈下的评级结果完全背离了最初的结论。那些手持资产支持证券的买家现在只剩下了不能变现的资产。”这起脱轨事故让那些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惊慌失措。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时的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作为全球信用体系主动脉之一的资产支持证券一夜之间失去流动性。然而对于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不信任仍在全世界蔓延。而这个苦果恰恰源于这些金融机构没有全面分析它们所从事交易的潜在风险。这段时间里,美联储官员们奉命救市,更加激进大胆地降低短期利率。由于担心重蹈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的10年”开始时所犯的错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迅速大幅降息,其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史无前例。虽然货币政策的实行能暂时稳住更大范围内的金融市场,争取到时间,然而降低利率的举措却仍然无法挽回投资者对于与贷款方毫无关联的施贷方金融投资工具的信心,也无法迅速恢复其对于这种将金融风险转嫁给神秘的表外工具的体系的信任。2008年3月中旬,美联储官员陷入恐慌。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和其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方式都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著名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已经濒临破产。美联储官员指出: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这样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破产,将可能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并造成股市暴跌,全球性经济崩溃也就不远了。美国经济已经濒临衰退。而那时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其深远影响可能要到数年后才能被充分了解。3月16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周末后,美联储将贝尔斯登和其他一些所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归政府安全体系之下。在此之前,该体系都是专为美联储所监管的银行设立的紧急救助站。不仅如此,美联储还为贝尔斯登敞开了“贴现窗口”。“贴现窗口”设立于大萧条时期,专为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而不论它们的抵押品资质如何。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强制要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同时美联储以获得贝尔斯登的290亿美元不良资产做交换,向这家深陷困境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提供借款。请允许我解释一下这个决策:美联储原则上似乎为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了这项政府保障,同时美联储和其他一些管理机构可能会承担更重要的金融市场监管任务。鉴于金融危机的急迫性,尤其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绝境,也许美联储别无选择。然而这顶宽大的政府保护伞最终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对于贷款会起鼓励还是抑制作用,还有待观望。在一个受政府保护的体系中,一些管理机构需要维护公众利益。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监管机构在风险评估和把握资金流动性问题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辉煌战绩。难道一个新的巨型美国监管机构,不管设立在哪里,都能够做得更好吗?金融市场中那些万能的巫师们总能够发明出各种合法的手段来规避监管限制。如果有一个新的美国监管机构,我想很多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一些更加灵活的金融实体可以轻易地在国外从事金融交易。美联储或其他监管机构的职员可能会成为一项新的复杂决策流程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的格雷格8226;伊普曾做过报道—“美联储被委以也许无人能及的重任:预先识别并防范危机”。哈佛大学的马丁8226;费尔德斯坦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复杂的衍生工具进行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回报丰厚,冒着存亡风险的金融机构犯了错,靠美联储就能纠正吗?”事实是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的监管机构职员都在关键时候麻痹大意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一个本分的政府官员无论如何也斗不过那些诡谲又擅长发明创造的金融巫师,还有他们那些打从监管条例一出台就立刻搜寻合法对策的精明律师。当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年薪为14.3万~21.6万美元,而高盛集团里最初级的决策师,其每年的酬劳都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2006年,高盛员工的平均年薪为62.2万美元,某些行政助理和秘书也能赚到20多万美元。然而现今的危险却在于:监管者在金融危机中被发现疏于监管,为了补偿,他们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监管。在金融市场上,过度监管对资金的流动性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对美国来说,过度监管会进一步削弱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监管过失会使已经受损的信用环境恶化。同时,由于那些活跃的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转移到管束较少的市场上,过度监管由此也会进一步削弱美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