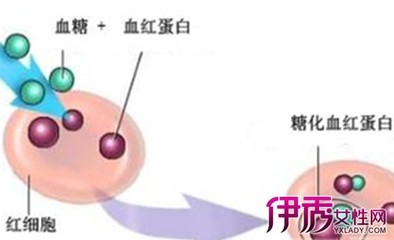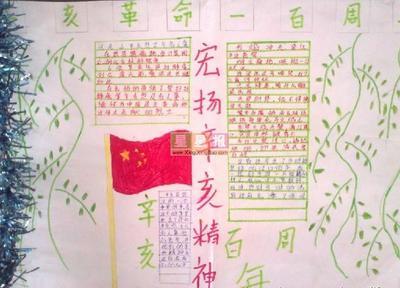虽说《系辞》的那句“一阴一阳之谓道”非常有名,但其实《易经》中并没有产生阴阳的概念。陈鼓应先生说,在春秋时代,还没有发现用阴阳解释《易》的例子。从现有材料来看,以阴阳解《易》,当出于战国时期。这种释法始见于《彖传》,而且只是在解释泰、否二卦时才出现: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从这里来看,《彖传》的阴阳是指干坤二卦,即以干卦卦体为阳,以坤卦卦体为阴。泰卦干下坤上,故曰“内阳而外阴”,否卦坤下干上,故曰“内阴而外阳”。《彖传》作者以阴阳解《易》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阴阳二气交感是万物生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咸卦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冯友兰先生说:“这个所谓的‘二气’,就是阴阳二气。”这种阴阳二气感应在《彖传》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天地交”。《彖传》中多次谈到天地交而万物通,反之则不通。后来《系辞》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说,“道”原为未分阴阳的混沌统一体,其后分化为阴阳两气,它们相互交冲,形成新的和谐体。庄子更是明确讲:“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翅,通“啻”)。陈鼓应认为,老庄的这种阴阳气化的思想正是《易传》以阴阳解《易》的理论来源。

《周易》以简驭繁,分别用“——”(阳爻)、“--”(阴爻)两种符号来指代阳和阴,用两种爻错综重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从而构成了《周易》的“象”世界。阳与阴最基本的象征是男与女、天与地、刚与柔、动与静,等等。推而广之,阴阳象征的事物遍及宇宙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原则。
《系辞》主要是论“阴阳”,文中运用大量篇幅反复论述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则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阴阳合称为“两仪”。《说苑·辨物》云:“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易有阴阳,性有好恶,人有生死,都是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回答赵简子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二,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二也。”世界上也存在物生“有三”、“有五”的现象,如“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但“三”、“五”都可以化约为“两”,是故“物生有两”是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形式。“陪二”即陪伴为二,是对“物生有两”的说明,与下文的“妃耦” 引义相同,说明事物具有两个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全然并列的,而是一种主从关系,也就是引导事物发展、变化的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如“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二也。”
“物生有两”的命题说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有完备的系统整体概念,而且有丰富的辩证矛盾观念。史墨提出“物生有两”,王安石说万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万物莫不有对”,程颐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朱熹提出“万物皆有两端”、“独中又自有对”。张载主张“一物两体”的命题,朱熹将其概括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方以智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二而一”:“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两间无不交,无不二而一”,“交也者,合二而一也”。王夫之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
史墨姓蔡,名墨,官为晋太史,故称史墨。他和赵简子问答的背景是:周敬王十年(前 510),鲁昭公被权臣季平子赶出鲁国,最终死于流亡地晋国干侯。晋国大夫赵简子就此事问史墨:“季氏大夫逐出他的主君,而人民顺服,诸侯友善对待,国君死于境外,却没有人怪罪于他,这是为什么呢?”史墨说得毫不客气:“天生季氏,与鲁侯并立如同两君,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人民顺服季氏,岂非理所当然?鲁君世代失政,季氏世代勤政,人民早就遗忘了国君。虽然死于国境之外,又有谁会矜怜他呢?”接下来,史墨作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社稷无长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壮,天之道也。”
史墨从具体事物中看到了“物生有两”的矛盾,事物的“两”不断变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君臣关系因而也无法逃脱变化的命运。他由此论证了国家政权旁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这正如大壮卦一样:干为下为君,上为震(雷)为臣,雷乘干所象征的正是君臣易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种变化被视为完全是正常的、合理的,这一政治结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