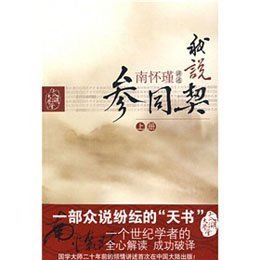《黄帝四经》看重“名-实”关系,欲通过这一关系来区分对与错,从而找到治理国家的方法。上篇专栏已经分析了“道-形名-治理”的逻辑推进关系,由此,统治者作为“执道者”如何审查“形”、“名”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先秦法家明赏罚的重要治术,是“形名参同”。形名,形体名称;参同,参验查证。形名参同讨论实体与概念的关系,其核心是名称要与事实相符。《韩非子8226;扬权》曰:“名正物定,名倚物徒。”这是说,名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事物的性质也就确定了;名如果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事物的性质也就游移不定。名的规定需要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吻合。那么,在治理上,如何才能实现吻合呢?就要“循名而责其实”,防止虚其名而滥其实。
《韩非子8226;主道》云:“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与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无所事事了。所谓“无事”,只是指毋需管理日常事务而已,君主还必须做的是监督与赏罚。“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韩非子8226;八经》)。韩非主张君主要听臣下发表的意见。“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韩非子8226;八经》),谓君主遇事要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集中起来讨论。“督其用,课其功”,继而“功课而赏罚生焉”,就是君主听臣下所陈之政策,令其执行,然后督察执行情况;最后课其功效,功效着者赏,否则加罚。
君主万万不可遇事自己逞能,做臣所做之事。惟其如此,才能督促臣民所做之“实”尽量符合他自己所命之“名”,然后君主按“名”考察功过,论功行使赏罚。《韩非子8226;二柄》中“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正是对君主运用形名术的最好诠释。
《黄帝四经》中并无“形名参同”的说法,但用“形名参同”来解释《黄帝四经》的思想是一种十分通行的做法。曹峰先生指出,这种解释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将《黄帝四经》中所见“形名”直接看作君主对臣下“循名责实”的“形名法术”,此为狭义的“形名参同”观,具体已如上述。另一种则是广义的“形名参同”观,也即《经法》所见“形名”的适用范围与一国之存亡兴废相关,不仅仅是一种督责、操纵臣下的法术。也就是说,“审名”作为事关国家兴亡的考察术,当国家或统治者之形态与规定的位置与姿态相一致时,称其为“正名”,不一致时则称之为“倚名”。
这与《申子8226;大体》中所言“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一样的,反映了对制度化与稳定对称关系的追求。《四经》在这部分明显地肯定了儒家对正名思想的强调,认为政治上的分工与位置的维系是政治秩序的重要凭借。在这种名分与实际相符的刻意安排之下,《四经》推导出自然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必定一致,而又辅以阴阳思想,使名位关系带有强烈的正当性:“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於人者阴”(《称》)。除了君臣关系的稳定对称之外,在《亡论》、《六分》中,《四经》分析了几种错置的君臣关系(《亡论》谈六危、三不辜、三壅;《六分》谈六逆),它们都是国家衰亡的重要指标。面对随时可能错置的的君臣关系,《四经》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追求“君用术於上,臣行法於下”的动态和谐。所以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正名虽然是孔子提出来的,但发展为循名责实的治国理论则是《黄帝四经》所首倡,后进一步经申不害和韩非的发展才转变为法家理论。
其间的区别是,与“循名责实”不同,孔子的正名可以“顾名思义”说之,也就是相信人世间某些基本人伦角色(如君臣父子)的安排和分际自有其天经地义的是非道理,由此孔子的正名就是要确定礼的规范,礼的各种规定即是名,它所规范的各种人的行为即是名的内容。此所谓儒家“正名以礼”。

而黄学的形名理论却是由儒家的正名思想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融合而成。《经法8226;论约》说:“执道者之观於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於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这里,清晰地给出了“执道者”如何利用“审名”展开政治活动的三大步骤。第一步,审查对象之“形”、“名”是否处於正确的规定位置;第二步,通过确认对象之形名,看穿对象的最终结局;第三步,再给对象赋予与“名”相应的赏罚。
“达於名实相应,尽知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经法8226;论》)。可见,确定名实关系即“帝王之道”,亦即治民之“成法”。所谓:“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十六经8226;成法》)。“一”者道也,社会之秩序也。“名”则是根据道而设的法及其他规章制度。“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抱道执度”就是由道而法,“循名复一”就是以法治国。由此可见,黄学的形名学说正是法家法治思想的方法论保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