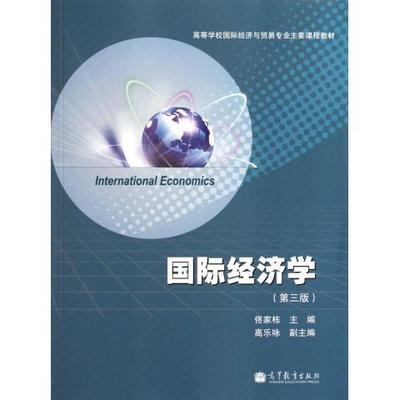在欧洲,公元 1500 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如: 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在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8226;诺斯的笔下,这两个世纪中,荷兰和英国为优胜者,法国为失败者,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为明显的失败者。“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尽管它们宫廷宏伟、雄心勃勃,却不能与荷兰和英国一争高下。”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到诺斯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归咎何处: 它们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体系。这是与两国在政治发展上的集权制密切联系的: 两国的代议机构为得到稳定和秩序,放弃了对征税的有效控制,王权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垄断权力。对这种政治集权的后果,托克维尔沉痛地说: “在法国,再也没有城镇、自治区、村庄,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大学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或可以不受任何干预地来管理其财产。”
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有两大相互联系的特点: 王室对税收的控制是绝对的;除了税收外,国王又开发了一个生财之道,即卖官鬻爵,致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而这支官僚队伍完全唯王室之命是从。
这两大特点造成了一系列后果: 首先,法国政府的税制和特权削弱了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从而弱化了企业的创业和组织精神。17 世纪英国法律发生变革,允许政府的卡特尔公司把通过革新所赚的大部分收入留在公司,而同一时期的法国政府却把这样的利润留给自己。路易十四的传奇财政大臣柯尔伯很难建立一个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同等集团,他抱怨说: “我们的商人不善于从事那些他们不了解的事情。”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私有经济一直习惯于依赖政府的恩惠。

其次,行会被用来作为政府控制的主要代理机构,它和产业官员一起,形成双重管理机器,成为对制造业和商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实行巨细无遗的控制的支柱。行会受到法院支持,甚至当它们的中世纪式管制有时遭到政府稽查人员反对时,法院也站在它们一边。行会成了法国产业组织的基础。国家支持行会垄断存在下去,是为了得到岁入。行会向王权购买了垄断权,这是王室的一项可用金钱购买的特权。如果新发明威胁到现存垄断,王权为了不违反以前的转让就会规定,转让只适用于有限的市场区域,而非整个法国。创造发明过程由于这种行为实际上得不到鼓励。根据道格拉斯 诺斯和罗伯斯 托马斯的研究,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以织物染色为例,管制条例达 317 项。条例是在与行会官员协商后制定的,一般反映了中世纪的生产技术。由行会官员控制和检查的制度可能相当繁琐,在柯尔伯时代连普通织品也至少需经六道检查。
第三,由于“例外、特权和约束”遍布法国各地,致使法国到很晚的时候还不能形成完善的民族市场。荷兰联合省幅员逼仄,英国领土不广,它们的反应相对灵敏,较易达成统一。而法国在进入近代时,是一个既统一而又分散的国家。说它“统一”,是因为它在大革命之前有比较牢固的王权;说它分散,是指它各地发展很不均衡,如布罗代尔所说,法国有如“若干色彩不同的小块地区拼成的镶嵌画,每个地区在一狭小的空间内自给自足”(《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358 页)。大概可以把旧秩序时的法国看作是由 30 多个孤立的市场区所组成。各地被国内关税制度人为地分隔孤立开来,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阻挠一个广泛市场的发展。
第四,税制和特权政策也影响了法国的社会结构。从许多方面说,法国是一个充满阶级的社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述道,法国把人总体分为三个等级,而在每一级中又存在著细微的地位区分。英国式的“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法国,而卢梭那种强调“平等”和“公意”的政治哲学只能产生在法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法国社会阶级分明的特性,以及法国人对权威的传统态度,造成了一种缺乏弹性的职业体制。人们木然地接受强大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威,但实际上这种权威是非常脆弱的,当改革的压力造成了突破口,体制中的人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颠覆并怀疑一切权威。这种模式体现在法国的劳资关系上,就是因它不会循序渐进地进行小幅调节,而往往是周期性地爆发高度政治化的工人运动危机。
从精英层来看,成功的法国资产阶级往往被贵族阶层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同化,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并不想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扭转地位,而是向往贵族安定、有土地、食利的生活状态。法国大众消费市场形成较晚。还有,法国人对小型的、贵重的、高品质市场的顽固坚持,都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贵族式鉴赏力的遗风。
总之,在法国,(1)劳动的流动性到处受到限制,结果使进入一个行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困难重重;(2)资本的流动性也同样受到限制;(3)那些不得违背习俗的烦琐生产条例,使创新到处受到限制或被禁止;(4)行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一直延续不衰,使法国经济丧失了可以从交易部门得到的增益。所有这一切,造成法国在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域滞后于荷兰和英国,“取得的进步像画面上的斑点”(布罗代尔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