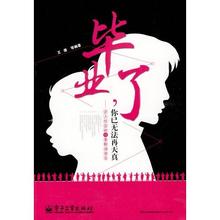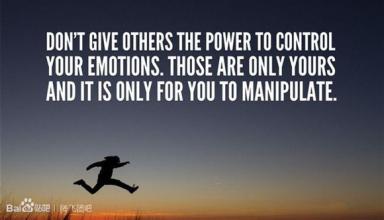系列专题:《徐小平帮你设计成功人生:仙人指路》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大约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吕林,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家里吃饭。电话中吕林说他非常想来,但实在是赶不过来,我说有什么来不了的,来吧,我等你。吕林说:"真的来不了,我在威尼斯采访呢!"我和吕林开心地大笑,心头充满了一种无名的喜悦。 这是我和吕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后一次对话。九月中旬,我从外地回京,突然听到吕林去世的噩耗,在难以置信的悲伤和震惊中,我按下了手机通讯录里"吕林"的名字,电话接通了,响起的是吕林生前设置的音乐铃声,那是一片百鸟朝凤的天籁之音。当时的我,呆呆地期待着吕林也许会来接听电话,并且说:"啊,小平,你这个家伙,又在干嘛呢……" 吕林再也不会接我的电话了。我的生命里,少了一个最能欣赏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个曾经活跃,曾经奉献,曾经多次搅动未名湖文化风云的可爱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吕林成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刚来不到一个月,很多北大的学生学者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认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务正业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纳,需要朋友的支持。吕林把我写的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乐朗诵,在他主持的北大广播台播放。在吕林的帮助下,我刚刚萌发的发展校园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吕林录音采访了我们正在排演的剧目《活的音乐史》。《活的音乐史》是我到北大后创作的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关系到我本人校园文化实践的成败。通过吕林的这次采访和宣传,这部后来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留下持久记忆的节目,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并在首演的那天,引来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我和吕林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在吕林的追踪下,我俩找到了打出这些标语的同学。并在当天夜里九点多钟,在团委办公室,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稿,我清晰地记得吕林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发稿的形象,心里对他这种形象充满了喜爱和仰慕。 当时,我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对吕林这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学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吕林以及其他许多和我结下终身友谊的北大学生,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老师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师",而是"小平"。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人民和光明两报发出稿子之后,我们和中青报联系。值班人员让我们把稿子亲自送去,并答应给我们报销来回打的的钱。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时,那边来了电话,说不必送了。我和吕林都很扫兴,但吕林似乎更扫兴,他说,咳,可惜,早点出门就好了,一次兜风的机会没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