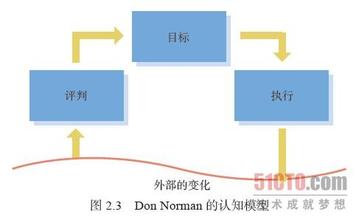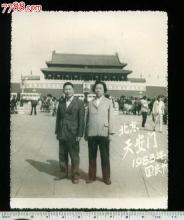
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1983年“中国式的” 从1959年开始,廖鸿英曾先后七次回到中国。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籍华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德里克·班以安(Derek Bryan)的夫人。1983年,她用英文写下了一篇长文《中国见闻》。 廖鸿英曾于1927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鸿英后来也曾到过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但由于当时剑桥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学位,她转向牛津攻读生物科学专业,并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结为好友。廖鸿英此后是中国研究胰岛素的先驱之一。在英国期间,她还和英国著名科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相识。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时,廖鸿英便是合作馆的秘书长、李约瑟的主要助手,为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创作提供过不少帮助。 廖鸿英的丈夫班以安曾经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在外交官任内经历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变。班以安先后在中国的福州、南京、广州、桂林、成都、澳门等地的英国领事馆供职。1943年,他在赴中国西北考察途中,乘坐的汽车抛了锚,不得不向附近人家求援,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和对共产党军队的欢迎。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正是在那次考察途中,他邂逅了未来的夫人廖鸿英,结下了与中国的半世情缘。国共战争期间,尽管国共两党实力悬殊,但他始终认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人心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以安留守在南京英国使馆。1949~1951年,班以安作为三名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中英建交谈判,并由此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新中国”在短短一年间发生的变化。1951年班以安回国休假。然而,当他宣传“新中国”的变化时,却受到了“亲华”的指责,并因此不能再去中国工作。班以安最终离开了英国外交部。此后,他参加过英中友好协会,后又创办英中了解协会,并通过译书、写作、讲学等方式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和夫人廖鸿英在中国各地讲学,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廖鸿英的《中国见闻》描述了这些“巨大变化”。 正如廖鸿英在青年时代所见,中国农民有着长期苦难的历史: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既受到本国苛捐杂税的剥削,也受到外国人的剥削。这一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言:“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逐步实现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廖鸿英眼里,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然而这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这许多改变使农民富裕起来了,但人们在一个生产小组里面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宁愿依赖集体而不愿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对于生产责任制,廖鸿英的理解是,一家包干一块地,负责提供定额的粮食、林木、鱼虾,“他们可以在公社计划的范围内自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了”。 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否定了这是“又回到了过去的个体耕作制”的观点。因为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出售或购买别人的土地。责任制,“不论对一个生产队,一个家庭或对某个个人来说,都只会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劳动效率和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分工负责’和‘个人耕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了,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家庭的收入在增加,新建的住宅一座接一座地落成。商店里挤着满满的农村妇女,“她们还嫌东西太少了呢!”“自由市场”现在出现在中国街道的两边,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略高于国营商店,但是东西很多,品种齐全,不用排队。 但是廖鸿英也注意到了“竞争”问题。比较富裕的农业生产单位现在开始派人进城,用比在城里高得多的工资去招聘技术人员。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她看来出在个体户,由于他们认为生产越多越好,于是,就把原本应该上学的孩子留在地里帮助大人干活,以致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更为难以解决的还有计划生育问题,许多农民仍然受到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总想要个男孩子。 在政府管理机构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过去的一年,就是以对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和精简整编以及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为标志的一年。经济资源的浪费、政府部门工作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这些病害可以说渗透到了全国。报纸上经常刊登读者来信,甚至有读者引证毛泽东在1942年关于精简机构以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章来说明精简机构的必要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