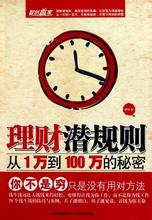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英国的《金融时报》这年说,“中国式的自由企业试验看起来是有效的”。地方官员也说,“生产有大幅度增加”。成都的自由市场和全国的其他自由市场,都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它们的售价要比国营商店高,然而却比国营商店更受欢迎,原因也许是因为自由市场上卖的东西比较新鲜。 自由市场是在四川省中正在进行的一场小小的经济革命中最明显的表现。自由市场使得昔日死气沉沉的街头变成了活跃的商业活动中心。这项试验不久就会使全国的工农业管理得到改观。 四川经济的活跃景象,在1980年要远超过北京。前一年的3月,重庆(重庆当时还属于四川省管辖)26家国营农场成立了“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收入。这个从业人员有9 000人的公司以生产和加工牛奶、水果、淡水鱼和茶叶为主。建立联合公司的目的,是因为过去这些国营农场只生产原料,赤字累累。但联合经营之后,这些国营农场的经营方式转变成了从加工到销售在内的综合性多种经营,一下子就使得几近停滞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活力。这家公司虽然只成立了一年,但1979年盈余高达170万元。工人的工资也从国营农场时的每月40元增加到了50元,甚至一些人年底最高还有200元的花红。 四川省不声不响地试图与沿海的商业中心比如广州或者上海一比高下。省当局此时也成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委员会,以便向海外推销四川的产品。一些外国公司也表示对在四川做生意感兴趣。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四川这么开明,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自由市场。上海就有一些居民不断地投诉自由市场,说他们现在“基本在臭气中生活”,并且抱怨说有摊贩出售劣质食品。江阴路上的一条小路,由于上班的人和赶集的人发生冲突,已经发生了几起打架事件,偷窃也时有发生。 由于议价商品价格被有限度地放开,价格问题也成了投诉热点。国营商店也参与到争购农副产品的行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一些产品价格只升不降。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这年出台了一个严厉的规定,规定不准在贸易场所以外交易、不准在一些闹市设摊、不准干部职工(甚至是退休的)搞“贩卖活动”,外省来的也受到严格的交易限制,工业品不准在集市交易,私人甚至不准印照片和各种印刷品。当然,“投机倒把”也在严厉禁止之列。 再过一些年,“投机倒把”这条罪名就将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市场经济,现在虽然只是被撕开了一个小口,但这个潮流,却再也挡不住了。正如金奇(James Kynge)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 此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营销”一词,只有“销售”,但营销的确正在逐渐从商业活动中萌芽。一些外国公司现在正在努力进入中国,中国的市场和商业环境,也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这年已经开始有人在报纸上讨论商业道德的问题,认为“在加强政策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遵守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一位叫罗浥成的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商业根本没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这位作者在《文汇报》上侃侃而谈,最后希望商业部门的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以后的中国商业社会已经不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了。 1980年,改革初期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还有很多,但商业社会已经逐渐地在萌芽,而且看起来“市场经济”这个刚破出“冻土”的幼苗,长得还很快。 这一年,一个叫梁国坚的年轻人结束了在广西苍梧石桥镇和一些“革命红小鬼”一起日晒雨淋的日子,考上了湖北医学院。在浙江,一个叫谢宏的15岁少年离开家乡台州来到杭州,成为杭州商学院最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正在大学的教室里憧憬着窗外的未来。日后,他们将分别创建在中国市场上足以和外资企业抗衡的索芙特公司和贝因美公司。这时的宗庆后已经是一位销售员了,不过卖的还不是他日后创建的品牌“娃哈哈”。 康佳集团这年在深圳成立了;美的集团也开始进入了家电业,不过他们用“美的”这个品牌还要一年后;广东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也成立了,日后,它将叫做“TCL”;美国国际集团开始重返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代表处,成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的首家代表处。日后,它旗下的友邦保险将会是第一个获准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保险公司。 在大洋彼岸,阿尔文·托夫勒写了一本《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日后将风靡中国。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在这年12月8日遇刺身亡,不过在他逝世很多年后,他的歌才会传入中国。 南京一家工厂这年生产了一种叫蝙蝠牌的电扇,在销售上遇到了一些麻烦,现在,需要有人来帮他们“策划”一下;广州则发出了“商业网点恢复难”的感慨。 年底,法新社的记者夏尔·安托万·德内夏这样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已经使他的国家走上了逐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向不发达现象开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