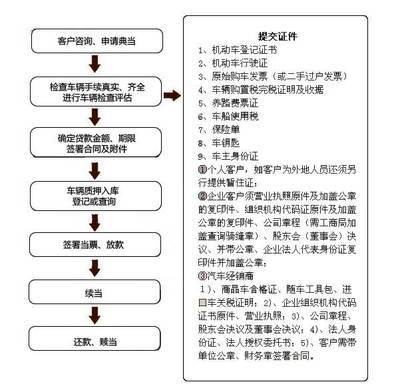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其实有两重涵义。首先,在现象的层面,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由他经历过的事件(记得住的和记不住的)串接成为一部“个人史”,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当一个人要寻求他自己生命的价值时,他便立即意识到这部非他莫属的个人史之重要性。若不如此,他的生命就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了。其次,在意义的层面,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由他体验过的意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串接成为一部“情感史”,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在这部情感史的尽头,是生命终结时可能呈现的意义(最初的或最终的)。生命的意义,有些人很早便感悟到,有些人很晚才感悟到,还有一些人——或许他们数目极多——至死也不曾有所感悟。
上述的两重涵义是纠缠在一起的,我称之为“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我们经历了的事件,未必当时就呈现意义。对我们不呈现意义却被我们经历的事件,我们对它们“无动于衷”。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意义往往必须在一系列事件之后才渐渐呈现。另一方面,由于那些被我们称为“本能”或“直觉”的生物性质的演化,意义一旦呈现,往往成为未来事件的预兆。 最近几年,尤其是2007年以来,我熟悉的年轻朋友——他们多数已经毕业且在财经行业有了收入较高的工作,以我的观察,他们的困惑正逐渐从物质生活方面转入精神生活方面。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之后,对他们而言,所谓“发展”,究竟是指什么呢?1923年圣诞节,鲁迅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面对一群年轻的知识女性做了一次演说:“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是易普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的主角。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知识界,那出戏剧和它的主角,可说是“追求进步”的象征。鲁迅继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多年来,我始终感受着鲁迅这一演说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想到的首先是那些尚未走出温饱不足状态的中国人——他们的发展机会和生命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如娜拉一样,不甘愿继续生活在旧的传统里,他们走出农村,在城市里寻求新生活并感受新的痛苦。然而,如娜拉一样,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出走之后又怎样”。据我观察,他们绝大多数人选择(或别无选择地)模仿更富裕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就让我感受到鲁迅演说的另一重影响:作为“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经济学家,我们还应想到的是那些已经走出温饱不足状态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他们的发展机会和他们难以避免地要寻找的人生意义。富裕之后又怎样?我们的富裕之梦,醒来却发现是了无意义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不是吗?是吗?经济学家的座右铭是“没有免费午餐”,所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询问:“富裕的代价是什么?”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回答下面这一问题:“一个人要多么富裕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最终需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经济学问题:“经济发展的合理限度在哪里?” 我所谓“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大致而言就是由上述的“富了之后又怎样”这一类问题引导而来的。这一问题,先儒谓之“安身立命”问题。在传统尚未瓦解时,中国人早已将这一套安身立命的办法缩写为《大学》四字“修、齐、治、平”。可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却在西方文明100多年的连续冲击之下瓦解了,虽然我们仍可争论诸如“中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的传统”以及“什么是传统”这样的问题。 我们姑且称当代中国人是生活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转型期的中国人。此时,一个中国人怎样才算是安身立命了呢?注意,假如一个人完全不在中国传统之内,则汉语所谓“安身立命”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没有意义。取而代之,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我们充其量只能谈论一个人的“幸福”,或他的“主观幸福感”——这是一个足以连接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方智慧的观念。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关于“主观幸福感”已有丰富的阐释。这一思想传统又由当代的脑科学研究者们加以实证并细致化,以致我们能够提出斯密曾反复强调过的这样一个重要得几乎就是同义反复的命题:主观幸福感的特征,甚至唯一可感觉的特征,是“内心宁静”。 若要一个人不出世且恒久地处于内心宁静之中,虽很难,却是无数主静的实践者的理想,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市场里,熙熙攘攘,为名利权势而来,为名利权势而往,何处求静?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上述命题,虽只是同义反复,他们仍不愿相信幸福的唯一特征是内在的安宁,或曰“心安”。 其实,数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如何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使多数中国人可以有安心之所?(汪丁丁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