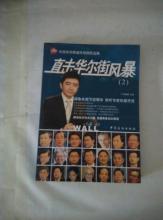系列专题:《风暴中的瞭望者:直击华尔街风暴2》
虽然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在避免利益冲突问题上都有明确规定,但SEC的调查显示,一些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谈。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独立性。而批评家们更是认为,穆迪和它的竞争对手标准普尔及惠誉其实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帮凶。 《纽约时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向人们展示了债券评级是一种复杂的专业过程:一个名为ABC的债券池摆在穆迪的前面,所有的按揭贷款都是次级贷款,而穆迪没有可能看到每一个贷款人的文件,更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以证实贷款人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它能做的就是使用自己的数学模型,依据贷款人的历史行为分析进行评价。对于穆迪来说,它们面对的贷款人正处于美国房地产业最狂热的时代,必要的规范和风险控制都被抛到了脑后,而这样一个行为,如果做一个国人熟悉的形象的比喻,就是用“三亚的气象资料去预测哈尔滨的天气”。 在2006年,美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忙着做和房地产有关的生意,穆迪公司的分析师们通常只有一天的时间处理相关的数据。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些次级贷款“有点不那么可靠”,但是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大部分贷款人是为了取得自己的第一套住房,这也许表明,不到万不得已,贷款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房产。 于是穆迪给出了3个A的评级,投资银行则专门成立了负责这部分债券销售的公司,由它们买下这些按揭贷款,然后向外发行债券。投资银行想让穆迪知道的是,只要给了ABC高评级,它们的债券就畅销,它们所做的一切就有利可图。 在上面这个AAA债券的生产线中,信用评级机构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经不无讽刺地说,世界上有两大超级力量,美国和穆迪。 于是,在那样的一个投资狂热、风险控制被漠视的年代,这些盈利越来越丰厚的中介机构不仅没有发挥自身的作用,反而成了疯狂市场的一部分。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表现并不是最可耻的——人们回忆一下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明白。 早在2007年,穆迪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丹尼尔就意识到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在2007年10月给公司董事会的报告中,麦克丹尼尔明确告知管理层,公司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忽视评级质量,而是在对评级质量进行惩罚。发行人要高评级,投资者不想评级下调,银行家在玩短视的游戏,在此基础上的恶性竞争已将整个金融体系置于危险之中。

国会从标准普尔和惠誉公司员工那里获取的文件更让人吃惊。一位在标准普尔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员工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可以评级,哪怕它是头(被结构化过)母牛。”另一位员工说,“评级机构创造出一个更大的怪物——债务抵押债券市场(CDO)。但愿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富裕地退休了。” 穆迪公司的员工对于自己的工作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五 金融危机拷问美国消费文化 把眼前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仅仅说成是“美国靠借钱发展的模式”出了差错,只是窥豹一斑之言。我们透过借债危机看到了经济制度的危机,同时也透过经济制度的危机看到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危机。当今在美国,不仅是个人靠借贷来超前消费,而且整个国家也是靠举债过日子。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在助长这种存在方式,一直在说明这种存在方式是合理的、正当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已构成了当今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在这种美国人的存在方式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间看到其内在的联系。 自己的储蓄率太低,完全靠美元的霸权维持运转,中国有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