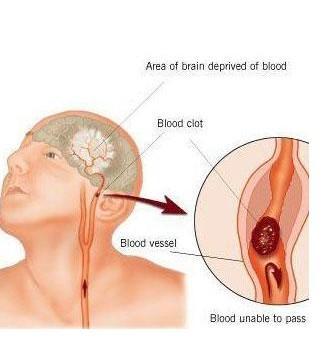这个院子的简陋条件曾经让李丽丹有些担心,但当血液在透析机里循环后,她全身都放松了,“那种感觉很舒服,又想活下去了”。在这里,她想透就透,不再害怕花钱。
对魏强而言,他还面对这17个人的管理问题,他深知透析的危险,而且也在考虑个人的死亡会对集体造成的影响。为此,他草拟了一份入股合同书,合同里规定了2万元的股金,此外还注明: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一切问题(包括死亡),都与合伙人无关,一切自行负责。 所有的合伙人都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对他们来说,死亡并不陌生。 钱,始终是个难题 这个自助透析室曾经换过3个护士,她们的月工资呈递增趋势。 第一个护士来自农村小诊所,不是专业的透析护士。魏强上机后遇上停电,护士慌了,摇泵摇得太快,血路里的血流回了体内,空气也进去了,魏强当场就翻了白眼,喝了点红糖水后才缓过劲来。 第二次的护士倒是很专业,但是三河市卫生局查处小院时,护士怕被吊销执照,走人了。没人扎针,他们几天没有透析了。想去医院,又心疼钱。 熬到第三天,魏强决定自己试试。牙签一样粗的枕头扎向动脉,扎了6次,胳膊上的窟窿像筷子那么粗。这天他没扎上,第二天早上,在一片血肉模糊中他终于成功了。 相比其他病友,王新阳则幸运很多。2004年,王新阳的档案从学校调入当地职业介绍所,加入了医疗保险,首都优越的医疗保障系统将为他承担85%的费用。 现在,王新阳在指定的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透析,每次透析,自己承担15%,差不多100元不到。 小院里曾经聚集的17个人,随着各地相继推出的医保优惠政策,一些人的境遇发生了变化,他们渐渐离开了,剩下10个人相依为命。 来自三河市的潘雪峰曾经也是小院的一员,现在,他可以躺在燕郊人民医院血透室内,享受免费透析的优惠政策。 2008年8月,当地政府出台了《三河市减免慢性肾病患者透析费用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具有当地户口的低保人员、优抚对象及持一、二、三级残疾证的慢性肾病患者免除透析费用,其他慢性肾病患者减除50%的透析费用。减免标准为每人每周不超过2次的单纯性透析费用。超出部分还可以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 在2009年的三河市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尿毒症被列为13种特殊门诊补偿,可报销80%,最高额度为1万元。这些政策的实施,让潘雪峰们离开了白庙村。 好运气总是有些原因的。三河市去年财政收入高达28亿,经济实力超过河北的其他市县。而与之相邻的大厂县,去年财政收入仅为4亿多,该县的尿毒症患者每年最多只能报销3000多元。因此,大厂县的病人赵春香不得不坐着三马去小院透析。 介绍李丽丹入股的山西老乡也入了医保,回去了,那个老乡是个运城人。魏强的家乡也有医保,但只能报销50%,还必须去离家乡很远的呼和浩特的大医院里进行透析,他还是付不起那个费用。3月4日,向透析机提供纯净水的水处理机的水泵烧坏了,没有净化水,血液透析就无法进行。那天,原本有4个人透析,但剩下的水只够一人使用。大家让最难受的赵春香用完了最后一点纯水,这是他们的规矩。
幸运的是,当地一家教会当晚就捐助了1万块钱。他们连夜调试,最终在凌晨把水泵给修好了。 3月底,面对最早来此采访的《京华时报》记者,魏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困境,或许不是坏事,他们只是想活着等到纳入医保的那天,“不是穷缺钱,而是要活命”。 去留风波 不过,媒体的介入带来的不是转机,而是危机。见报后,通州区卫生局便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 “经查实魏强等10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许可,从事血液透析的活动。上述活动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取缔。”这份公告现在还贴在透析室门口。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和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也带着通州区卫生部门的相关人员来到小院调查。一位领导当面指责这些病人是“无知者无畏”。 “如果有钱,我也会找条件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这里肮脏,我都承认。但依靠这些东西,我活了6年,要是没这些东西,我6年前就死了。”魏强高声说。 左右为难的通州区卫生部门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4月2日下午,通州区政府联合市卫生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小院里守候的记者都去了发布会现场。 与此同时,小院里的3台透析机被执法人员异地封存,搬上卡车运走了,简陋的透析室门窗上贴了药监部门的封条。 56岁的老太太胡爱玲落泪了:他们搬走的是我们的“肾”呀。 一段时间内,他们将获得免费透析的临时救助。10名因无法负担医药费用的患者领到了每人一张的免费透析卡,目前能使用11次。 通州区及市卫生部门认为,此举是在维护法律尊严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折中之举,同时坚持认为,“患者返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病人的想法却更直接:哪里能活下去,就活在哪里。 通州区卫生局的一名相关负责人表示,民间透析室的出现是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当造成的。现在在此透析的均为外地患者,邻居城市或者各地执法机构的“对口”工作仍未到位。
小院里的第三个护士也走了。这名护士是他们花了2200元的月工资请的,没有执照,但是素质和技术都不错。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来下达取缔通知时,一名警察对护士说:“你应该考个资格证,没有资格证是犯法的。”他们走后,护士便向魏强提出了辞职。小院的房东崔先生也表示不能留他们了:“我的压力很大。已经来查过我的房屋出租证等东西了。肯定不能再久留了。” 4月3日上午,他们被安排到宋庄卫生院做体检。当天有5个人要做透析,但是卫生院说只管体检,于是病人们就追着有关人员的车去了卫生局。最后,对方答应,下午5点前给安排医院。 这天下午,这群病人和记者坐在小院里聊天。他们黄灰色的脸庞和格外温和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前者是病痛和毒素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迹,后者则发自于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人与人温情的渴慕。虽然身体上极度脆弱经济上极度贫困,但任何一个走近他们的人,都会透过一个个心酸的故事看到他们站在生命面前无上的尊严。 黑龙江人陈炳志在小院里外号“陈院长”,这天兴致高昂,向四周炫耀他的新球鞋,这是他花75元买的。下午刚刚从医院透析完的王新阳回到小院,感慨“活着就好”。 孙永琴看着透析室上的封条,里面还封着她2000多块钱的药品和针具。这对她来说是笔大款子,为了让她活下去,娘家的父母欠了10多万的债,她的丈夫不愿出钱,“去了趟公安局(调解)”后才每月愿意出点生活费。 老太太胡爱玲在院子里收拾废品,她以拾荒为生。本来她这天上午就要做透析,脸上早已浮肿,她让记者用手在她脸上按按,一个坑半天没有平复。 下午4点半,卫生局那边还没有给回复。胡爱玲已经开始憋气了,陈炳志也收了他的好兴致,愈发沉默起来。大风卷起灰尘,沙粒撞到了绿色掉漆的铁门上,“哐哐”作响,小院里已经没有了那股乐观的气氛,魏强谨慎地说:“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 5点过后,当天急需做透析的病人才在迟迟等待中获知了结果。小院里又开始沸腾起来,大家张罗着送病人去做透析。在这个大团圆的结局中,王新阳却一脸焦躁地站在小院里,满脸写着担心:卫生局为什么非要拖到现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