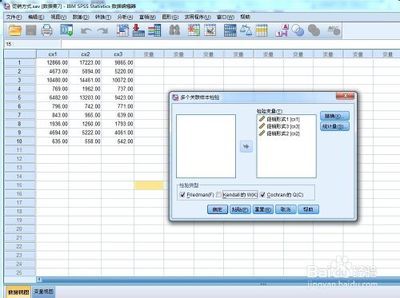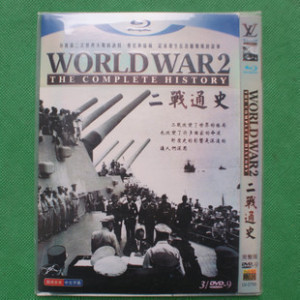转化 在武汉大学,1949年5月,对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面临着一个众所周知的共同选择:离开这座国民政府即将丢失的城市,还是选择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但关键还是他自己的决心。 刘绪贻仍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的这个“历史污点”,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在1947年6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享受了国民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480块银元的薪水足以支付这个教授家庭所有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尽管这最后的中产生活很快就被暴跌的金圆券和武汉市接连翻番的物价指数击垮,但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刘绪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沿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仕途方向,先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任职,后又通过老师费孝通和吴景超的关系转到经济部工矿调解处工作。国民政府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后者是一个“肥缺”。刘绪贻1944年放弃这个职务去芝加哥大学就读社会学系,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失望,这个知识分子跟体制显得格格不入。 96岁的刘绪贻如今坐在武汉大学的家里,对本刊回忆说,“当时经济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我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我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这事之后,我觉得再在机关里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 他1942年加入国民党,并非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是事出有因。“我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的时候,单位有两个共产党地下成员暴露,被国民党抓了,社会部部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的人,出于政治考虑,他要求凡是想留在社会部工作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刘绪贻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并不等于他了解共产党,在他动身去美国前,“我仍然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不过是个争权夺利的政治组织”。他回忆说:“我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 刘绪贻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些“中间特征”已经足以使他成为新政权尤为重视的统战对象,说服工作从刘绪贻离开武汉到美国的那一天就悄然开始了。 在众多个人选择的时刻,对解放区的宣传一直是让更多人了解新政权的窗口。“这个工作从解放前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解放后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吴仲炎接受本刊采访说,“武汉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以及长期在美国从事病毒学研究的科学家高尚荫,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但对更多共产党想要争取的对象,如何接近并转化他们呢? 1947年在美国主动接触刘绪贻的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犹太学生。在海外华人学生中,讨论国事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举动,学生们热衷于“站队”,留学生自动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刘绪贻对这位主动提供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和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杂志给他的外国人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个美国学生是学俄文的,因此去过解放区,他似乎知道我对延安的好奇,讲了很多他在延安的见闻,和我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耳濡目染的那些完全不同。”这些潜移默化的接触的确让刘绪贻对共产党的态度大为改变。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名美国学生是受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 组织

在解放前的武汉,不止一个组织做像刘绪贻这类教授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解放前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已经扩大到500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100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组织结构,即使对于某个进步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汉大学来说,除了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驻武汉大学支部外,大学里,还有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还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除此之外,武汉大学里还有不少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形成竞争关系的组织力量,比如远征军退伍复员后的人,国民政府承诺一些立过战功的士兵可以到国立大学继续深造,还有数量不少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曾任武汉地下市委委员的刘实接受采访时说,“这些组织除了要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做教师工作上也竞争得比较厉害。” 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再次展现了它的特殊性,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分有极为复杂的一面。“解放前的武汉大学不像人们想的那种校园状态,它的人员非常庞杂。当年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往后方撤,武汉大学在乐山时,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成都五大学联谊会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抗战结束后,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学生和复旦学生随着武汉大学迁校来到武汉。”中共武汉大学地下党成员、后来担任江汉大学校长的张薇之向本刊回忆说,“武大实际上在一段时期,成了一个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来要去上海因路费问题滞留武汉的人,都住在武汉大学里。这样,往往上海学生找上海学生、山东的找山东的,一时学校里‘同乡会’很多。这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帮派气息和社会气息很浓厚。” 拉帮结派并不被当时武汉大学的知识青年们视为陋习,相反,同乡会帮助那些刚到陌生城市的年轻人迅速解决居住和就业问题,它也成为在学校发展社会运动的便利。但这些同乡会依靠各自的私人关系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被地下党迅速发展成为大量的外围组织,并构成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张薇之认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武汉大学开展活动、发展学生外围组织和教师外围组织的顺利,在于地下党充分利用了中国旧有的私人关系和社会网络。 共产党再一次做刘绪贻的工作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老乡关系。“我回武汉一年后的一个暑假,武汉大学有个工学院的讲师蔡心耜突然到我的单身教师宿舍找我,他带着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说要和我一起打桥牌。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两个,那个同学跟我也只是同校而已,但他们提起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乡朋友,说从他那儿知道我桥牌打得好,就过来一起玩玩。”刘绪贻回忆说,“后来蔡心耜就常来我家,直到1948年底传言共产党已经决定过江的时候,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说自己是共产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叫‘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的组织。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刘绪贻加入“新教协”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做校长周鲠生的工作。为了稳定周鲠生,“校教协”和“新青协”一起为这位老校长的60岁大寿组织了一场晚会。 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下设两个支部:教授支部和讲师助教支部,两个支部下设三个小组,但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只对它们的上级联系人负责。“新教协”在1949年二三月间的工作任务很明确,“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当局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这两个支部要把各自的材料写出来,交给蔡心耜,蔡将这两份材料汇总,上交给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