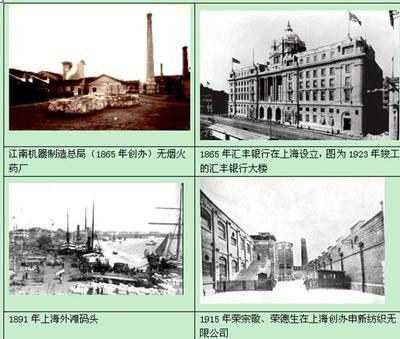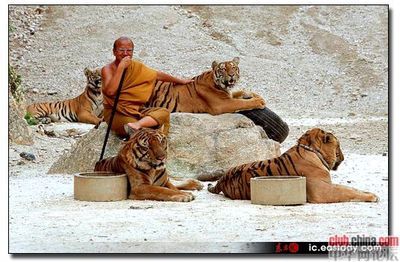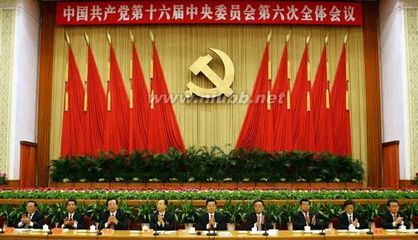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本文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公共政策的“偏向本性”角度探讨公共政策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偏向性,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应当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分别扮演“不和谐”偏向性、“不和谐”引导性、“不和谐”融合性等角色,才能使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在该进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和谐社会 公共政策 偏向性 引导性 融合性
引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新命题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到了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认识上的质的飞跃。然而,作为被称作是“政府手脚”作用的公共政策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又应当有哪些变化、充当哪些角色以及发挥哪些作用呢?以下笔者做一点简单的分析,供大家探讨。
一 公共政策的偏向本性
根据戴维8226;伊斯顿的观点, “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进行的权威性分配, 即通过政策实施, 让一部分人享用一资源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对该资源的享用。”[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具有其天然的偏向本性。而托马斯8226;戴伊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简洁的公共政策定义:“政府选择要做或者不做的事情”[2]。也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是政府,而政府本身就代表了一定的利益群体,因此,其所制定的政策没有偏向性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政策真的具有“偏向本性”吗?
对于公共政策“偏向本性”的怀疑者很可能在于执着于公共政策中的“公共“二字,既然是“公共”的,又如何会产生偏向性呢?对于此,首先我们暂且不说“公共的”是否就是“大众的”,我们先讨论是否真正的存在“公共的”。对此,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E·林布隆认为“严格地说来, 人人共享的利益也许并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局部利益。”[3]笔者认为:首先,公共政策产生的缘由就在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而公共问题的产生则是由于公共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引起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公共政策本身就是针对着公共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去的。正如上所言,公共政策是针对公共利益进行调整以解决公共问题的一个过程,归根结底是要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对此,肯尼斯·阿罗也认为:“由于多元利益间冲突的不可调和性, 公共利益在一个冲突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说它的存在甚至是一种神话。”[4]前面已经提到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行为的一个过程,而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公共问题,正是由于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与此同时,某些群体又获取了不在当时公认的社会道德或国家法律法规规范之内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问题是作为冲突的多元利益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结果的。
由此,我们可知其实公共问题的产生不过是利益冲突的一个过程,而利益的冲突必然要涉及利益集团的权力角逐,在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的制定过程不过是平衡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一个权利角逐过程。正如我们看到的,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而这种紊乱正是由于权力角逐造成的,权威、说服、威胁、交换等权力角逐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拉斯韦尔也认为:“政策的意义是为了某种目标、价值及实践而设计的计划;政策的过程包括一种认同、需求及预期的制定、发布和执行过程”。[5]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公共”是相对的,公共政策具有其天然的偏向性,至于其偏向于哪一方,其实很容易可以分析出来,肯定是偏向于社会主导权力掌握者的那一方,至于某些政策看似倾向于非主导者,其实从根源上来看,还是偏向于主导者的。总的来说,公共政策的“偏向本性”是可以肯定的。
二“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党的执政过程中,必然要充分反映广泛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就必然要充分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党在新时期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就是充分反映了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简单的说就是要清除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做为“政府手脚”的公共政策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戴维8226;伊斯顿所认为的,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进行的权威性分配, 即通过政策实施, 让一部分人享用一资源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对该资源的享用。同时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具有天然的“偏向本性”,而公共政策又是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因此政府的偏向性便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性。而当前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就必然要充分围绕这个新命题来制定和执行。因此,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政策就必然要偏向于解决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保障相关群体的利益,也即“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清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逐步达到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生活的稳定和幸福。
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主体身份和公共政策的偏向本性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方向,而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又要求和决定了“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引导性
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什认为:“考察政治体制的性质是理解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途径之一”[6]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了最广泛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以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和谐社会”的指引下,不仅应具有“不和谐”偏向性,还应该具备“不和谐”引导性。
如上所述的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可以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使社会趋向和谐。然而,公共政策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还可以引导方向,也即具备引导功能。任何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个个的去解决都是永无止境的,问题会不断产生。大禹治水重疏导而非堵塞,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世间万物莫不如此。仅仅靠公共政策的偏向性,发挥其对“不和谐”因子的管制功能,也许可以较好的解决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不和谐问题,然而,却较难很好的限制即将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下,不仅应当注重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而且应该注重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引导性,利用公共政策来引导社会“不和谐因子”自动向“和谐因子”转化,疏导社会“不和谐因子”汇向“和谐大潮”中去,这样才可以很好地发挥公共政策的消除社会不和谐因子的作用,使社会可以很好地保持稳定和谐。此即“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引导性,引导不和谐因子向和谐因子转变,可以以逸待劳,充分消除不和谐因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不和谐”融合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时期下的新命题,如上所述,公共政策是“政府的手脚”,公共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具有天然的“偏向本性”,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应当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偏向性作用。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注重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偏向性,注重公共政策的“不和谐”引导性,还应当充分注重公共政策的“不和谐”融合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铺平道路。
所谓的“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共政策的“不和谐”融合性,指的是公共政策不仅具有偏向性和引导性的特点和作用,还具备针对“不和谐”因子的融合性作用。我们不仅应当使公共政策具有“不和谐”偏向性和“不和谐”引导性,还应该进一步使其具有“不和谐”融合性,将社会中的各种“不和谐利益”“不和谐因子”融合到“和谐利益”“和谐因子”中去。对于“利益融合”,美国学者德博拉·斯通在其《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一书中有相关阐述,具体如表:
(政治竞争的修辞特征)[7]
德博拉·斯通认为,一种小的、自私的利益是可以主导较大的、美好的利益的,表中的“强而坏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因为其内在地邪恶或者不合法而成为坏的。它们是坏的,仅仅因为它们强大到足以将那些更加合法地利益挤出去。也即从根本上来说,二者不是“质”的问题而仅仅是“量”的问题,二者并非“誓不两立”,而且二者还可以统一在一个体系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公共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针对“不和谐利益”的“融合性”功能。
公共政策不仅应当偏向于社会不和谐因子的清除和引导社会不和谐因子向和谐因子转化,还应当可以针对社会不和谐因子,融合社会不和谐因子,彻底消除社会不和谐因子。因此,我国在“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制定公共政策地过程中不仅是要具有“不和谐”偏向性和引导性,更应该具备“不和谐”的融合性,将“不和谐利益”融合到“和谐利益”中去,在清除中削减,在引导中转化,在融合中彻底消除,这才是大道。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从根源上发挥了公共政策在“和谐社会”命题下的作用,我们才可以真正地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小结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8]而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执政的重要手段之一,必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偏向本性表现为“不和谐”偏向性、“不和谐”引导性和“不和谐”融合性。从偏向性到引导性再到融合性,层层递进充分挖掘和发挥政府公共政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党、政府及人民大众的的目光聚焦到社会和谐上,公共政策的角色也随之有了变化,正如哈马贝斯所言:“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市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9]
[1][美]戴维8226;伊斯顿.王浦劬译:政策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T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2):2.
[3][美]查尔斯·E·林布隆. 朱国斌译. 政策制定过程[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4][美]肯尼斯·阿罗. 崔志远译.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5][美]哈罗得·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加]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1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7][美]德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M].2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曾庆红.关于国内形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学习时报.2005年3月7日第275期.
[9][德]哈马贝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1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