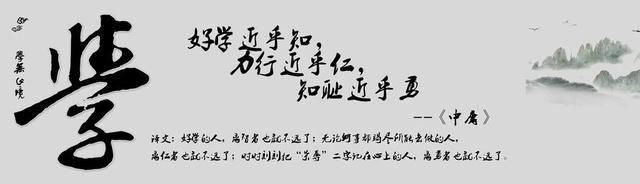第三个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人的精力主要不在福利制度的改革上,对战后福利制度改革与重建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制度准备远远不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英国就预料到了战后重建任务的艰巨性,成立了“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英国不管部部长、国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于1941年6月就正式邀请贝弗里奇出任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授权该委员会调查英国福利制度现状,全面制定一个战后重建的福利制度。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11月贝弗里奇完成了这个全方位的福利改革报告,为英国设计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的福利体系框架。英国政府几乎完全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随后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宣布正式建立福利国家,于是贝弗里奇被后人誉为英国福利国家之父。法国则不同,戴高乐在远离法国本土的英伦三岛创建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孤悬海外长达四年之久,这些法国精英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如何“重返”法国上,而较少放在如何“重建”法国上,于是,战后福利制度改革在这个“流亡总统”的案头上很难像英国那样很早就提到日程上来。如果说英国福利国家之父是贝弗里奇的话,法国福利国家之父就应该是皮埃尔·拉罗克(Pierre Laroque, 1907-1997)。拉罗克早在1928-1930年法国社保改革立法时就曾参与起草工作,是个社保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英国参加了抵抗运动和诺曼底登陆。法国解放之后,直到1944年9月临时政府劳工部长亚历山大·帕罗迪(Alexandre Parodi)才开始委托皮埃尔·拉罗克议员着手制定社保改革方案,匆忙草拟的方案几乎完全参考了贝弗里奇报告的精神,试图制定一个“三统一”的福利制度,1945年10月4日据此立法建立了“普通制度”,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准备仓促,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之中,在建立第四共和的宪法即将在1946年秋天出台前夕,不得不在1946年5月22日立法中予以妥协,确认了“特殊制度”的独立性,这标志着1945年10月4日立法的流产与失败。表面上看,法国改革的妥协是当时不同力量对比的结果,实际是德国俾斯麦模式与英国贝弗里奇模式之间的妥协。
与英国的贝弗里奇相比,要说法国的拉罗克有成功的话,那就是在其主导制定的“法国社会保障方案”(le plan français de Sécurité sociale)中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替代了1928-30年立法中使用的“社会保险”概念;除此之外,拉罗克的思想和贝弗里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1944年3月15日制定的工作计划里面。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拉罗克的思想脉络及其妥协过程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5个立法上。这5项立法可以分成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10月4日的立法。这个立法的第一章规定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旨在确保工人及其家属抵御和防范所有由自然风险所可能导致的收入减少,覆盖所有包括生育和家庭等在内的全部费用……”;还规定,以前的旧制度可以保留,但是要有改革的预期,要逐渐扩大社会保护的范围。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个立法所建立的“普通制度”却没有扩大到其他人群,而旧制度却保留下来,第二阶段的立法对“特殊制度”的合法化作出了规定。
第二阶段主要是由4个补充性质的立法构成的,他们是1946年5月22日关于普及社会保障的立法,1946年8月22日关于扩大家庭津贴的立法,1946年9月13日关于全民建立养老保障的立法,1946年10月30日关于“普通制度”覆盖全体人口和抵御风险的立法。
4.法国福利制度术语的演变:第三只眼看法国碎片化福利制度的起源
如前述,法国人将formules(“格式和方式”)用作每个碎片régime(制度)的含义,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所有法国人的著作和官方文件里(即使他们用英文写作),在使用“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时,使用的是Système ,例如“Le système française de Sécurité sociale”;但当意指这个制度之下的所有小制度时,则始终使用“régime”这个词,从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与著作使用“système”;相反,在法国人描述欧美任何一国社保制度时,从不使用“régime”,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使用“système”,例如,法国人说“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时,使用的是“Les assurances socials en Allemagne”;换言之,法国人将“régime”作为描述法国社保大制度中的诸多小制度时的唯一术语。例如,法国人在讲他们的“四个制度”组成(普通制度、农业制度、自由职业制度、特殊制度)时,在讲到四个制度里大大小小的“小制度”时,均使用的是“régime”,如同法国人在使用社保费的“费”时,唯一使用的术语是“cotisation”(强调“分摊”的含意,强调个人的“责任”和“无奈”,在英文里没有这个词),而决不使用“contribution”(同英文一样,法文也有这个词,具有“贡献”的含意,强调个人对制度“奉献”和“捐助”),就是说,在法语里甚至在整个拉丁语系,他们使用的是cotisation这个词,不用contribution这个词,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相比,二者的用词的差异性对理解社保制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法国人在讲法国四个社保制度及其以下的各个小制度时使用的词汇不一样?从前述法国社保历史可以看出,法国大制度下的多如牛毛的不同“制度”之所以使用的“régime”这个词(相当于英文的regime)是非常恰当不过的一个专有词汇,其他术语确实难以替代,其原因主要是这个词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除了其核心含意之外具有不确定性,而只是一个框架。“régime”确定的核心含意是难以扩展(élargi)、难以延伸(étandu)、难以普及(généraliser),应该是更加强调权利(droit),就是说,“régime”的含义边界要小于“système”。我这里如此辨析这个术语,目的在于,“régime”在这些核心含意不变的前提下,它具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个特征适应了法国几百年来社保“制度”的需要,能够基本准确地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法国社保的“制度”变迁,所以,在讲述和分析法国社保“制度”时,“régime”成为法国“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术语。早在二战之前,“régime”就被借用并使用起来,那时,法国还没有整合全法的社保立法,在互助性比较明显的状态下,来自于个人薪水的“分摊金”(cotisation)社保制度,在拿破仑法典的理念下,这自然是一个statut,即欧洲大陆法的“物权理念”,属于典型的物权法的思想;就是说,从那时起,使用“régime”来描述法国的社保“制度”就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词。
思考到这里,又想到了福利制度研究中的另一个专有术语“福利模式”。创造并使之流传开来的丹麦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教授(Gosta Esping-Andersen)使用的也是regime这个词,而没有使用model,system或institution等英文法文里都使用的类似“模式”和“制度”含义的词,后来,“福利模式”(Welfare Regime)被广泛使用(缩写WR)。体会起来,好像只能用regime,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在90年代以来的学术著作里,人们已经找不到其他的用法了,几乎行内大家都已经使用welfare regime。尽管在中文的语境下,我们只能将之称为“福利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转换回去的话,如果换成welfare model或别的词的话,显然感到味道不对,至于错在哪里,好像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比如,法国人从来就将法国的四个退休制度用四个régime来表示,这是专用的,从没有人使用model或其他什么词。于是,在中文的翻译中,有学者将法国四个regime译为四个方案、四个计划、四个类别等等,五花八门,在中文里很难找到对等的一个词汇。我之所以将之译为四个制度,虽不理想,但也没有更好的译法。说得再远一点,组成法国社保制度的四个régime,不是什么广义的四个模式,而是四个具体的“客观存在”,这四个statut(英文是status)不是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进行主观选择的,法国的这四个statut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要改革它?很难,政府很无奈!舍弃它?也很难,法国人离不开它!继续保留它?也很困难,因为这个四个“客观存在”既是中央财政的包袱,又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导火索。所以,法国的WR是个烫手的山芋。
这里从辨析法国社保制度使用不同词汇的角度来强调法国社保制度的特殊性,绝不是吹毛求疵。法国用于社保方面的术语经常看到和使用的大约有三个:第一个是La protection sociale,它一般指“社会保护”,是不确定的普通泛指,例如法国人在讲法国和外国社会保护制度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即le système de protection sociale。我们中文里也可将之泛泛的译成社会保护或社会保障,但绝不应翻成社会保险;第二个是Les Assurances socials,这个专有词汇是专门指法国1945-46年改革之前的法国社保制度,在法文所有著作和文献当中都是这样使用的,我们会注意到,它是复数并是大写,专指当时由许多小制度组成的“法国社保制度”。此外,Assurance这个词是保险的意思,具有精算的含意,所以应该翻成“法国社会保险制度”;第三个词是la Sécurité sociale,我们可以将之译成“社会保障”。法国1945-46年拉罗克改革方案中专门有一条指出,从此之后,沿用了几百年的法国社会“保险”制度这个词不再使用,改为使用社会“保障”制度,把assurances改为sécurité,即把le système français des Assurances sociales正式改为le système français de Sécurité sociale。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实际上这个小小的用词的变化反映了战后法国政府至少拉罗克本人欲整合法国碎片化制度的想法,以减少“保险因素”,增加“保障因素”,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官方用词的变更从字面表达上看也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保险”(assurances)与“保障”(Sécurité)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后者更为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强调国家财政的积极因素。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当年对法国战后1945-46年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英国1941-42年贝弗里奇报告以外,还有1934年美国实行的新政、1936年凯恩斯主义的流行、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等党派以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名义进行联合竞选获胜,建立其首届人民阵线政府,社会党首次出任总理,为争取劳动群众的基本劳动权利发挥了作用)、1944年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在美国费城通过的《费城宣言》(主要精神是强调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在自由、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实现此目标而创造条件应成为各国和国际政策的中心目标)、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等等,等等。当时这些国内和国际大环境造成的气氛和趋势,他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等,对法国重建社保福利制度的理念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和财政支出的作用、强调社会福利制度应实行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待遇等“三统一”。这里要说的是,当时美国通过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概念比较狭窄,专指狭义上的“养老、遗属和残障”保护,而不像法国人使用这个词时涵盖了养老、医疗、家庭津贴、失业和工伤保险等五大项目,这是法国人与美国人在使用social security时存在的差异。对于法国人使用这个概念时包括这五个项目的问题,法国半官方的权威机构“社会保障历史委员会”(CHSS)在其出版的每本专著和研究报告中都曾作出专门的释意。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继续追溯,在用词上还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在1928-1930-1935年福利制度改革的立法中,法国人使用的术语是“社会保险”(assurances sociales),在此之前一次重要立法是1910年,那是法国历史上一次重要改革:首次在全国范围地强制性地将工人和农民纳入到养老制度里面来,那次使用的是“退休制度”(retraite)。1910年4月10日的这部立法是《工人和农民退休制度》,法文是《Retraites ouvrières et paysannes》,简称是“ROP”;随后,1911年7月3日立法、1912年2月27日修正案等,使用的均是“退休”概念。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农民、矿工、铁路工人的“特殊制度”(régime)得以确定和成熟起来,1910年立法确立的《工人和农民退休制度》(ROP)成为现代法国社保制度的雏形,其历史意义相当于1882-84年德国立法的地位。据统计,当时ROP所覆盖的人口情况是,在1000万领薪者中覆盖了将近800万人,而当时的经济活动人口是1250万人(男性和女性合计),1906年全法人口是2100万,1911年是3920万。据法国学者的说法,1911年的法国“退休制度”是le système de retraite,其基本理念和原则是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这个互助就是assurance mutuelle,带有保险互助的性质,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共同发起并负责,而绝没有来自于公共基金的“公共救助”(assistance publique)的含意;但正是从1910年立法开始,国家公共干预就逐渐成为必须的了。
从上述近代法国社保制度用词retraite——→assurance——→sécurité这三次立法时的更替,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法国社保制度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的情况,它反映了法国社保制度及其理念的发展路径:1910年立法的互助性质——→1928-30年立法的保险制度——→1945-46年改革的保障制度,等等。
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法语的掌握和知识十分有限,即使英语也是略懂皮毛;我对上述法文用词及其语意的上述理解和提出的辨析,不一定完全准确,只是从社保研究者的身份,想说明和理解法国人自己对其社保制度和概念的诠释,深层的含义是试图考察和探析法国社保制度“碎片化”的演变过程、历史源头和基本现状,旨在从第三只眼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法国社保制度的某种特殊性。但是,无论如何,一国使用概念术语是有目的的,可从一个侧面看出社保改革的一些脉络。
五、结语:感慨与沉思
1.历史传统:特殊制度与罢工盛宴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由社保待遇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大约有10多次,平均10年一次。这100多年来的法国大罢工几乎都离不开法国铁路工会和铁路公司的博弈。如果以1937年建立法国国铁公司(SNCF)为界,在此之前主要有4次,他们分别是1891年、1899年、1910年和1920年大罢工,这个阶段铁路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水平。当时,铁路主要由6大公司垄断(PLM,北方公司、巴黎-奥尔良公司、地中海公司、东方公司、西方公司),这6个公司的雇员总共是250285人,在此之前的退休金每月大约262法郎,平均退休金替代率是11.55%,1899年大罢工之后上涨到18.08%。1937年4月,这6个铁路公司合并成立现在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简称“国铁”,SNCF,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国家持股51%,其他49%由原来的股东持有,从这一年开始,法国铁路的经营彻底完成了从私营向国营的转变,同时,也形成了罢工的传统,成为法国“特殊退休制度”罢工的导火索。
在1937年之前铁路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罢工的规模要小一些,但自从1937年组建国铁公司(SNCF)之后,全国性的大罢工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影响一次比一次大:1947年是因为工会分裂导致的,1953年罢工的诉求主要是反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引发的,1968年罢工主要表现在席卷全法的红色风暴之中,1986年罢工主要是对希拉克政府日益不满,物价高涨(购买力下降了1.49%)。1995年大罢工是反对于贝政府拟发起的对“特殊退休制度”改革,这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在全法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国性的交通瘫痪整整21天,震撼全世界。2007年11月这次罢工的规模仅次于战后以来1995年的罢工。
细心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样五个特征:第一,在法国铁路工人一百多年的10次大罢工历史中,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罢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工资待遇等,战后引发罢工的导火索主要有两类,其中三次是由于其他原因,另外三次是由于抵制和反对改革“特殊退休制度”引起的。第二,战后以来这6次罢工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比如,1986年罢工参与率是47.5%,1995年是75%。第三,除了这些全国性的总罢工以外,中型的罢工次数越来越密,矛头直接对准“特殊退休制度”的改革,尤其是自1995年以来,几乎每2年左右都在巴黎发生一次铁路大罢工,影响全国的交通秩序,几乎每次都是由于政府欲对“特殊退休制度”采取改革措施或相关的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发生一次大规模罢工。第四,除2007年11月这次以外,几乎每次罢工都是工会胜利,政府妥协。唯独2007年11月这次是以工会妥协和政府胜利而告终的。第五,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日常的小型罢工多如牛毛,非常密集,几乎每月都有数起,笔者为此查阅了2008年1月1日至6月1日主要报纸,仅在巴黎发生的与福利待遇有关的罢工就高达三十多次,这里笔录其主要活动如下:
1月22日法国能源部门、巴黎公共交通公司(RATP)以及法国国铁路(SNCF)职工在巴黎举行全国性的示威,要求提高工资和退休金,“捍卫购买力”;
1月24日全法五家医护人员工会成员举行全国行动日,呼吁提高待遇;
1月24日全法小学教师、公务员和法国电视二台的工作人员举行大罢工,呼吁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
1月30日和2月6日全法出租车司机联合会(Fnat)会员两次停工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要求“全面敞开”出租车和高级包租汽车(VPR)市场和增加出租车数量;
2月11-12日,法航空中管制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待遇;
2月13日全法广播电视系统罢工,要求提高待遇;
3月4日巴黎科学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和科研机构负责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科研经费,反对行政干预;
3月6日几万名退休人员在巴黎和外省同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立即”和“大幅”提高退休金,认为1月份养老金提升的1.1%是根本不够的;
3月18日和4月3日法国中学生和教师在许多地区举行示威和罢工,抗议裁减教师岗位;
4月7日,教育部与师生对话失败,全国高中生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减少教师职位的改革。这是两个星期以来的第5次全国行动日;
4月8日,巴黎中学生联盟举行了全市教师学生大罢工,大约有2万人参加,其中教师有几百名,抗议从下个学年开始取消部分教师职位的改革;
4月9日,数百人在巴黎和外省同时出现集会示威,反对自2008年1月1日以来实行的医疗保险“自费定额”措施。示威者在卫生部大门前堆置了一些药盒,高喊“要健康,不要自费定额措施”,糖尿病人协会和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以及法国共产党等派代表参加了集会;

4月10日法国医疗、外科和产科工会进行全国范围大游行,旨在反对由政府制定的2008年诊所医疗收费规定等。同一天,法国空客公司在几个城市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公司裁员;
4月23日,马赛等一些港口工人罢工,抗议旨在“提高竞争力”的吊车司机等搬运部门的私有化改革措施,港口陷入混乱;
4月24日,法国空客职工举行罢工,总部和分厂几千人参加,旨在反对取消工作岗位,反对出售工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