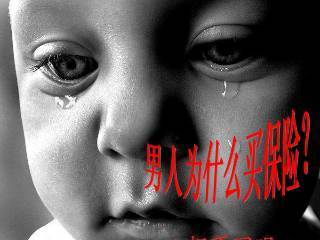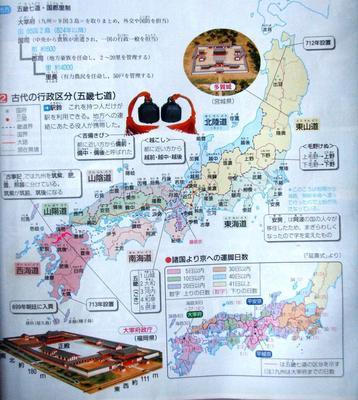我本着大陆人不谈香港事,免得被人认为是大陆人有心来破坏一国两制的嫌疑,但见得任寅博士们就香港是否已被台湾取代,而被中央边缘化谈的兴趣高昂,我也自然的被感染了,也就顾不得许多,提笔上来说上两句。要而言之,香港今日之问题乃实奈其‘东南亚化’所导致,何为‘东南亚化’,我曾为一小文,试论过,贴如左,望诸君批评之: 所谓的东南亚化,其特征表现在,政治领域上是:这些国家依靠专制,通过手腕和领袖的个人魄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让人民摆脱贫困,并保护国民免受内在和外来的威胁。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领袖们用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表述的内容却大同小异的所谓的“社会经济变革”理论。这些国家在政治领域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在遏制社会和政治变革方面可以说是天然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着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同时他们也对西方民主有着莫大的抵触,甚至敌视,他们信奉自由市场原则,但不排除间歇性的基于国家主义或是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反西方意识。同时这种意识体系的政治家们都怀着同一想法,那就是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应该凌驾于其它顾虑之上。而这一原则起到了作用: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东南亚地区及中国的收入暴涨,从东南亚的丛林和贫瘠的中华农村中冒出了一个个欣欣向荣的城市,该地区一下子变成至关重要的能源开采业、制造业、贸易甚至金融的中心。 也正是基于政治上的专制的“社会经济变革”理论,这些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他们总担心于资源下放民间,而使民间力量强大起来,从而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因而这些国家总习惯于用国家安全作为托词,来加以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而当国家掌握过多的固定资产配置权时,就迫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对于为什么这些国家更习惯于将自己演变成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拉动型经济,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却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但这却并不合适于这种东南亚体系,该种体系之所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 因此,也驱使他们更乐于将自己成长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型拉动经济体系,因为这样做付出的社会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一些,他们的“政绩合法性”更容易得到保障。因为要想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对我们的制度的要求相应的就提高了,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必然的高了。但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它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这些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 同时这也跟这些地区的政治哲学有莫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所谓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和新加坡,但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下而上由外而里的观点是怀疑的,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治理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智力还不具备这种由下而上的治理意识基础,那么他们很快活的以具体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予以了抛弃,他们把儒教中的精英主义拿了过来,于是这些地区的执政者以该国家和地区人民中最先进者自居,在这种意识环境中,中央计划也就水到渠成了。 再加上曾经的殖民地历史带给人民和他们自身的伤害,于是他们更喜欢以计划的态度,以国家产业安全为考虑因素,将某些行业以国家产业安全为由加以保护或者以计划的形式予以引导。这样的结果是:国有(如中国和新加坡)或者是官商利益不清的政府特许(比如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过高。从而导致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严重畸形。 在具体的经济层面,这些国家都乐于大力发展房地产将其作为经济支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商业家族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看看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富豪中房地产商的比重就知道了)、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显然这跟儒家意识还是有莫大关系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的“关系学”是很有市场的,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中国的表现来看,在这里: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用,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然而富豪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太多存在的意义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经济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生产业,但东南亚富豪几乎全部出自寻租者而不是这些出口制造业(没有一家具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这一事实,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在特定市场情况下有其价值,但它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却值得我们怀疑。 1、于消费者而言,除了这些企业将获得更多的行政性的行业垄断外,什么也得不到; 2、于企业而言,除了他们在行政性垄断的特权的庇荫下,形成更强烈的惰性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3、于国家而言,正如迈克尔.波特说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而一个个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他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又能够做什么贡献呢。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好象也正在体现这一问题。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样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在对各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全社会谋福利方面(或者是托词)的不幸失败而已。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而且如乔8226;斯塔威尔所说,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蠢到投资于那些富豪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 但这种方法的采纳,却也带来了问题: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也就更丧失了创造性的改善国内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环境;从而导致官僚体系的腐败,而这种制度架构以及管制环境的缺失,将更让他们热中于将经济出口导向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也因此他们长期执政的可能是为未来留下很多隐患,这包括种族关系再趋紧张(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是例证),以及一个受阻于腐败的经济体系。20世纪的东南亚的强人们所建立的体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40年过去了,当年新生的东南亚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早已基本消除,而其中的佼佼者在经济上又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代表其起飞阶段的显著增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做出调整以取得成功将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难题,东南亚过去1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新财富给这些传递富裕的强人带来指责,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与外界交流,而使他们见多识广,也开始了他们对这些领导人留下的规条感到不满。 我将香港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相并提之,大抵是会诱发某些有优越感之港人大不满的,至于我之所论,确乎然乎,愚无权断之,“实践乃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信之,然仇共者亦大可谓愚实中中共之毒太深。 然,乌呼请听我解之,东南亚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于政治领域上是:这些国家依靠专制,通过手腕和领袖的个人魄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只要客观认识香港历史的人,大抵是不会怀疑我的这一说话的,的确香港之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而言实在是个自由的地方,但它由的确从来就是个专制的地方,关于这个,我已经在我的小文如:《民主不是目标》《民主不是实现自由的决定因素》里已经谈过,不提了。远如清者不说了,就香港而言,其经济的发展,确得利益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但问题却也在这里了,正因为是殖民统治,那么也就决定了,香港的政治领域是完全由英伦所专制治理,而后终于是回归祖国,但其治理结构却并未有明显之改变,只是专制治理的操纵者的空间从英伦转换为北京,仅此而已。但无论是董先生、曾先生,亦或是诸位港督、亦或是中共(即汝等声声慢的阿爷),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之争还是基于民族主义之争,他们都在努力的依靠专制,通过手腕和领袖的个人魄力,意图把自己的香港建设成现代先进国家,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香港于其它东南亚国家一样,统治者都有美好的意图:把自己的祖国和地区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都使用相同的手段:依靠专制,都私图通过手腕和领袖的个人魄力,董先生在这方面是个输家。 综上述,我们可推的是香港在政治领域上完全符合东南亚化的基本要素。 同时在经济上,香港也完全具备东南亚化的所有要素: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领域方面,他们总担心于资源下放民间,而使民间力量强大起来,从而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英国人在1970年代以前表现的最为直接的明显,而港人之阿爷,则也隐蔽的多,他们与超级商人结盟,比如中信在港的种种,实在是因为他们总习惯于用安全与稳定来作为托词,并以此来加以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而当国家掌握过多的固定资产配置权时,就迫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对于为什么这些国家更习惯于将自己演变成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拉动型经济,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却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但这却并不合适于这种东南亚体系,该种体系之所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 因此,也驱使他们更乐于将自己成长为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系而不是内需型拉动经济体系,因为这样做付出的社会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一些,他们的“政绩合法性”更容易得到保障。因为要想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对我们的制度的要求相应的就提高了,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必然的高了。但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它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这些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要在香港玩一套完全不同于其国家的治理模式的缘故。 在具体的经济层面,这些国家都乐于大力发展房地产将其作为经济支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商业家族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看看香港的富豪中房地产商的比重就知道了)、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显然这跟儒家意识还是有莫大关系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儒家的“关系学”是很有市场的,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老实说香港的表现也在其列,想想李小超人与港府玩的数码港就可见端倪了)在这里: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用,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然而富豪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太多存在的意义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经济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生产业,但东南亚富豪几乎全部出自寻租者而不是这些出口制造业(没有一家具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这一事实,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在特定市场情况下有其价值,但它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却值得我们怀疑。韩国在世界上叫的响牌子的有三星、LG、现代等等,但香港呢?老实说,或许是我听力有问题的缘故,我还真没听到过。也因此: 1、于消费者而言,除了这些企业将获得更多的行政性的行业垄断外,什么也得不到; 2、于企业而言,除了他们在行政性垄断的特权的庇荫下,形成更强烈的惰性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3、于国家而言,正如迈克尔.波特说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而一个个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他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又能够做什么贡献呢。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而令人担忧的是,事实上香港却正在体现这一问题。事实上,可以这么说:这样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或者是他们的终极操纵者如英伦和北京)在对该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地区稳定或者为大众的福利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托词?)的不幸失败而已。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看看低税率的香港的房价罢。而且如乔8226;斯塔威尔所说,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蠢到投资于那些富豪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这方面郎咸平先生做了有益的贡献,当然从他的著作和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拿人手短的事实,无他,我们只要仔细读读他的书和报告,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他的研究里,李家的长江和和黄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是干净的,但这点《李嘉诚传》的作者就比他老实的多,至少《李传》的作者,就花了一点功夫来认真的说明李在股票市场上对小股东的残害,没有办法,谁叫郎教授拿了长江商学院的教席呢? 但这种方法的采纳,却也带来了问题: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也就更丧失了创造性的改善国内或地区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环境;而这种制度架构以及管制环境的缺失,将更让他们热中于将经济出口导向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也因此他们长期执政的可能是为未来留下很多隐患,香港自港英所建立的体系,就是极度依靠政治学家们所说的“政绩合法性”的典型,即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力。董建华先生的下台,本身就是这种体系的牺牲品。 的确,40年过去了,当年香港所面临的危机早已基本消除,而其亦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代表其起飞阶段的显著增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香港回归11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新财富给这个体系带来了指责。我们固然承认这种体系来源于港英,但即定的事实我们无法改变,那么只有面对,我们也固然承认,对此做出调整以取得成功将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难题,但除了前进,香港甚至中国都别无选择,香港试图依靠国内的经验就港,这显然是缘木求鱼的买卖,从政治和经济领域上看吧,中国现在正在走香港的昨天,也就是他正在全面的‘东南亚化’,靠一个毫无创新意识,只知道亦步亦趋模仿的学生来就老师,这实在是荒唐。所以我个人决定,对于香港人来说,要救香港就必须跟自己的过去即‘东南亚化’做个有效的切割,拿出自己的创新意识出来,走自己的路才是最紧要的。到时候香港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也就成为完全可能。 香港,走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