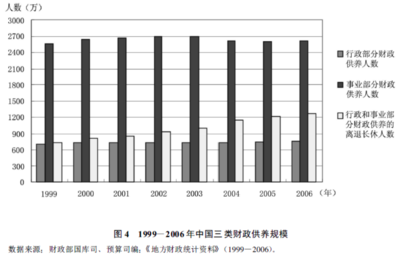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一是社会中多数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他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理由。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则他会忍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他就会舍生取义,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本体价值信念)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时提出,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是他人的外在评价。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置,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位置,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关键恰恰是其所在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经济上的)、士绅(声望上的)、族长(权力或权威上的),老年长者(年龄上的),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要求爱有差等,尊敬长者,要求三纲五常,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受会十分地负面,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有机会向上流动,做“人上人”,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会好评,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后,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中到底会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对他人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新中国平等的一员,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都加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所有人都有了获得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被他人歧视(不重视),都要求有脸有面,要求社会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这个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那些积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此,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在生产、政治、文艺的各个方面,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重新固化,个人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村庄内也出现了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个人对社会价值的积极追求就因为经济的可能性(大集体解体了,土地承包制度及由此释放出来可到城市谋取收入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村庄内部爆发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乎寻常的社会价值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背景下,往往变得荒唐不理性。直到新的结构形成,过度社会性价值竞争本身的荒唐性使这种竞争不再能获得社会性的荣誉评价时,这种社会性价值的竞争就可能嘎然而止,而留下的则可能是社会性价值的一片荒漠。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人就不能生存下来,也无法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希望更加舒适的个人生活,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是一个只要有条件,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个人自我满足,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等等。
总之,个人的价值或需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本体性价值,二是社会性价值,三是基础性或生物性价值,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关系,三种价值之间的互动及消长,即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又是生动的社会现象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三种价值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条件。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首先是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是不被反思的身体无意识,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及个人的最深沉的情感。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稳定,而使一个社会较少花功夫争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个人很少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理想。本体性价值确立了一个社会运转最基础也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模式。本体性价值构成了一个文明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通过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可以理解一个文明的核心,本体性价值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巨变的结果,也是原因。不同文明的差异,有时候正是源于本体性价值的差异。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是向外扩张的文明,不断地向外探求真理,西方文明所要处理的,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来获得人生价值。印度文明是向内扩展的文明,不断地向内探求,节制自己的欲望,通过禁欲来实现人生价值。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强调中庸,既反对不断地向外扩展,又反对一味地向求探求。中国人将人伦关系的状况,将传宗接代、延续子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
当一个社会中有着稳定而明确的本体性价值时,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关注的根本人生目标就不是问题,人们不会在人生的根本意义上发生困惑,人们要做的事情是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对于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来说,他就会表现出宗教般的宁静和纯粹,就感到满足,就可以忍受贫寒苦痛。而对于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或难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乃至醉生梦死。当本体性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他就愿意牺牲其他价值,就会“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本体性价值的实现,是一巨大的幸福,是一深沉的满足。
在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人生目标明确之后,人们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安排上,都会围绕本体性价值的目标进行。而一旦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不与本体性价值发生冲突时,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社会性价值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人群中的受尊敬,希望个人生活得体面,希望获得其他人的好评,希望有面子和尊严,希望“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等等。基础性价值则追求更舒适的经济条件,更安全的环境,更良好的娱悦生活。等等。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在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时,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不会太疯狂冒险,就会具有底线——除非有时候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本身替代了本体性价值,因为重要的在于本体性价值,且有本体性价值目标,有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本体性价值目标变得可疑或难以实现时,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目标就可能被无节制地推到过于重要的位置,以致于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因为失去依托,而变得面目全非。本体性价值的动摇或丧失,生物性欲望就无节制,人们就会醉生梦死追求刺激性体验,在乎口腹之欲,行事缺乏底线,就更加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在乎当下和眼前的东西,就渴望赤裸裸的炫耀,就更缺少生活中的耐心和难以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更容易表现出极端情绪,就更加在乎外在评价,更加敏感于他人的态度,更加期待他人哪怕是表面的尊重,等等。
虽然本体性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体性价值在决定人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上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构成所有人的生存意义的最基本条件,却是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即一个人首先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可以保障。或者说,只有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在乎他人的评价,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一个终日为解决温饱而不停止劳作的人,一个总是处在生存威胁之下的人,就很难有时间停下来想人生的意义,他至多是本能地按照习惯来繁衍子孙。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是讲基础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关系,此外,也只有仓禀实,才有功夫去关心更加超越性的东西。简单地说,一个生存不再存有问题的人,他就希望有朋友,有面子,有吹牛皮的机会,他就会思考有限生命的意义,并接受一套(极少数人可以创造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的哲学(宗教)。这就是说,一个人及一个文明社会,一定要为有限人生提供一套关于永恒意义的说法,一套构成人们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体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