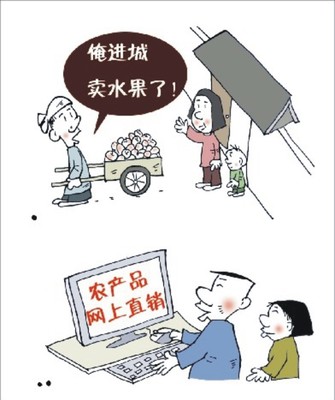(2006年3月13日刊发于《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认为,随着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社会分工和资本投入的进一步发展扩大,社会财富会逐渐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相反,马尔萨斯却悲观地认为,由于人们受制于有限资源的压力,经济增长将会受到约束。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似乎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认为两种力量会同时起作用,其最终结果会由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漫长的时期内自己来决定,是不可能提前准确预测出来的。在穆勒的设想中,第一种设想沿袭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和技术提高产出的速度时,资本家的利润会越来越高,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会越来越低;第二种设想继承了斯密的分析,认为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时,就会引起实际工资增加从而使工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第三种设想符合李嘉图的结论,认为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时,由于生产技术没有提高,在肥沃的土地被首先开垦完毕后,较为贫瘠的土地就会被开发,但它会提高食品的生产成本,利润便会下降;第四种设想认为,假设生产技术创新的速度超过了资本和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将会使粮食种植变得更为容易,并同时降低了工资和地租,最后将促使利润提高,整个经济也将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穆勒的几个设想中,社会分工问题好像被淡化,好像它无足轻重似的。事实上,人口问题,生产技术创新的问题,以及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核心点就是社会分工问题。
如果人类社会中只有种植粮食一项工作可做,那么生产技术的创新只能使一少部分人完成耕种任务而大部分人闲着没事干。闲着没事干也要每天吃饭,因此靠技术创新实现的价值仍将被耗费一空。只有让富余出来的人员去干新的工作,去创造新的价值,实现社会分工的扩展,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
要想实现新的社会分工,它不但需要生产技术,还需要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只有不断地有新产品开发创新出来,才能为资本寻找到投资的新动力,才能实现新的社会分工,才能使增加的人口去从事新的工作。如果将目光总是盯在农作物上,好像农业耕作技术创新提高水平后,从中解放(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了,若是这般,怎么会有工人呢?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怎么会提高呢?
从18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几乎总是领先于经济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指标增长的速度,但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未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超快而陷于低落,总体上看是逐渐提高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究其原因,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工扩展迅猛,不断地吸纳新增加的劳动力,在工资水平和地租水平单向性的不断上涨的同时,商品价格也随之攀升,利润大量地从中产生。可见,地租和工资是提高还是降低,它们并非能独自决定利润的提高或下降,它还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水平因素是怎样的,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这一切的一切,都最终取决于社会分工能否在科学技术的激励下得到飞速的扩展,使新增加的人口与由于科技发展在原有行业中被节省出来的人口都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从而保持或提高需求能力,使这些人成为有能力参与市场的劳动者和消费者。
最初,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机器有助于劳动分工并可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予以附和,这同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机器的广泛使用将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不会导致企业裁员,这将使整个社会都受益。
但后来,李嘉图的此书第三版出版时,增加了“论机器”一章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转而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机器将带来持续的高失业率,即我们现今所说的“技术性失业”。
然而,现实情况证明,李嘉图也过于悲观了。这是因为,就某个企业而言,使用机器后势必会形成裁员,但是,这个企业所需要的机器恰恰是需要一些人进行研制、生产制造的,企业所需要的机器种类越多,那么其他生产这些机器的企业需要的人越多。可以说,某个企业使用机器而裁员,是因为其他一些企业先扩大了就业,招聘设计者、研究员及生产该机器设备的钳工、铣工、车工、电工等等工人。这种“就业替代”尽管肯定会使一部分被机器挤下岗的工人失业,但其原因是他们在“就业替代”的转换中没能具备替代的能力,即由简单操作到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往往这部分人过去在获取的工资中没有对教育、技术等学习内容作出预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打算过学习什么新技术,也没有想过对自身的教育投资,所以当他们“技术性失业”后,几乎都缺少“就业性技术”,成了被社会“淘汰”的人。
一个聪明的劳动者,在他找到一份工作领到劳动报酬的时候,他是不会忘记应从中拿出来一部分收入用于“充电”,通过技术培训等职业教育,使自己增加技能,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素质储蓄”。对于工人来说,“货币储蓄”获得的利息微乎其微,而将“货币储蓄”变成“素质储蓄”,这等于是教育投资,它所得到的收益比起那少得可怜的利息简直有天壤之别。教育投资不但是一种“素质储蓄”,而且它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就业保险”,它的无可替代的职能就是防备万一将来失业后,可以为后来的再就业提前储备能量创造条件。
很多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实现就业的行业,虽然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但由于它自身存在着一定量的无形亏损,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种无形亏损传染给他人,故而政府不得不对它施以限制,宁肯一部分人无业可就,也不愿意让这一行业存在。例如博彩业和色情服务业。
在过去,中国视彩票行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斥之。而如今,彩票行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它的诸多好处暂先不论,仅就业一项就是一个典范。当然,它肯定也有弊端,但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将它所造成的无形亏损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应该说乃明智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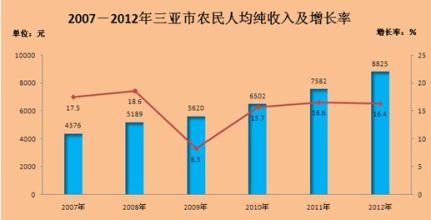
“色情服务”,从中国传统道德观之,实属败坏至极。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地承认,它的需求之市场是如此地有潜力,而愿意从事此行业的供给者也大有人在,想禁绝了是根本做不到的。它的弊端自不必说,但它实实在在毕竟还有一点点好处,在高失业率时期,这一行业可以使一部分人就业;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时期,这一行业可以使一部分富人增加额外消费从而实现“利润摊薄”,使一部分“穷人”得到额外的收入;这一行业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当然,这一行业的弊端现在仍然远远大于好处。在没有办法保留它的好处的同时消除它的弊端之前,对它下禁令确实是正确的,但有没有办法既保留它的好处又能克服它的弊端,从而让这一行业从“地下”升到“地上”,这也应是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合作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假如政府能够加大管理力度,对此行业的就业者和消费者都有明确的限制、管理措施,也许晚婚者就不会再感到性压抑;丧偶的老年者就不会因再婚问题与子女打得如同仇人;立志不做生育机器、为减少人口基数作出贡献的独身者也就有了消遣的地方;财政赤字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估计还能创收外汇,使国家获得价值剩余……这一切的好处必须在政府有能力消除掉它的大部分坏处之后才能实行。如果暂时实行不了,那就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多大的“眼”、闭多大的“眼”,取决于失业率的高低;经济繁荣时期,略微将“眼”睁大一些,经济萧条时期,略微将“眼”闭紧一些,这应该算作不是办法的办法。
科学技术所实现的发明和创造刺激了人的需求,需求的扩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工的扩展,也就必然会增加就业;只要有需求市场,我们禁也好不禁也罢,它都会勾来就业者,且不管是公开就业还是隐性就业。想把黄河之水全部拦住那是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怎样疏通好、管理好,让它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