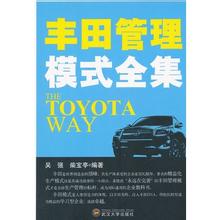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多难登临录》,三之三
《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发表后,懂经济的朋友说比我以前的解释远为清楚了,明白,好。还有不少读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试找一篮子不同的水果,每个写上价格及重量,然后拿起我的文章逐点读下去,每步以那篮子水果对照。
有四点这里要澄清或补充的。一、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彷佛昔日的金或银本位制,但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银作货币,出口流失或供应不足很麻烦。我建议的是用金或银之价作为基标(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标在市场买卖成交,但金或银的本身不是货币。乙、单用金或银,可能的市价大幅波动很麻烦。用一篮子物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自由浮动,但整篮子的总价(指数)不变,不会受到个别物价波动的影响。
二、物品可从期货或批发市场选择,二者之间批发市场(如果有足够物品的话)较为优胜。这是因为期货之价,虽然一般比较精确,有时容易出术。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丑闻。我建议的篮子,物品的质量要精确,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价的精确性不是那么重要。
三、固定了篮子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后,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如果某重要外币的汇率变动太大,人民币调整指数的应对可能引起「货币战争」之见。但如果国内的所有价格自由浮动(包括工资),这些价格的浮动足以应对汇率的大波动,不需要调整那篮子的物价指数。所以在原则上,这篮子的指数调整只宜用于调控通胀或通缩。要注意,好些时,外币汇率的大波动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汇率变动的一个功能,是为国际竞争提供一个均衡点。
四、像今天那样国际金融大乱,或历来把经济学者弄得频频出弹弓手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会把这些烦扰平静一下,其它有关金融的问题会远为容易处理。
转谈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立场早就明确。再谈,因为资料愈来愈不对头。读到的报道,产出工资成本因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个月前我估计的高出约十个百分点。违法的不说也罢。广东今年上半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区升百分之二百五十)。听说一个法庭的书记员累得哭了出来。空置的厂房激增不论,整国看,厂房的月租每平米约下降了五元——看来还要下降的。感谢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几天国家的总厂房面积,资料差一小点,不能用,但天文数字的损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进机械设备、人才流失、吵架费用,等等,以五厘年息率折现,我不知怎样说才对。
我与中国的贫困农民结了不解缘。抗战时在广西一个今天遍寻不获的村落住了一年,约八岁,没有吃过一粒饭,不穿鞋子,单衣试水,背着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在荒山野岭找到什么或可吃的就塞进她口中。村内的农民比我们一家七口还要穷,整生只在结婚与孩子满月时有机会吃饭。当时农民告诉我,抗战之前他们也是没有饭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医生说妹妹营养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该医生应该死了,妹妹还活着。
日间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难的教古文的老师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几本厚厚的书朗诵。我不知何解,但过耳不忘,今天还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数以百计。父亲当时在香港,母亲带着六个孩子,无力供养,让我背着妹妹到处觅食,过程中我对农作有深入的体会,二十多年后写论文《佃农理论》,对农业资料的处理自成一家,验证该理论的第八章,把老师艾智仁与芝大的两位庄逊吓了一跳。因为这一章,我被邀请在芝大教过一个学期农业经济。高斯后来说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实证研究。
今天老了,回顾平生,我是个没有从小认识的朋友的人。当年认识的小朋友都饿死了。今天高举以新劳动法协助穷人的众君子真的见过穷人吗?他们见过小朋友在面前饿死吗?驱之不去的回忆,是七岁在柳州中正中学附小时,一个变黄变肿的小女同学问:「我快要死吗?」年小无知,我答:「他们都说变黄变肿是要死的。」她再问:「我做错了什么呢?」答不出,我哭了出来。
当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聪明。后来自己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知道机会难逢,拼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后就成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机会中国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这样的背景,是我后来极力为中国的穷家子弟争取自力更生的机会的原因。

这些年我反复推断,考虑到神州面对的局限与各种复杂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发展要顾及的焦点,是穷人,尤其是穷家子弟。补贴不宜,因为长贫难顾,余下来就是要设法放开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了。这类推断我的准绳度早就前不见古人,而衷心说实话,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诉,主要是教育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好些是快不来的。想不到,新劳动法的引进,把那穷人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会有如此这般的效应,而是想不到北京会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国面对的资源与人口的局限下,老少不论,工作年龄的农作人口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强可接受的上限了。农地太少,某些农产品是要进口的。这里的要点,是农作人口大幅下降,不会大减农作的总产出。理由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隐蔽性失业,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农家作业制度下,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是繁忙期。几年来这农家作业的传统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大约二○○○年吧,职业农工的运作开始,不久后盛行。把牛宰了,引进小机械,耕、种、收成以每亩算价,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在农忙时间回乡帮一下。市场也因而协助农民选择各种轮植图案,让职业农工不停地工作。(中国传统的轮植知识无敌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中解释得清楚。)这些资料我跟得紧,不是政府数据,而是在实地找了好几个查询站。我因而知道农民的收入,从二○○○到二○○七,每年增长达百分之二十。继续下去,加上农产品之价再升,大约十年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齐——平均不会看齐,但农家的平均与城市的中层会。
新劳动法的祸害是容易解释的。工业成本上升,租值近于零的接单工厂纷纷倒闭,回乡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这里我要读者考虑最低工资的推论。一个工人的工业产出贡献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工厂不会雇用。怎么办?不回乡,在城市行乞,或盗窃,或望政府救济,对社会的贡献皆负值。这位无业仁兄可以转到街头卖小食。环保不论,卖小食对社会有贡献,而因为风险较高,收入可以高于最低工资。但有两个问题。其一,工厂可以作为学校看,工作勤奋,学得多,前景远比卖小食好。其二,工业可以容纳很多人,卖小食或作小生意,竞争者增加就要一起亏蚀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处境:新劳动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挥之使去。不挥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样忙顾左右,工人吵起来却不能不依法办事。工业的投资者见新劳动法的阴影还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当局对农民的补贴相当慷慨:回乡潮急升,安抚一下无可厚非,但这显然不是长远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劳动法坚持下去,不管地区政府怎样打松章,中国的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定会出现!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讨过,总是想不出有什么变通之道,能把新劳动法的不良效应化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缔的。新劳动法别无选择,取缔算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