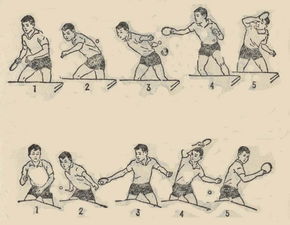前不久听商业银行的一位朋友讲课,讲到银行经营的高风险特征。他讲关键是放出去的款收不回来。他讲到银行的改革,讲到银行正在建设各种制度以降低放款风险,然而独独不提产权的问题。我听不下去,忍不住要发问:高风险的经济含义是什么?
一个行业,风险很高,当事人就有损公肥私的激励,因为事后他总可以把不利的结果归因于行业本身的高风险。行业风险很高,那我是不会尽心尽力工作的。我会高工作中消费,请漂亮的女秘书,住高档的酒店,我还要干其它损公司利益肥私人腰包的事情,因为事后总是可以开脱:我是尽了力的,是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搞坏了我们的企业绩效。
为了降低道德风险,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加强监督。这正是不少银行的改革思路:一个人说了不算,要集体说了算;一个部门说了不算,要多个部门说了算。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监督者怎么有积极性监督呢?当然,也要搞激励:放出去的款回收率高,就给当事人一定的奖励;也要搞惩罚:放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就给当事人一定的惩罚。问题是,怎样的激励和惩罚才是构成强激励和强惩罚?激励吗,强度不够,效果是不会明显的。惩罚呢,搞得不好,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减少放款或者不放款,一度发生的银行惜贷,就是证明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让私人资本去做高风险的事情。自己给自己办事总会用心的吧。
今天,我们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殊不知,创新和高风险乃是一个铜钱的两面。从国际经验看,技术创新不仅投入大,而且风险高。国际上大跨国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然而只有5%左右的项目可以成功申请专利。在这些专利项目中,又只有十之一二能投入到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正因为创新的高风险特征,所以在经验上我们看不到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的成功例子,反倒是看到了不少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的失败例子。然而很不幸,从计划经济走来的我们似乎容易沉迷于政府主导所创造的种种“奇迹”,沉迷于公有产权的“奇迹”。不是吗?别人搞出原子弹,我们很快也搞出原子弹;别人卫星上天,我们很快卫星也上天,似乎政府介入科学研究很有成效。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别人搞过了,是模仿,有径可循,信息充分了许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讲:“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来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兹,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这样看,假如我们真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话,那么就应该大力提倡并切实保障私有产权,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才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