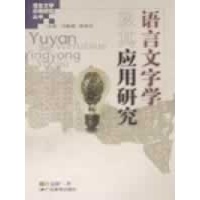「内容提要」现代性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阶级话语的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在当前中国农村,传统的规范已失,现代的规范未能有效建立,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将是今后农村政策设计的方向。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转型/乡村治理/公共品供给 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与欧洲有着极大的差异,因为中国是在欧洲列强的胁迫下,在灭国亡种的忧虑下,开始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因此,现代性在中国最集中的表现,是鸦片战争以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失败、清政府被推翻以后的五四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富国强兵,五四运动则提出民主与科学,提出启蒙及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现代性同时从两个方面进入并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即中华民族如何应对西方列强并做到救国救亡;一方面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对民众的解放。现代性的这两个方面,在五四运动中就变成了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并因为民族危机的强化,而变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单方面现代性的展开,即现代化的展开[1]. 而仅仅就现代性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来说,可以清理的方面虽多,大体却不外以下诸端:一是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二是阶级的话语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三是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四是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理念,传媒的发展;五是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 一、国家政权建设:资源抽取与组织建设 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回应西方现代化挑战的重要步骤,其核心包括建立一个现代的上层官僚系统,和为现代的目的而向下渗透的基层组织体系。杜赞奇考察华北农村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时认为,清末新政要求村政建立一套财政制度以资助兴办新学堂、新的行政组织和自卫组织,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基层社会[2].王铭铭在考察福建溪村时写道:“到20世纪上半叶,溪村的村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保甲制度取代了明清的乡里制度,并导致村落社会秩序的结构性改变。保甲制度的发明,实在宋代,在明清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方亦有实施,但其制度化和扩大化集中发生于民国期间”。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是行政力量的强化,而行政力量又包括对社会活动信息的储存与人们行为的直接监督两方面。王铭铭认为,民国期间保甲制度的强化,原因可能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为了适应吉登斯所说两个方面的要求[3]. 因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要从农村抽取用于现代化的资源,同时要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基层社会,包括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等等,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基层行政建制。吊诡的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在基层的表现,是通过“乡镇自治”来展开的。到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始倡行乡镇自治,预计到1913年在全国普遍实行。根据《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镇乡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城镇设“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为自治职,议员由选举产生。 之所以称清末新政实行乡镇自治为吊诡,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一个广泛的自治性单位,虽然在这个乡村自治中,乡绅、地主、宗族领袖或村庄地痞恶霸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学界一直对如何来描述中国传统乡村秩序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基本意见是乡村自治则无疑义。清末新政实施地方自治,与传统的民间自治的差异,不仅在于新政要求由选举产生自治机构,而且要害在于自治机构的设立,是由国家来安排的,自治机构是国家行政建制的一部分,是承担着国家任务的新的编户齐民方式,因此,清末新政的重点不是要强化传统中国乡村的自治,要民间化,而是要强化国家在农村的权力,要强化国家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要国家化,也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4].因此,毫不奇怪,清末的地方自治到了1915年,县以下设区村两级,区是县之下的行政机关,而“村”虽有“自治”之名,却渐失“自治”之实[5].而有着模范省之誉的山西村治,有学者认为,“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6].到了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再次浮出水面,就十分正常了,不同的是,30年代民国的保甲制度是“复兴”于政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的,“与清代国家权力并不直接延伸到县以下的状况有所不同,国民政府则将保甲完全纳入其行政权力系统之中……,力图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乡村社会”[4]. 关键并不在于乡村自治的外表,而在于其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措施,是否收到了实效。杜赞奇考察20世纪前期华北的地方政权建设,认为新政的推行,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而没有能够用到现代化目标上去。 杜赞奇认为,在民国时期,华北的村政建设十分的不成功,原因是“村政权的正规化,其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脱节,以及来自政权内卷化的压力,使村政权落入那些贪求名利的‘政客’手中”[2].直到1941年推行大乡制,取消自然村的管理职能,并以此来划定其控制的最基层单位,使地方精英与原所在社区相分离,才为新型的乡村领导创造了一个新的获取和施展权威的环境。“从各个方面来看,推行乡镇制(即大乡制——引者注)表明国家政权使下层机构正规化,从而克服村民偷税漏税以及拒交摊款等积弊,这是与村庄利益相关的传统领袖与地方恶棍无法完成的任务”[2]. 在华南的福建,以王铭铭调查的福建溪村为例,溪村所在地区,“1934年5月开始实行的保甲制度,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及10保以上)为镇(或)区”。“保甲法的实行,打破了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随着保甲法的实行,村政制度走向了规范化。明清时期如果说有村政存在,那也是由非正式的权威人物(如耆老和族贤)来行使权力。相比之下,到了民国保甲法出台之后,出现了保长、甲长的任命”。“保甲法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明清时期以乡约为象征的‘伦常式’村政向社会经济控制型的村政的转型”。王铭铭特别指出:“民国期间保甲法的创设并没有致使家族制度走向消亡,而仅仅意味着家族作为一种村政制度被新的政区和权力结构所取代。家族的组织、区域网络、经济功能和仪式相当大部分得以保存。家族的认同感、通婚制度、轮耕轮祭制度基本上因袭旧法。再者,保甲制度并没有触动乡族势力的社会根基,而为家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3]. 以回应西方挑战为目标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真正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以民国政权留下来的制度为基础,一方面通过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将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组织起来,一方面通过建立以村支部为基础的党组织,使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正是“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为中国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同时,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结构,较为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以宗族为基础的自然村结构[7].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乡镇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 二、阶级话语的构建与后果 梁漱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传统社会,只有职业分殊,没有阶级对立,原因有二: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卢辉临则将革命前的村庄称作“没有地主的村庄”,他通过检索相关社区研究资料发现,“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这提醒我们,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8]. 梁漱溟和卢辉临讲的,只是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无地主的一面,不过,中国农村地域庞大,不同地区的情况相差何止万里。据吴文晖的统计,建国前中国水耕地区土地占有状况中,30%的地主和7%的富农,分别占有了30%和27%的土地,而23%的中农和67%的贫雇农(含其他),仅占有23%和20%的土地[9].其中1940年四川全省有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其中土地最肥沃的成都县,竟有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1.1%的地主手中。浙江平湖县,大地主户数仅占总户数的5‰强,而占有田数为耕地总面积的30%强[10]. 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估计的偏差,原因之一是研究的地区差异,水稻种植地区地力高,有投资价值,而旱作农业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太低。二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的破败与凋敝,尤其是社会不安定,使有钱人不愿也不敢住在乡下,并逐步脱离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毛泽东曾描绘过在大革命形势下地主逃亡城市的情景,他说:“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民投降”[11]. 卢辉临又说,“在革命前的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分化主要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生产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经济分化“通过广泛的社会生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和仪式进一步成就村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和差异”。卢辉临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认为革命前的农村中各种保障穷人生存权利的习俗,促进农民接受社会分化的结果的“命运观”,可以看作是“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社会分化由经济生活中的上升和下沉开始,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出来,在“文化网络”中获得其合法性。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能够不依靠强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维持秩序的部分原因[8].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