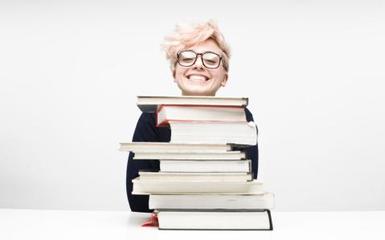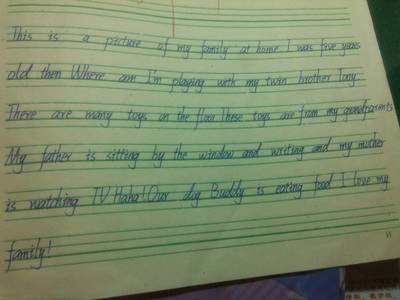二十世纪是一个真正商业化的世纪,最显著的特征是大量的大型公司制商业组织的崛起与发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GE、GM、AT&T等大型公司为代表的公司纷纷建立起了成熟的组织机构,这是战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1],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新社会基本结构。很快,公司组织结构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就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再次得到了显现,日本依靠学习借鉴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涌现出了诸如三菱、丰田这样的大型公司,以此为基础日本经济才实现了腾飞。
纵观美日公司结构的演化过程和最终形式,呈现出来诸多的一致性:矩形组织结构、适度分权体系等等。实际上,这些特征表明了韦伯所论述的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不断延伸,在复杂变化的环境面前,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实现扩张和发展,需要一种高度效率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也必然会出现组织结构的相似性。
与经典韦伯式的分析不同的是,格兰诺威特在80年代对经济现象进行社会学解析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更新的分析思路[2]: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这一结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将“嵌入性”作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即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形式一致性的对象由于嵌入的环境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实质性差异。因此,即使美日公司在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这些公司的组织结构也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兴起和成熟,人们再次发现了美日公司在面对新经济形态所展现出来的不同表现,美国公司在新经济中表现抢眼,涌现出了微软、苹果、GOOGLE等一大批经济新贵,而日本的SONY、松下等知名公司则很难再继续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了。
为什么美日公司的表现会出现这些差异?它们的组织结构具有怎样的个性?本文试图从组织对其所处文化的路径依赖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组织结构是对组织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3]
在系统论的分析进路下,组织与环境呈现出了一种嵌入关系:即组织必然是存在于环境之中,成为周围环境的组成部分;环境为组织提供存在、发展、变异甚至是消亡的所有外部因素。这种嵌入关系使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具有依赖性。实际上,组织行为与结构可以被看作是组织是对环境刺激的综合反映。
最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是链式结构和矩阵式结构。采取链式结构的组织通常面对的环境比较单一,环境的刺激可以以一种单向的方式在组织各个部分之间传递。而矩阵式结构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刺激的时候,可以做到横向传递和纵向传递的结合,因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可以应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刺激。在现实中,更多的组织也选择了矩阵搭建内部的结构模式。
容易被忽视但却极其重要的是:组织面对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环境的秩序形成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结果。自生自发秩序作为一种“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产物,组织及组织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的时候将处于一种必然的无知状态。处于必然无知状态的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很多制度性的风险。在这种状况下,组织只有不断的调整自身的结构,增强组织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适应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实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综上所述,环境是组织结构形态的决定性因素,理解这个基本立论,就可以对美日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公司组织结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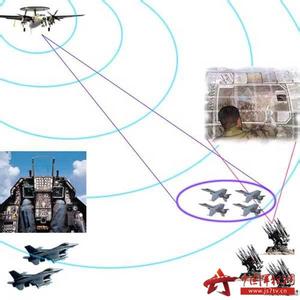
美国公司:人的组织[4]
正如德鲁克所论述的那样,美国民主人权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公司组织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作为组织的公司,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理性工具。在这种具有社会唯名论色彩的传统中,人具有相比较与组织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即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目的而存在,组织不应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将不道德的目标强加到个人身上。
美国公司形成这样的组织结构特色不是偶然的,由自由民主精神所塑造的宪政体制和对欧洲公司的经济反抗的双重作用塑造了这样的商业文明。韦伯论述了新教徒将商业成功视作为个人证明上帝之存在和能力的首要方式,经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自我是上帝的选民。这样的公司鼓励员工充满发挥作为个体所具有的活力和创造性,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上帝和世俗世界面前证明自我的存在。容忍创新所带来的失败和损失,鼓励曾经失败的人重整旗鼓,激发了整个体制的活力,也就产生了微软、苹果、GOOGLE等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虽然,美国的大公司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科层气质及其消极影响,但是相比较于任何其它民族国家的公司而言,美国公司的员工往往具有更大的自由意志的空间。同时,受惠于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社群联合会的原因,个人也具有了更多的能够和公司进行议价的能力,因为即使最坏的结果发生——雇员丧失了工作,他也依然可以相对容易的获得其它的可替代性机会。这就对公司产生了一种外在的客观性制约,使得公司将员工的利益放在一个核心的地位上,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宪法和劳动法的要求,也才更加符合美国文明的文化气质。
日本公司:组织的人
与美国公司的社会唯名论色彩相对的是,日本文化中的公司组织则更加具有唯实论的特点,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具有高于任何个人的地位,公司雇员的最终目的是为公司服务,以工具理性的效率原则为最高指导,促进公司发展。这是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中的社群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联的认知方式的表现结果。
虽然,日本公司非常重视员工在公司内部的表现和成绩,管理方式也具有很浓重的人情管理的特色,甚至在90年代以前普遍采用终身序列制的人事制度方式。但是,公司作为一种实体始终具有高于任何个人的地位,对于公司的决定个人几乎没有议价的能力,只能被动服从。所以,日本公司组织结构的最核心的特征是组织的人,这也是日本公司组织结构和美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本质差异。
依靠这种组织人的结构,日本大公司取得了令人瞩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雇员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人均工资在6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3000美圆以上。但是,经济收入的提高并没有改善雇员的组织阶层位置,雇员只是公司庞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件。
日本公司拥有这样的组织结构特征也不是偶然的,虽然没有新教伦理作为文化支撑,但是武士道却是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其道德核心是忠诚。在封建时期是对领主的忠诚,进入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后,这样的忠诚感便被转化到公司身上,公司中的人便成为了公司的人,雇员对公司形成了强烈的文化经济性依赖关系,公司对雇员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公司的意志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效率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至。
可见,正如盛田昭夫所比喻的那样,美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砖匠模式,在一个组织框架的基础上全面发掘人的潜力,提升其发展的空间;而日本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石匠模式,将不同个性的员工打造成为适合公司使用的合格雇员。盛田昭夫用形象的比喻所说明的正是美日公司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在组织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人的组织”和“组织的人”的差异。
自我管理型组织:人道主义与效率原则的融通
其实,作为嵌入到不同文化情境中的组织结构,并没有优劣区别,任何组织结构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有限性。历史上,美国的砖匠模式和日本的石匠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种理想型分析,“人的组织”和“组织的人”分别标指出了组织内部生成构架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效率原则。人道主义将“人是目的”作为了一种首要遵从的行为规范,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的重要性;而效率原则强调出为了保持组织调动、运用资源的能力,而需要对个人的权利、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指导原则都具有合理性,也曾经主导了一个时代的成功。但是,正如二十世纪90年代所呈现出的新动向一样,在新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组织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上述理性类型区分的诸多特征,在当今的市场竞争中,类型融合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传统的公司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应该更加人性化,这样才符合经济社会深层次所发生的变化。将人作为组织的最终目的,公司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使股东、管理层、雇员、消费者受益,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人道主义的文化理念变成强有力的公司文化。同时,公司具有超越个体的属性,在个体交往与群体交往的互动中提高效率,不断发展。这样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管理型的组织,它具有以下两大核心特征:
1、扁平化
弗里德曼出色的证明了世界正在日趋变得扁平化,传统的围墙逐一被拆除,未来的世界各部分的界限日趋模糊,以个人为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格调。在这样的时代中,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公司自身的扁平化将决定世界格局扁平化的走向。
扁平化意味着公司在不同文化类型中拥有更加灵活的定位和自我调试的主动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重视由各地差异性所带来的机会和风险。以个人为核心的全球化3.0时代不是对以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化2.0时代的简单取代,正如以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化2.0时代并没有简单取代以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1.0时代一样。管理界将实现一场革命,最终的成功者必须找到个人的生活意义与公司的作业效率的有效结合点。
2、社区化
自我管理型组织不可能是单独的巨无霸式的大型机构,在一个对灵活性具有高度要求的市场环境中,最优规模的定义意味着必须保持足够小的规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型公司的末日,实际上大规模联合几扩张所带来利益仍然十分巨大,但是对大型公司的管理却难以在造作层面上拥有一致性。公司必须按照地区、职能、消费者满足等几个纬度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划分,最后的模式将变得具有社区化的色彩,既保持规模优势又可以灵活运作。
公司母体更多的负责战略制定、文化整合等宏观层面的工作,同时通过分权的方式将具体施行的部分放权[5]给各个社区子体来完成。社区型公司因为具有完善的功能系统所以具有最好的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性知识和资源,实现全球性的生产和服务。这是跨国公司实行“本土化”战略的深化,以文化一致性为主轴,重新规划全球业务的布局。
拥有了扁平化和社区化的组织结构,自我管理型的组织将登上中心舞台,这也必然意味着一场管理科学的革命的到来。为了更好的迎接新经济社会的挑战,任何公司在面对这一变革的时候都需要更加突出的强调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重视地域性文化知识多带来的多样性风格,打破陈旧的束缚,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新组织架构,这就是时代环境提出的新命题!
参考文献:
《组织社会学》,于显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未来的组织》,[美]德鲁克基金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未来的社区》,[美]德鲁克基金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公司的概念》,德鲁克,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华夏出版社, 2005年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丰田生产方式》,大野耐一,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6年
《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新渡户稻造, 商务印书馆 ,1993年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格兰诺威特
《组织化社会的未来》, 籍磊
《未来企业组织结构展望》,中国经理人在线http://www.51cxo.com/Article/strategy/design/200505/2015.html
[1] 这正视促使德鲁克从社会政治学研究转向公司管理研究的重要原因,企业在20世纪已经成为了社会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力量。
[2]格兰诺威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3] 籍磊在《组织化社会的未来》一文中对于不同的“组织”的概念及其对应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只有采用一种“关系性视角”才能对组织的情况做出最深入全面的理解。
[4] 德鲁克再次为我们理解美国的公司组织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深入的视角“公司的本质是社会性的组织,也就是说是人的组织”,《公司的概念》,第22页。
[5] 最早最好运用分权思想的大公司是GM,正是凭借这一有效的管理方式,GM超越了福特公司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巨头。参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的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和德鲁克的著作《公司的概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