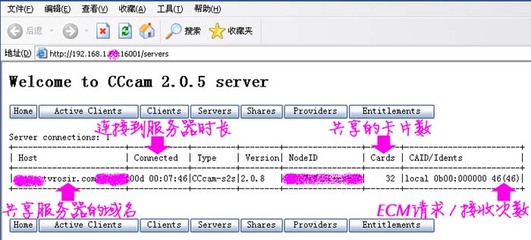以下文章出自作者所著《经济学:范式革命》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ISBN:978-7-302-17259-8。如需引用,敬请注明出处。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振聋发聩式的诘问——“(西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或者更像是一种鉴定结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至少蕴涵着以下四重含义:
1、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西方经济学继承和延续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在先的“本质”,并据此作出“人性贪”的“经济人”先验人性设定[1](通俗地说,人的自私自利乃至无穷贪欲都是天生的,是在娘胎里或更早的时候便落下的毛病)及其周围环护拱卫的基本假设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和数理推导,从而建立起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其间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设定为已知的”[2],这种逻辑推演和数理推导过程不外乎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经济人”行为假设出发来得到具体的、细化的“经济人”行为模式,并回过头来再度说明“经济人”先验假设的天然正确性,因而其所有的研究都不过是在自我臆想、自我意淫的封闭空间内同义反复、循环论证、颠来倒去、无病呻吟。
西方经济学家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先验人性”的真实存在,包括近年来所谓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的不懈努力[3],却沮丧地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4],甚至还常常得到相反的结论,无奈之下也只能继续假定其为真,正如神学中神之存在无法于“现实世界”中直接获得证明,而只能告诫和教谕其信徒在心中无需理由、不假思索地信仰膜拜。由于这种人性设定是先验的、似真的,无法将鲜活缤纷的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们纷繁芜杂、变化万千的社会心理全面涵盖并能与之真正契合,因而当假定和现实之间本来妇孺皆知的那些个明显差异之冰山一角被西方经济学者间歇性地当作“重大发现”提出之时,在此唯心哲学观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自然就会发生全局性的危机,如同沙滩之楼,地基尚不稳,大厦复何存,即使外观再富丽堂皇、精巧绝伦也无济于事。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既然“本质先于存在”,那么必然存在一个天赋的“自然秩序”[5],一种由上帝强加给人类世界并由先验人性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东西[6]。这一“自然秩序”就是新老自由主义者百般推崇和宣扬的放任自利、放任竞争,通过自由逐利、相互对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个人利益”或“个人效用”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一般均衡的自由市场机制。西方经济学家的神圣使命就是发现并证明这一“天赋秩序”,以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服从、服务、服侍于这一“市场神话”[7]。
为此,西方经济学家从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出发,对牛顿经典力学范式或借鉴、或模仿[8],把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原子式”质点,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的个体行为,把普遍的经济联系割裂为彼此无关的自变量,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机械力学范式”,即“由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三个基本假设所构成的研究视角”[9],其核心框架可以简单地(虽然不大严格地)表述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而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是对行为主体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的抽象描述。在这个假想的范式中,牛顿绝对时空观统治了一切:时间空间是一维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是教条的、凝固的[10],系统演化是机械的、可逆的,最终达到或者趋向于某种“呆滞的均衡”[11],从而忽视甚至根本否定了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经济规律自身各种可能的复杂表现形式,因而这个自诩为“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12]与“以为他们利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最后解释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3]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同样的沾沾自喜,又同样的幼稚可爱。至于为什么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析,仅仅只是因为数据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充分、数学形式还不够精巧和复杂,正如拉普拉斯妖假设所宣称的那样:如果已知宇宙中每一粒子的位置及速度,就能预测整个宇宙的未来状态;只要伟大到足能将所有数据加以分析,就能将宇宙间所有运动凝聚成一个单一公式[14],这便是牛顿机械力学范式留给我们的浪漫梦想。西方经济学全面承袭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念,裹上写满演绎逻辑和数学等式的华丽外衣就想挤进科学的神圣殿堂,却被缪斯女神无情地挡在寒风凛冽的大门之外[15]。因为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乃至其后的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的革命已经彻底打破了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神话。
3、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无论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获取知识的结果,都毫不怀疑自己在人类知识宝库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自信,乃是因为:所有知识都根植于已知事实,已知事实均已得到说明,没有已知事实与之相矛盾,并且继续从已知到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与这一通行做法相颠倒的是,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整个儿植根于一堆先验假设,试图从先验假设推导出各种已知事实,这一奇怪的做法,显然不是为了探究未知领域的奥秘,而是不断证明给定假设的神圣。两种方法看似殊途同归,其实大相径庭:前者在新的事实发现以前,已经是可靠的,可以称之为科学,并能放心地运用于实践;后者在其自身或其相关结论未被全部证实以前,仍然是可疑的,还不能称之为科学,亦不能安心地应用于实践,否则就是拿着科学的名誉去冒险。相对严谨的态度是:暂且将其作为非科学,而不是姑且将其作为科学。
不仅于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西方经济学第一假设——“经济人”假设被公认为是一个非现实的理想模型,由此演出的全部故事也就浮在现实之上、飘于幻境之中,“请不要和我谈论现实,我们是经济学家”[16]。“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思维不过是从主观到主观,从臆想到臆想,从假设到假设,从演绎到演绎,充斥于西方经济学教材、著作和论文中的,通篇都是“假定”、“如果”、“倘若”以及“模型”、“图示”、“推导”和在此基础上“想当然耳”的研究结论,却自我陶醉于形式上的优雅,对着假想的镜子顾影自怜、喃喃自语,讲述着一个个远离现实的美丽传说,这种用数理语言写就的童话,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和令人昏昏欲睡的乏味集于一身,引诱着众多博学之士“尽入毂中”[17]。西方经济学家比摸象盲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事先精密计算、精巧设计、精心打造了一个曲线优美的笼子,然后告诉一头幼象,钻到里面长成“U”形或倒“U”形模样才是理想的,才是完美的,如果多出些巨耳长鼻粗腿细尾,则是大象有问题而非西方经济学[18]。“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也必然导致从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与从现实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规律或统计结果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譬如厂商“L”形长期成本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库茨涅兹之谜”等,因而有调侃戏谑道:“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19]。“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还必然导致因基本假设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直接获得验证而使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基本假设的理解产生分歧,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结帮成派、党同伐异。剑桥之争表明:不同的西方经济学者站在各自立场上都能认为自己是武林正宗,一打经济学家会冒出十三个观点,缺乏公认的确定性和典范性,“学派林立、自相抵触,明显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20],这种情形是与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完全不相称的。
4、西方经济学的检验方式离科学标准还相距甚远
一个理论,如果不是源于实践,则更要归于实践,到实践中去检验。“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21],也是科学的诚实品格,科学的东西是不怕任何检验的,并愿主动接受检验,无论一次还是多次,无论证实还是证伪,并且还会在各种可能环境下的不同检验中获得升华的养分,不经过检验,就无从判断其科学性。即便是科学假说,原则上也应当是可检验的[22],否则“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23]。
卡尔·波普尔提出:“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24],在这种检验中,九百九十九次的证实并不能证明其理论为真,只要第一千次是否证,那么理论便被证伪了;而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命题恰恰相反,一千次的否证或不一致都是正常的,只要第一千零一次偶尔被经验证实,也就获得了证实,所以被斥之为“可笑的奇迹证明”[25]。
显然,这种宗法神学的“奇迹证实论”是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但却能让西方经济学家安心地躲在太虚幻境中自娱自乐,对现实世界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长此以往,每天都在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还是让他们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一套更为精致、圆滑的自我辩护技巧被发展起来,一旦理论受到现实反驳,便通过辅助假设调整,不断消解种种反常[26],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却能保护其理论内核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可是巧言善辩终究敌不过铁的现实,当更多现实之锥戳向其理论核心时,他们便武断地宣布:可检验的理论并非真正的经济学,不可验证并非什么坏事,而是真理性的标志[27]。
至于理论性相对较弱的计量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就指责它是从最复杂深奥的数学中“戏弄出”一个又一个的“相关关系”,而以这些相关关系来代替因果解释对经济现象作出明确预见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而只是一种“相关关系的暴政”[28]。一个极端滑稽的例子是:“用中国的消费基金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前苏联的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得到拟合优度为0.9的方程:中国消费基金=-14720.13+68.29×前苏联人口数。”[29]
正因为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知识体系、检验方式这四个方面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所以加林·库普斯曼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30]。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不是发育不全的问题,而是错义基因引起的多发性先天畸形,以一条未经检验之假说的软脚,一条无法检验之结论的瘸腿,在迷失的方向上蹒跚跋涉[31],并不知道自己是通往科学的巅峰还是通往非科学的沼泽。
[1] 许多经济学者都存在着一个误解,认为“经济人”不是假设,而是现实人性的提炼和抽象。即便如此,这种抽象也是失败的,因为概念抽象是对事物同质的提取,反过来又统摄范畴内一切对象,并在这一层面全然成立,绝无反证,更不是或然的、概率的,否则就须重新抽象或将反证划入非类,“人类行为确有百分之八十的情况符合此模型,问题是隐匿的另外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经济学派只能提出难以服人的解释。”非“经济人”于现实中的广泛存在,说明“经济人”并非“一种不容置疑的经验事实”,只能是一种假设。参见弗兰西斯·福山.信任——对社会财富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0.
[2]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3.
[3] 参见Smith, V.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Apr.):111-137. Kahneman, D. &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s [J]. Econometrics, 1979, 47(2):263-291. Laibson, D. A Cue-Theory of Consume Current Draft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5):19-27. Mullainthan, S. & R. Thaler. Behavioral Economics [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7948, 2000. Camerer, C., Loewenstein, G. & D. Prelec.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1):9-65.
4] 郭新华,郁惠英.对“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诘难[J].经济问题探索,2001,(9):36-37.
[5] 高续增.“自然秩序”:通向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编辑《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手记[N].中华读书报,1998-07-01.这种“自然秩序”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并被索罗斯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参见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M].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16.
[6] 杨立雄,王雨田.物理学的进化与非线性经济学的崛起[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3(10):21-25.
[7] 韩德强.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7.
[8] 陈璋,陈国栋,刘霞辉.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9-61.
[9] 李跃.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困境[N].中国经济时报,2005-03-01.
[10] 这种因果关系可表述为:“如果P2的存在或变化总发生在P1之后,那么现象P1就是现象P2的一个原因。”参见Tinbergen, J. The Functioning of Economic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1, 5(3):33–38.
[11] 刘安国,杨开忠.克鲁格曼的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评析[J].地理科学,2001,21(4):315-322.
[12]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财经科学,2002,(增刊):1-8.
[13] 威廉·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277.
[14] 转引自刘怀德.论经济学的复杂性[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4):47-51.
[15] 傅琳.混沌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动态,1994,(1):75-80.
[16] 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N].贾根良译.经济学消息报,2003-06-20.
[17] 王定保.唐摭言:卷1[A].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78.
[18] “这一神学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不被放弃,反而是现实要受到不与神学理论相一致的指责。”参见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前言.
[19] 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M].香港:新世界出版社,2002:68.
[20] 李建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管窥[J].桂海论丛,2002,18(1):72-74.
[21] 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37.
[22] 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4.
[23]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41.
[24] 卡尔·R·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2.
[25] 狄仁昆.西方经济学理论检验问题的哲学分析[J].江海学刊,1997,(6):112-116.
[26] 胡乐明.证伪主义与经济学的发展[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5):3-7.
[27] Knight, F.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A]. In: William, L. & J. Alexander (eds.).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Selected Essay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51-178.
[28] 转引自梁正.对西方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考察[J].经济评论,2002,(2):58-62.
[29]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11.

[30] 加林·C·库普曼斯.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M].蔡江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
[31]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32-13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