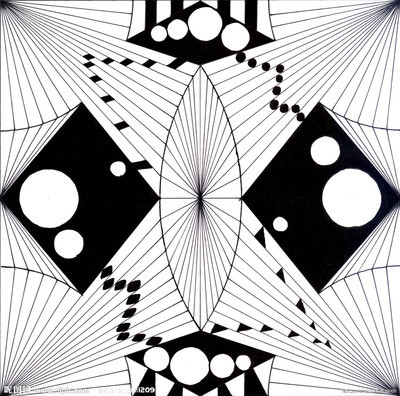――纪念湖南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光辉历史,讲到底,是一段“让中国与世界同步”的思想解放史。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要遵循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把我们的思想从一个更深的历史层次和理念障碍中解放出来。具体到湖南,作为“两个凡是”领袖的发迹地和“计划经济”的主战场,到底应如何联系自身特点和省情,找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临床诊断样本以准确破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量。鄙意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用“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去破除那深藏在我们灵魂深处、多年来被主流媒体无限放大了的“湘军”崇拜和“湖湘文化”情怀。
其一,要破除对“湘军”的历史崇拜。这里所说的“历史崇拜”,包括对“湘军”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崇拜。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南京大屠杀”: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皇军”干的,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湖南“湘军”干的。19世纪的那次中外历史上最为残烈的“南京大屠杀”是“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的基本标识,也是其统帅曾国藩被无边“黑雨”收天、民间咒之曰“曾剃头”的口碑由来。在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序列中,人的生命和尊严总是居于最顶端,其它一切都要退居其次。因此,日本人一直在或羞于面对或拒绝承认或愤怒谴责“南京大屠杀”;李鸿章当年访德也自愧于“铁血首相”俾斯麦“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的指责;而我们为什么至今还在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目大肆称道“湘军”,不以为鉴反以为傲呢?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要把“湘军”打造成湖南的“名片”,要以它自傲,因为“湘军”身上粘贴着湖南的“湘”,它是我们湖南的传统和历史。但我总是在想: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魏源、蔡锷、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睁眼看世界、出生于湖南的民主斗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面前,在浩荡的世界民主潮流面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这些人为傲?我们要继承的传统到底应该是哪种传统?我们要尊重的历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
为了给“湘军”诛杀起义农民和无辜百姓寻找理由,有人故伎重操地论证说太平天国是“邪教”。诚然,太平天国运动重复了中国式的“起义”或“革命”大多只是封建专制的“改朝换代”,而不是现代民主的“制度创新”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也绝不应成为“湘军”在攻下“天京”后大面积、长时间杀人放火的借口。难道因为太平军被定义为“邪教”,就有理由承认“湘军”的滥杀无辜了吗?两军相交,死伤难免,但胜者“不虐待俘虏”和残杀百姓乃古今之公理。在当今的法治社会里,更是或废除了死刑或死刑判决是有极其严格程序的。即使是“治乱世须用重典”,也是绝不能搞“宜肯错杀,不可轻放”的,即使是处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国际上不是也有针对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指控吗?转过来想,为什么称基地组织等为恐怖组织、文明毒瘤?不就是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炸、滥杀生灵!由此,我们应更深刻地反思自“湘军”以来与“长毛”类似的诸如“共匪”、“蒋匪”、“反革命”、“右派”、“右倾”之类“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罪名的现代非理性和它的历史悲痛感。说句实在话,当我每次“红色旅游”到彭德怀的故居并翻阅他的“万言书”时,我总是欲哭无泪啊!
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审视“湘军”的这段暴力史,我们要研究:用纳税人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军队到底是抵御外侵的,还是镇压人民的?现代国家应不应该宽容、善待自己的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无立锥之地之农民、有拳拳之心之学生――的诉求?应如何彻底避免同胞与同胞间的、政府与民众间的相互仇杀?我们要懂得: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是世界上最安分守己的,百姓造反是专制极端压迫、民生极度凋敝之果,“暴政”出“暴民”,“暴民”灭“暴政”,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杀戮老暴君,农民当政后又像朱元璋、洪秀全们那样或迟或早变成新暴君,如此往返循环,形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更替,即被从湖南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人民大救星”毛泽东曾经所称的“历史周期律”。我们一定要乘市场经济改革之风进行民主制度的全面创新,走出这种“周期律”,创造一种使老百姓不揭干起义,或者尽量使动乱的振幅缩小、频率减少的体制、机制,不然,我们一百多年、乃至几千年来“怨怨相报”的“窝里斗”何时休?何时才能实现我们稳定建立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看看当今之世界,为什么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来社会和谐、没有大的流血冲突,其资源和财富能最大限度地用于改善民生上?我看,就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人类优秀的制度文明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宝贵品德,进行了“选票里面出政权”的制度变革,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渠道进行权力制衡和权力更替,使老百姓平时的不满和怨气没有堆积、积累,而是自由地在法制的框架内宣泄了。
其二,要破除对“湘军”的精神崇拜。为了避开对“湘军”的历史谴责,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此‘湘军’,非彼‘湘军’”的善良论调。其意思是说,他们现在推崇的不是历史上的“湘军”,而只是借“无湘不成军”的近代美誉虚拟一个“湘军”名称用来推介湖南某个行业集体或产业集团“能打硬仗”的精神和理念,意在将其发扬光大、并应用于湖南的经济建设中。
历史上如果没有“湘军”,“湘军”只是一个人为构造的纯文学词汇,这种寓意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很有创意。问题是,历史上确有那么一个血迹斑斑的“湘军”;“无湘不成军”,为什么不可以组成一个也主要由湘人参与的“北伐军”、“工农红军”,而独独只成一个“湘军”?至于“能打硬仗”一说,我们不回顾曾国藩当年怎样妙笔生花地把“湘军”由“屡战屡败”变为“屡败屡战”上报朝廷邀功的历史往事;不追究当年“湘军”是如何以抢劫掳掠百姓来鼓舞湘勇士气而能“屡败屡战”的;也不去讨论其滥杀百姓的大方向错了,其“能打硬仗”的精神越强、危害人民的程度就越大的学术问题。我们只是说:发展市场经济、富民强省能效法军事理念、军事体制吗?别的不说,当年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就是军事理念、军事体制搞经济的惨败记录。
1860年一系列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们因“镇压得了百姓却奈何不得洋人”而开展的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客观地讲,较之于极端顽固派开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封闭中国的开放之门。但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去接受学术界早有定论的研究共识:差不多同期开始的“明治维新”使得我们民族原来的“学生”――日本早成了发达国家了,而“湘军”们的“洋务运动”却让我们至今还在“发展中”?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之“用”以“自强”;维护中国的传统体制、伦理道德之“体”以“立国”。非常明白的道理:有“体”才能有“用”,没有“体”,焉能有“用”?这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思路嘛!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作为传统体制的忠实信徒,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触动专制制度,采取的都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国家垄断方式,焉能成功?更为严重的是,洋务运动确立的“中体西用”理论经传统卫道士们的操作放大而固化成了近百年来学习西方的特定模式,“师夷智”变成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制夷”,把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引入歧途,直到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全球化潮流的强烈冲击下,这种局面才有所突破和改变。正是这种“中体西用”论的顽强干扰,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至今仍然还要呼喊着“振兴”,我们有着优越资源的湖南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资收入更是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差了几大截。所以,洋务运动给予我们的只是“教训”,我们再也不能在传统的历史荣耀中陶醉了,我们需要一次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解放过程。没有制度、思维方式、行为观念的“体”的深刻变革,仅靠以技、智等“用”的引进来开发自然资源和发挥劳工低成本优势,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万万不可能的,我们热切期待的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滥用公权力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全面扫除不仅不可能,还可能由于面对社会财富的激增而变得越来越猖獗的。
从经济理论上探讨,“湘军”的理念和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官本位”的理念和精神。将这种理念和精神引入经济生活,对内便重上轻下、重官轻民,抑制草根经济、漠视百姓创业,厚待官办的“大而强”,歧视民营的“小而多”,热心“拉郎配”,习惯搞“整顿”,致使“寻租”泛滥、效率低下,社会财富贫乏和就业空间狭窄,缺少促进社会公正的物质基础。就会继续几千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没有自由、明晰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整个经济、科技必发展不起来,为市场经济护航的民主政治推进更是步履艰难。而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将“湘军”的精神引入经济生活,对外便会将商场由合作共赢的“情场”变为兵不厌诈的“战场”,或者是虽说“开门引资”,但总在“关门打狗”,排斥包括人才在内的外来资源,甚至丢掉“和气生财”这一中华民族最简单的商业古训,将商业行为理解为政治行为,将企业纠纷上升为国家摩擦,产生不了市场经济“双赢”“多赢”的基本经济生态。
糟糕的是,正是基于这种“湘军”理念和精神,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有意无意地“湘军”化,比如“电视湘军”、“出版湘军”,还有“机械湘军”、“奥运湘军”,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什么“理论湘军”、“地板湘军”、“美术湘军”、“饮料湘军”、“家电湘军”之类,最近又冒出了个不伦不类的“申遗湘军”。湖南三十年来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成就,是现代政治文明吸收的成就,不是“湘军崇拜”的成就。试问: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有“湖南电视”这些年这么迅速的发展?能有至今还有人在质疑的“超级女声”?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还能有“快乐大本营”?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有“湖南机械”这么大的成就?“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们,当年在涟源火车站旁边创办小焊条厂时,我曾经应邀给他们的员工讲授了一个礼拜的市场营销课,我是深知他们的创业辛苦的。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有“湖南奥运健儿”?当年不是有人把“奥运”看作是帝国主义操纵的工具吗?“奥运火炬”如今在中国所以能突变成“奥运圣火”,难道不是体制改革、思想解放之功?
实证地分析,湖南经济之所以落后于人,之所以发展缓慢,很大程度就是屈于“湘军”理念和精神的干扰。比如,有“湖南的温州”之称的邵东,其百姓创业热情高,境外投资、经商就已到了美国、意大利、越南、老挝等30多个国家,但为什么不愿返乡创业?是的,我们湖南有“三一重工”,也有“远大空调”等等,但请问:除了它们,我们还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温州一粒小小的纽扣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大市场,而湖南不能?为什么我们治理经济环境总是把板子打在民营企业身上?湖南外贸为什么规模小、结构差,抵不上发达省区的一个县?本人当年提出“外贸企业制度的彻底再造”命题时,为什么总是有好心人提醒“小心挨整”?为什么改革初期外省市大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而我们则极力进行传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目前,我们的“长株潭”已经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再也不能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要努力强化在以抑制公款消费为起点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农民的国民待遇、城乡“二元结构”、土地及金融市场化、垄断行业改革等方面的“改革试验”,而如果继续沿用“湘军”理念和精神,不改善百姓创业环境、激发群众创业热情,民营经济只是在狭缝中生存,能真正建设好“两型社会”吗?
其三,要破除对“湘军”的文化崇拜。对“湘军”历史及“湘军”精神崇拜的产生和坚持,不是凭空而起,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的,那就是我们常不离口的所谓“弘扬湖湘文化”。因此,要有效破除“湘军”崇拜,就必须对“弘扬湖湘文化”进行分析。
湖湘文化,虽然学术界对其精髓、精华的概括,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还是有着基本的时空范围和文化特质共识的。从时空范围上说,它是在“两宋”以后的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过程中所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被乾隆皇帝赐之为“道南正脉”的程朱理学浸润了的湖湘境内的地域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它是我们的先辈为追求福祉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适应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济模式,没有经历过城市文明、工业文化洗礼的农耕文化。由此可以得出,我们对待“湖湘文化”所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搞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我们岂能不“与时俱进”、“与世俱进”,而去固守传统的、地域的农耕文化?
文化,广义地说是“人化”,或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奥格朋所定义的,文化是“一切人为的东西”。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当然有许多人民群众创造的优秀的东西,其中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积淀的瑰宝很多,仅以商业地名为例,有关的诸如洪江古商城、“宝庆码头”以及遍布湖湘各地的“铺”名——“铺”是人们商贾生活的纪录――就不少。这些文化遗产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传承、去修复、去发扬,以重建曾在计划经济时代“以革命的名义”破坏殆尽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但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自汉董仲舒以后的制度文化,是统治者的“官”文化,是教统治者如何去统治,教被统治者如何去接受统治的文化,它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专制文化,它的问题很多,也很大。程朱理学被奉为湖湘文化的正统,理学家用佛学道家中的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儒家学说,其问题更多,也更大。比如,把“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天条放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面前考量,请问:没有“人欲”,哪来“天理”?没有“人欲”的“天理”,那是什么样的“天理”?市场经济是在产权明晰基点上的自由经济,它承认人们对利益追求的本性,用制度去激发“人欲”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人欲”这一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前提,怎么能搞好市场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再比如,即使是非正统的“湖湘文化”思想家王夫之,虽有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认为“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重农轻商、鄙视商品经济的。我们能以这样背景的文化思想理念,引导我们新时代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吗?
从地理位置看,湖南曾被称为南蛮之疆,流放之地。湖南地形是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倘,域内山丘起伏、河溪纵横,缺乏大海洋、大草原、大平原一泻千里的交通便利和一望无际的视野环境;三湘大地气温多变且湿度大,时而受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侵袭,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控制,冬季“千里冰封”,夏季“烈日炎炎”,洞庭湖水面蒸发的热气郁积不能散发,闷热难熬;洪灾、旱灾、冰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交替肆虐;湖南远离政治中心,天高皇帝远,是屈原、贾谊、范仲淹等“进亦忧,退亦忧”的心忧天下之士的流放地,也是江西、四川等各地“老表”的移民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正是这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性格中就具有所谓“吃得咸、耐得烦、霸得蛮”的“蛮”品德、“辣”精神,同时也就多了些自负自狂、固步自封、故土难离、安贫乐道的因子。这些东西如不加以改造和扬弃,是难得适应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要求的。
当人们倘佯在岳麓书院前,欣然地琢磨那赫赫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八个大字时,我不知道这个“惟”是指“中国之‘惟’”,还是“世界之‘惟’”?是“人文之‘惟’”,还是“科技之‘惟”?是“历史之‘惟’”,还是“未来之‘惟’”?如果是指上面所有“之‘惟’”的后者,我想:倘若不是天遥地远使得牛顿、爱因斯坦们当年不能旅游到此,真不知他们面对这个“惟”会作何感想?我们意“取欧美之长”的三湘莘莘学子们面对这个仿佛就是世界文化和科技中心的“惟”该作何抉择?面对这个“惟”,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愧对了那前人给我们在麓山脚下竖立起来的以作谦恭笃实警示的“自卑亭”?即使是“惟楚有才”,但我们又想过没有:历史上还有“楚才晋用”之说,现在则是“孔雀东南飞”、“麻雀东南飞”,人才流失、资金流失,以致本土经济空心化,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之骄傲的湖南精英为什么总是“出生在湖南,成功在省外,扬名于天下”?我们还常说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但光凭一个“敢”字就能“天下先”了吗?我们现代的湖南经济又哪一项真正是“天下先”了?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但我们的屏幕上总是被“杀人如麻”的“硬”皇帝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蛮”英雄所充斥,这能很好的使人们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吗?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要讲“科学”,讲“科技”,我们“莽”、“硬”的传统品质能适应吗?即使是面对自然灾害,也是必须讲“科学”的。仅以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的生命救援为例,没有高科技的生命探测器,没有现代的机器设备和科学的救援方法,光一个“蛮”“硬”的精神又能起多大的作用?最近听一智者讲演,其中有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总结语:“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便无道理”,此话值得我们三思。我们以往的所谓“弘扬‘湖湘文化”,根据我的观察,它不是“弘扬‘现代文明’”,而是在弘扬那个“蛮”和“硬”,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悖的。刻薄一点讲,它是我们的经济落后感、心理自负感发挥到了极端以后所迸发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文化标号。
总之,“文化”一旦形成,就是“以文化人”。正是这种农耕性质的湖湘文化传统深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就“化”为了湖南现代化的思想阻力。如果我们对“湖湘文化”没有一个“去粗存精”的科学过程,不能把传统价值观转换成现代价值观,那就容易让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否定、“忽悠”现代文明,扭曲、异化市场经济,乃至残存、复活计划经济。我们一定要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破除“湘军”崇拜,弘扬现代文明,以推进我们富民强省的全面建设和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湖南是中国的湖南,“湘军”和“湖湘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影响深远。
[1] 根据2008年4月在湖南省社科院《思想解放与富民强省》专家座谈会和在中南大学召开的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综合整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