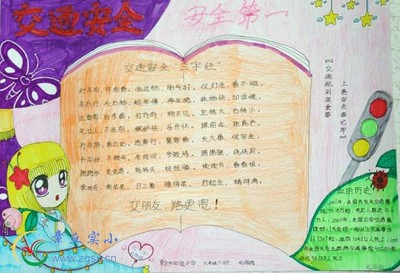摘要: 本文站在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类活动:以科技和劳动换取闲暇,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生活状态,使其变得更安全、更便利、更舒适。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发生科技与生产的背离,生产与生活的背离,或者科学技术直接与生活目的的背离,导致各种形式的科技负效应,经济增长负效应。这是值得我们用理性来反思的。此外,文章认为,我们只有敬畏自然、关爱自然、关爱他人、关爱自我,才能“愉快地接受爱,又自然地奉献爱”,获得幸福。
关键词 :幸福;科技;理性;关爱
(一) 人类活动的终极意义哲学家休谟曾说:一切人类活动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我想,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穷其精力、孜孜以求的所有努力。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人类主要从事的几种活动:劳动(财富创造)—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休闲、娱乐。当然除了这四种主要活动以外,战争也是常有的,但战争归根到底还是源于这四种活动的不当运行。比如,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遵守经济规律,就可能爆发经济危机,饥荒、战乱也就在所难免;科学不发达、宗教迷信往往产生宗教战争;而技术滥用也往往是毁灭性战争的源泉。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终日劳作却往往衣食不足,居无定所。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活动可以描述为:劳作吞噬了闲暇,科学与技术尚处于蒙昧状态。

在农业经济中,人们的闲暇时间是充足的,但劳动人民也往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们不禁要问:农民为什么不象原始人一样终日劳动?或许他们就能够挖到野菜,摘到野果子或者狩到猎物?我想说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是农业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著名哲学家罗素讲过:“人们不快乐,一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一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当然,个人心理也大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农民仅拥有少量土地的使用权,也只有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他们才获得了劳动的权利,继而生活必需品。劳动权对他们来说是稀缺的。原始人则不同。他们的劳动技能(生产力)也许不及农业社会,但那时资源(如土地、水、森林)是相对丰富的(因为是公共财产),这就弥补了他们在技术上的缺陷。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人们便获得了更多劳动的机会。因此,有人怀念原始社会为“逝去的黄金时代”。对于农民来说,充足的闲暇时间并不意味着娱乐,也不意味着文化艺术的繁荣和生活的闲适,而是意味着对饥饿和贫穷的无能为力。如果有劳动的可能,他们都不会“缩在墙角等待取暖”。此外,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农耕经验的积累,专门的农业科学研究几乎不存在。虽然相对于原始人,他们积累了更多的耕作技术,但仍摆脱不了靠天吃饭,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劳动得不到解放。
是什么力量催生了近代巨大的生产力?早在17世纪,培根指出:知识就是力量。科技革命使得最先掌握它的西方社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切都被伟大的邓小平尽收眼底,他毫不怀疑地断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无疑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在近二十年内所取得成果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卓著。科学育种试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粮食增产的奇迹;水利技术、化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靠天吃饭”成为历史;机械化解放了更多劳动,人们不再困于一亩三分地,可以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自主做出选择。工业制造,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便利品,极大促进了生活的丰富性、方便性、安全性。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加快了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的速度,使得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大缩短。科技解放了劳动,创造了闲暇。闲暇不再充斥着“无所事事”,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文化艺术得到了飞速提高。反过来,聪明的人们便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小缩影。
从无知的原始社会走来,我们发现人类周而复始、紧锣密鼓所进行的活动,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为改善生活状态(更安全、更便利、更舒适)而进行的面向自然界的劳动,这就是社会性生产,它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制度)密切相关。二是为解除内心疑惑、求得平衡感而进行的面向真理的探索,这就是科学。科学有时是自发的、探索的冲动,多数情况下又是出于人类活动的第一个目的。正如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说 “ 科学有两个来源的分支, 一是人们对他们周围的完美宇宙的解释而形成的信念。一是不断发明的工具,它们使人类的生活更安全、更容易” [1]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活动的主要目的可以归结到:改善生活状态,使生活变得更安全、更便利、更舒适。
(二)关于科技、生产、生活的理性思考通过上面的回顾,我们发现,科学推动了技术,技术促进了生产,生产改善了生活。一切似乎就这样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中。但为什么近百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动乱、饥饿、失业、恐慌?为什么在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当今社会,人们仍然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幸福感?为什么交通便利、信息发达,人们仍然摆脱不了 孤独、冷漠、烦恼、疲惫?正如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到:“如果机器生产的利益,能对那些需要最切的人多少有所裨益的话,那当然应该阻止贫穷的延续;但如果夫人本身就在烦恼,那么让每个人富有又有何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科技和生产活动,往往偏离了“改善生活”这一终极价值,而走向了相反的片面增长。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科技的负效应,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
1.科学技术本身无罪
胡塞尔曾指出: 在19世纪后半叶 , 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 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 [2] . 一种绝对化的技术理性既没有了古典理性中的整体和谐, 也失去了近代启蒙理性中的人性关爱, 科学技术似乎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文明“本身则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 [3] 。
然而如果返回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去, 我们则会发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看来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科学技术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单纯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以工具为目的”的行为并使人类蒙受巨大灾害,或者不但没有增进反而削弱了人们的幸福指数,那也不是科技本身的意愿。而是人的行为的不当所致,包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现实世界的漠视;包括对自身需求的模糊理解,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无知。 正如爱因斯坦说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使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2.技术负效应与“理性 误区”
网络犯罪、不良信息传播、“数字鸿沟”等信息化发展的负面效应 ,克隆技术 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以及大量使用化肥、沙虫剂和塑料薄膜造成的土壤生产力的下降和污染的恶化。这些问题所折射出的认识和行为误区主要有:
(1)功利的眼光
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都是殚精竭力地抓取、掌握科技这个决定性力量,以企加速自身发展的进程。然而,只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大多数国家尚处于发展中或贫困状态,整个人类世界因此而贫富悬殊,裂痕昭然,矛盾重重。这样,功利性运用科学技术便以更大的力度而无所不在,已经成为危险难测的全人类的怪圈。
(2)膨胀的自私
出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人们凭着越来越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毫无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断刺激着人类的这种需求的日益膨胀,并为实现这种需求提供了工具。于是人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利用愈演愈烈。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危机日益严重,这已经成为科技时代的全球性问题。
(3)工具的严重依赖及主体地位的丧失
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滥用、误用、恶用)导致了人自身的危机,即技术的异化导致人性的异化,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精神的萎顿。历史上,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自身对自然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科技本身存在某种非人性化的因素,加上对科技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技术的异化。在异化状态下,技术不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倒成为统治自己的、压迫自己的异已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从属于它,人成了它的附属物。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蔓延的网络综合症,它剥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用于娱乐和发展的时间),也严重影响着上网者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心理的健康 [3 ]
3.经济增长负效应与“理性误区”
(1)经济增长等于经济发展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经济水平提高会带来两方面的积极结果:一是社会产品的增加,二是闲暇时间的增加(不包括非自愿失业)的增加。
曾几何时,谋求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较大增长,成为我国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官员热烈追求的主要经济目标,也成为上级考核下级工作业绩的主要标准, 叫做“以GDP和人均GDP 论英雄”。一时间,GDP 成为我国各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根重要的、乃至主要的“指挥棒”,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出现了敬畏和膜拜。GDP逐渐被异化、注水和弄虚作假。项目是建了,GDP也上去了,可是,产出增加了没有?劳动力节省了没有?闲暇增加了没有?这才是关键的。我们看到了耕地变工厂、别墅,看到了森林被砍伐,资源被开采,马路被修建,广场被树起。我们欢呼于GDP的高速增长,却没有看到粮食减产、土地劣化,自然感冒!
(2)物质丰富等于生活幸福
《新华字典》注释, 幸福就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也就是一种自我满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8226;莱恩认为:贫穷不能使人幸福, 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 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就小多了。研究表明,一些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在走低。如日本, 在全球82个国家(地区)幸福指排名中仅列42位, 排在越南(29),菲律宾(31)之后。而经济并不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墨西哥人民生活乐观, 生活又有保障, 福指高居全球榜首 [4 ] 。然而对物质(以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泛化”需求为主)的追逐却似乎从来没有减弱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的内容相当丰富,仅仅依赖于物质的增长是远远不及的。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的“乐感文化”认为幸福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求知”、“游戏”和“仁爱”。通俗一点就是说“科学探索”、“闲暇娱乐”和“关爱”。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就会自觉劳动,把劳动也看作幸福的事。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综上所述,如果科技不是服务于生产,而是出于别的目的或走向了别的什么领域,那么动乱、死亡、犯罪、堕落将不可避免;如果生产不是服务于生活,而是用于类似“GDP ” “利润率”等象征性的指标,那么,饥饿、恐慌、过剩、停滞将不可避免。因此,我要讲的是:科技为生产服务,不能偏离;生产为生活服务,不能倒置。
(三)回归自然,倡导关爱为了获得幸福,除了理性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信仰——对自然的崇敬与关爱,对人自身的尊重与关爱。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为追求经济增长而运用高科技破会自然;不会成为科技和物质的奴隶。
如果 “ 做什么、怎样做 ” 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社会的变迁处于不断更替的状态。 “ 为什么做 ” 却是人的内心世界,是做的源动力,是我们传承、发扬或者是摈弃的主要内容。
(1)我们为什么要回归自然
冯友兰先生说:唯有“负底方法”我们才能体认自然奥秘的无穷 , 从而能体认形上学意义上的自然的存在。登上太空不应使我们觉得人类即将征服整个宇宙, 相反这应使我们更加清楚地发现宇宙的浩瀚无垠和奥妙无穷,知识进步不应给我们以这样的错觉, 人类知识正日益接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相反, 这应使我们更明确地体认到, 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之未知领域只是沧海一粟!当我们能体认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时,就能反观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无论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在技术操作方面,人类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的无穷力量。人类对地球自然过程干预得越强烈,遭遇的惩罚就可能越严厉 [5] 。正因为如此,人类必须敬畏自然!
休谟有句很经典的话:人类最高的技艺和勤奋所得到的产物,无论在其外表的美好或内在的价值上,都不能与自然产物的最高和谐相媲美,这对于人类的虚荣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拿“人工湖、人工假山”和“黄山、漓江”比一比,拿“人工美女”和”自然美女“比一比,拿电子邮件和书信比一比,就不难发现休谟所揭示的道理。人们为什么要旅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什么成为千古佳话?不过是出于人对自然的依恋,就像对待久违的亲人的思念。自然会拥抱你,给你你想要的。高深流水的诗意;阳春三月的温暖;微风拂面的清爽,仅仅因为那是自然的。
(2)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关爱
如康德的感悟:“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便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两种东西便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除了自然,我们的还有一个求助的港湾:道德律。也就是我要说的关爱。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先天就具有在心理上与他人保持关系平衡的倾向,人类本性上是自爱(自保) 和爱人(向善) 二者相互依存 [5] 。
没有了爱,世界将会变成坟墓。我们深信不疑。没有了对自然的爱,我们便失去了获得幸福的最基本源泉。“仅从技艺的规则中,是毫无希望达到只有从自然的神灵启示才能产生的神圣的和谐的”。只希望从索取中获得满足,无异于将正在盛开的鲜花摘到手上,殊不知,漫山遍野的美丽才是长久的。对于他人,也是一样。如果仅仅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某种目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竞争与争夺,剩下的将是冷漠,荒芜。想一想,我们如何获得友情、爱情,如何增进亲情吧。没有朋友、恋人、亲人会是怎样的?失去了对自然的爱和来自自然的馈赠又会是怎样的?对自己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个不知道自己需求的人会成为外界的努力,成为科技的牺牲品。只有在关爱自己基础之上,人们才能有选择的从事对自己有益的活动。
最后,用罗素的话作为结束语:完美之爱给彼此以生命的活力;在爱中,每个人都愉快地接受爱,又自然而然地奉献爱;由于这种相互幸福的存在,每个人便会觉得世界其乐无穷。
参考文献:
[1] 徐建立.科技成果运用中的悖论刍议.周口师专学报.1998,15(4).
[2] Dampier , W. C. . A S hort History of Science. London , 194 5.
[3] 廖小琴.简论当前人的精神生活的不平衡. 《思想教育研究》,2005(9).
[4] 李昌森.幸福指数与以人为本.江南论坛,2005(8).。
[5] 陈利人.构建和谐自我. 湖南社会科学.2006 (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