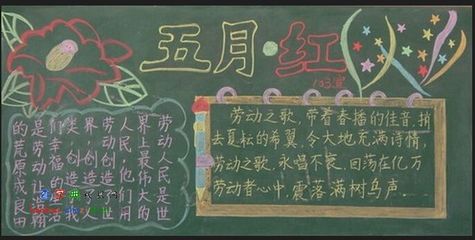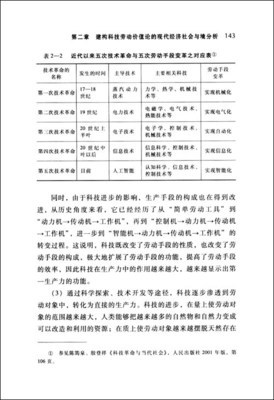价值尺度问题,是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之前笔者曾对之进行过在某些特定方面有所侧重的简要讨论,今天在此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价值量的判断[1],马克思说:
“……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52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是什么呢?马克思之前曾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中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2] 52
由上述引文,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这种正常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是仅就某一种具体的商品而言的,而非是就全部商品而言。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问:生产不同的商品的正常的社会条件能够一致吗?它们的劳动强度与熟练程度能够平均吗?也就是说,比如生产粮食的正常生产条件与生产布匹的正常生产条件能够一致吗?也许生产粮食的半机械化是其正常的生产条件,而生产布匹则是以全面机械化为其正常的生产条件。二者的生产有着完全不同的工艺要求从而劳动过程。它们之间的生产条件能够统一地“正常”起来吗?从而他们的劳动强度与熟练程度能够“平均”起来吗?[3]
马克思还说:
“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 [2]52
显然,马克思在此是认为:生产不同的商品的每一单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相等的价值。否则比例问题从何谈起?
既然如此,那么由前所述,当不同的生产者各自的正常生产条件不同,从而在此条件下的平均熟练程度与强度不同时,显然,他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也一定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质。可是这种不同质的劳动时间,又如何具有同样的价值意义呢?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就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问题吗?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不错,马克思是说过复杂劳动不过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没人会反驳这一点。但问题是,马克思未能指出,如何把复杂的劳动转化成简单的劳动。换言之,没能够指出如何确定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生产一定量的布所消耗的一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相当于生产一定量的粮食所消耗的几个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
在《资本论》中关于的商品这一章,当马克思指出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的原因“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的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2] 59时,恰恰是因为前面首先假设二者之间的价值的差别,然后才指出其差别的原因。换言之,在这里马克思不能由不同劳动的差别来指出他们的价值的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此只能以一种假设的结果推出确定的原因,而不能首先根据原因而指出结果。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从原因找寻结果,则必然要问:怎样断定“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呢?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此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考察的,因为如果要是这样,马克思就必须把被他踩在脚下的东西拾起并掸去尘土,这将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常常挥舞着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的瓦刀,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却是构筑了一个唯心主义价值论的危楼。
如果说商品生产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非生产者自身的需求。那么,所谓的熟练程度,就至少包括着满足社会需求的状况,而不是生产商品本身的自然状况。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就表现为供求状况的变化。
我们首先假设,生产100斤粮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1米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同质且量相等的。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二者的价值必是相等的。现在,如果布的生产者采用了一种生产上的便利方法,使得生产1米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其价值必然是减少一半的。显而易见,对于生产者而言,如果没有经济利益上的好处,新的方法是不会被采用的。那么当此时,在同样的时间内,其数量尽管增加一倍而其价值不变时[4],生产者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动力呢?毫无疑问,尽管这种进步的取得,我们可以假设并未显而易见地增加生产者的一分一毫的直接成本。但是,这种未增加任何直接成本的进步的生产方法,难道不是一种劳动的结果吗?从而生产率的提高难道不是以一定的这种进步性的劳动为前提的吗?显而易见,这种方法的使用,显然在生产者主观上,无不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客观上,也不会不使生产者获得利益。但问题是,如何确定新的生产条件下的一定的总商品价值呢?或者说,如何确定这种新的劳动的价值呢?
具体而言,如果生产者仍然生产原先数量的商品,那么显然,其现在的成本总是要低于过去的成本,对于生产者才有利可图。从而该商品——单位商品——此时的价值就此而言应是低于以往的,——比如低一半。但是正如前述,这种新方法本身难道就是毫无价值的吗?如果说它有,那么它应当如何计算或应当是多少呢?从而此时的商品价值应当是多少呢?如果商品数量增加一倍,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这种新方法的价值的问题。显然,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时间的观点,我们应当在按照这种方法生产的结果进入市场交换之前就应当知道其价值,可是,显而易见地,我们在这现实中却是绝无这种可能的。[5]
当我们把生产的一切外在表象剥去,仅看生产者在其中的作用时,那么,不同的生产者在相同的时间内的劳动价值[6],应当如何并且由谁来判断呢?两个具有同等学历的人,毫无障碍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工具,在相同的时间内,以相同的资本,研究出不同的两种商品,是否就意味着二者的劳动价值必然相同呢?——请注意,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这里是不允许以结果来推断原因的,而只能以原因而得出结果[7]。在这里,他们处于同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对本学科有着同样的熟练程度,并且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如果我们再精细一点说,他们所研究的产品除一点区别之外其它方面是相同的,这个区别就是产品的颜色,比如一个是兰色的,一个是金色的。[8]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而有理由认为,二者的劳动价值是一致的呢?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实践上的经验会支持这种价值一致的判断。这里有一个实证的例子:之前据预测,二零零七年夏天的时装流行色为金色。而当某一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运动品生产商,在某城市推出两款运动鞋,一款以兰色为主色调,一款以金色主色调时,恰恰就是这个金色的并不受大多数顾客的青睐。其中的原因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我们现只须知道这个金色就此而言不大为顾客喜欢就足够了。
在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对这两种产品颜色的不同市场把握归诸劳动熟练程度的范畴中去。因此,我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其决策者对于特定市场的社会需要的把握的熟练程度之不同,才导致了相应的商品生产在实践上的最终价值的不同。人们也许会觉得,我的这个观点似乎在证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正确性。然而,我们将要考虑的是:对这种熟练程度的最终评价是由谁来进行的呢?人们是否可以先验地指出,兰色运动鞋的生产就一定是代表着一种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先验而论情况恐怕恰恰相反。那么,这种实践上的判断,由谁来进行呢?生产者当然生活于其中,但没有人会愚蠢地认为这种判断是源于从而决定于生产者的。显然,这种判断是来自于生产者所面对的市场。生产者的经验或做出的任何判断,不过是基于对市场的把握罢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价值的评价或判断,是在于市场交换或市场运动的过程中,而不在于之某一孤立的方面。
换个角度说,若两个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是全新的,并且他们在各自领域内是唯一的生产者,从而他们自己的生产条件,就是这个领域的正常的生产条件;自己的熟练程度和强度,就是这个领域的正常的熟练程度和强度。那么,他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劳动或商品的价值呢?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劳动时间,同质化为对方的劳动时间呢?就算是他们知道对方的自然劳动时间,显然也是不行的。因此,就算是以一种相对的价值形式来表示其各自商品的价值,也无法在事先做到。来到市场上,二者除了面前的对方商品的一般状况之外,其他有关生产的情况一无所知,进一步地说,就对方的商品而言,一方除了这个商品的一般状况、自己的需要,当然还包括自己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他恐怕基本一无所知。[9]马克思曾说:
“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 [2] 51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 [2] 75
商品的价值不能孤立地脱离其它商品而获得表现,一件商品如果我们不用其它商品来表示,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呢?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可以回答说:它的价值是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是如上述,A商品的一定劳动时间与B商品的一定劳动时间具有不同的内涵,从而二者的分别一小时劳动时间,毫无可比性。也就是说,当我说一种商品中包含有二小时劳动时间时,没有人会理解这二小时的意义,从而这种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至少没有现实存在的意义。[10]
马克思说过,不能用麻布来表示麻布本身的价值[1]62。那么,又怎么能够用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来说明这种劳动的价值呢?这种劳动无非就是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时间过程而已![11]显然,必须用另外一种商品的量来表示其价值。[12]也就是说,一种商品没有脱离任何一种其它商品的绝对的价值!即:
“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 [2] 62
于是:
“即使商品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2]69
便是自相矛盾的了,[13]——至少是不严密的。因为显而易见,当我们不知道两种不同的劳动的价值分别是多少时,又如何以一种劳动来表现另一个劳动呢?
至此,我们的思想脉络是:第一,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于价值的决定的意义,以及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种种经验,可知道,不同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具不同的内涵的;第二,因此,应当找到一个把不同质的或不同内涵的劳动时间统一起来的尺度,但马克思没有找到这一尺度,因为马克思本身就忽略了这种不同质的问题。唯一可以令我们“联想”到的,是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论述。显而易见,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在社会过程中进行的。但是,这种关系最终只停留于马克思的观念中,而不是在其价值理论的阐述进而总体把握中。[14]毫无疑问,劳动的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简单性与复杂性,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是一种相对的存在。那么,制作一件上衣的劳动的简单与复杂,离开了另一种生产劳动的比较,便无法判断。从而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是一种相对存在,而非绝对存在,这一点如前述马克思是指出过的;第三,这样,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就是错误的了。因为这个价值尺度的定义没有涉及另一方即社会需要的存在。换言之,马克思在此把生产者的条件作为孤立的、唯一的价值决定因素。而我们由上述分析已经看到,由这个条件而存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是先验的,而不是实践的。如果我们愿意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的决定,是社会的商品生产的广泛联系与竞争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先验的臆断。从而这意味着,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市场的各种关系而讨论价值问题。
[1] 这个商品的概念是通俗地以我们日常的观念为准则,还是严格地以其真正实现交换时的一瞬间的观念为准则,在此并不重要。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我们知道,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为着社会需要的目的的,而不是为着自我满足的目的的。从而就上述马克思的意义中,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视为一种劳动的熟练程度。

[4] 或者说利润率仍然不变,——哪怕是暂时的。
[5] 如果马克思同意价值决定于市场而不是之前,那么,整个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就面临破产。马克思至少在客观上,混淆了价值基础与价值尺度的概念。如果以基础或内涵的意义来说明价值决定于劳动,那么一切分歧便止于什么是价值和什么是劳动这两个问题上面;如果以尺度的意义来说明价值决定于劳动或劳动时间,则一切分歧便止于谁被衡量从而谁有资格成为尺度这两个问题上面。当马克思不是以劳动本身之外的客观的存在为其价值尺度,而是以这个劳动从而劳动的存在条件为其自身价值的尺度时,我们才有理由认为:至少,马克思在价值论上,是唯心主义的;而当马克思断然否定供求关系与价值判断的关系时,无疑就等于割断了各个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商品价值内容的同质化设置了障碍,因此我们才有理由进一步地说:至少,马克思在价值论上,也是形而上学的。
[6] 在读者尚未充分理解我的所有观点之前 ,尽可以把这里我们说的生产者理解为一个小生产者或一个雇佣工人。
[7] 注意,毫无疑问,马克思在之前我们引用的“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 这段话中,却是含有着恰恰相反的意味的。
[8] 我们可以把这种颜色设想为这一产品的某一特殊部位的点缀。
[9] 至少因为有此一点,竞争才是必要的。一般而言,正如上述,我们事实上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产品的最一般知识外,其他一概无知,从而我们根本不可能根据经验去判断某一种商品的要价是否是合理的,而竞争,则恰恰可以使这种价格达到使生产者能够把其商品送到市场的最低水平(在此,我们不得不又想到了斯密的三种收入论与萨伊的三要素论)。此时的价格,就是商品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另外,显而易见,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多非完全竞争的因素存在,但这种因素并不表明由此而决定的价格不是意味着相应的价值,其中的原因或者说
[10] 本来,这个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且不管它是如何判断的,在人们可以把其均质起来以后,来指出其为价值的基础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马克思恰恰相反,他认为首先是可以确定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然后由此才是可以确定交换的比例。
[11] 显然,如前述,市场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劳动的质的情况是怎样。
[12] 显然,这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动态的。
[13] 只有把商品的相对价值理解成两商品之间关系,而把商品价值理解成货币价值才是不矛盾的。因为显然,商品价值在形式上就是相对价值(交换价值),我们不能一边说其变,一边又说其不变。但马克思在此是绝无此意的。并且我们要注意,在此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商品的价值不变,其实只能是相对于某一种特定商品而言,而不是相对于一切商品而言。说到价值从而交换价值,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价值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不同的劳动的关系时,我们将注意到,价值其实除了表现为这种为他人生产商品的从而不同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即: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在促进了人们进行的一种最大效用选择,或促使人们寻求效用最大化。从而这种概念的内在本质,是在反映着不同劳动的安排。从而价值的概念在实践上,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必要的。但在观念上,这个孤立的个人可能仅仅存在一种自我安排的即效用的观念,而不是作为事实上的人们之间的交换的从而社会安排的价值的概念。这样,如果我们从关乎有机体的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价值的概念,则它存在于相应的任何一个自然的与社会方面;而如果我们仅仅是从劳动的社会安排角度来考虑,则它仅仅存在与人与人的交换关系中。对此,读者可参见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M],第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第19—20、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4] 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讨论,在篇幅浩繁的《资本论》的三卷册中,仅仅有二到三处有所提及,而如何取得二者之间的统一,则根本没有一个逻辑上的构建,仅仅是观念地认为它们是统一的,从而马克思轻描淡写地说:“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2] 58。由此可见,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价值评价的问题被马克思所回避了。我之所以说是回避而不是说忽略,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将会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构建过程中遇到一个不易逾越的障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