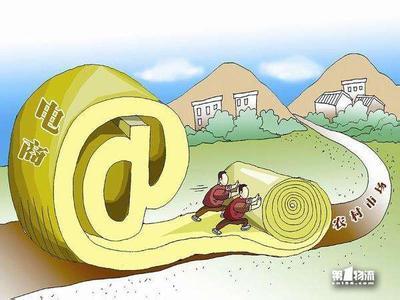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珠三角闹起不可思议的“民工荒”,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民工在中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廉价资源,于是在那个时候,媒体、政府包括很多学术机构都对“民工荒”投入了很多注意力。就在那个时候,我所在的学校院系适时的做了一个关于“民工荒”的课题研究,后来此研究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研究成果编著成书——《民工短缺与制度短缺》。当时我有幸成为这个课题小组的一员,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深入到珠三角的腹地——深圳、东莞、中山、佛山以及惠州做实地调研,深入到各城市的工业区,所到之处均是一派勃勃生机的生产景象,到处都是招工信息。此情此景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是三年之后的今天,在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广州火车站却提前的迎来了民工返乡潮。“民工荒”问题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迅速瓦解,很多民工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毫无准备,束手无策。想起三年前的一次讨论,我的导师指出,其实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民工“荒”,在“民工荒”现象的背后凸显的是制度的短缺。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很多社会学家试图通过各种理论去解释,包括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制度理论、城乡二元体制理论等等,试图从环境角度、制度角度、个人选择角度去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真相。当时的这个现象引发了很多争论,甚至连最基本的——是否真正的有民工“荒”问题也引发了争议。
三年过去了,很多争论还萦绕在耳边,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民工荒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要保护民工的权益,改善其工作环境生存环境,为民工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保障民工。而经济危机的到来让这些解决方案显得有点不切实际,尽管是高屋建瓴却有点像空中楼阁。因为危机让民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凸显到最重要的位置,生存都不保遑论权益的保障?
假设“民工荒”现象曾经真实的存在过,而就算在那个“民工荒”的年代里,在我所接触过的民工个案中,我真实的感受到在那样一种“供不应求”的环境下,民工依然没有多少议价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潮流大势中随波逐流的散兵游勇,甚至散兵游勇也算不上;我真实的感受到很多理论在他们的处境里是苍白与无力的;我真实的感受到我正在做的课题对于他们来说毫无作用,而那时的我也只能通过手中的笔去记录那一切,并奢望自己的记录能够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关注。可是今天我连这点奢望也没有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长三角与珠三角用工环境的对比,因为小组中有些教授认为民工荒的现象在珠三角比长三角严重很多,而且珠三角的民工很多流到长三角去了,于是试图用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去解释。认为长三角在民工待遇、用工环境等方面都优于珠三角,于是作为理性人的民工必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去寻找更优的待遇和环境。于是在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对珠三角的民工造成一种“挤出”效应。因此,“民工荒”出现在珠三角是一种必然,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在对待民工方面从制度建立到环境改善甚至到最基本的人文关怀都是缺失的,长期以来对民工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浪费和滥用,作为理性人的民工,被迫作出“用脚投票”的选择。当时,我对这样的结论深信不疑,我为卑微的民工还能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感到安慰,无论这样的选择是多么的无奈,至少能够在客观上促成我们的社会、政府以及民众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去改善他们的环境,去保护他们的权益。
三年后的今天,当全球经济危机悄然而至的时候,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置身于全球体系的每一个行业,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应声而倒。连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都变成了乞丐,而我们的民工更是赤裸裸的暴露在这样的一种惨景之中,一丝不挂。他们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首当其冲。于是,工厂倒闭了,他们失业了。无需解除合同,无需任何赔偿,甚至有些人连最后的工资也因为老板跑路而泡汤了。是的,因为他们是廉价的,因为他们是低贱的,于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成为牺牲品。是的,他们在此时再一次的“用脚投票”,他们“选择”了回家。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一种理性人假设是多么的愚蠢和扯淡。如果说无奈也是一种选择,那这种理性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这种假设所基于的前提有两个:一是作为人要具备理性算计的能力,二是作为人必须要有两种及以上的选择。可是民工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至少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两种及以上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从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卑微的活着。于是,是否具备理性算计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显然这样的一种理性人假设在民工群体中是不成立的。
其实我早已不是愤青,我也不是要借此表达我对民工兄弟的同情,我知道这样没有用。只是看到火车站提前返乡的民工,心里默默的说声“一路走好”!但愿这该死的经济危机快点过去,幸福生活又要来临(罗斯福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竞选总统的口号)。
想起1929年经济危机时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新政中提出的人民应享有的四大自由(日后国际法的基础):①人人有言论自由、②人人有信仰自由、③免于匮乏的自由、④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此之后,美国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美国人民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够真正的尊重国民,保护国民。而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国真的应该认真去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每个置身于这个体系的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今天,大量的失业以及由于失业带来的物质匮乏,心理恐慌正在不断的蔓延。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抨击资本主义体系之与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可是社会主义体系在危机之下似乎也很难独善其身,甚至乎更加不堪。网络上调侃的语言“那边厢农奴翻身做总统了,这边厢主人还猪狗不如”并不是无稽之谈,更像是黑色幽默。农业时代为了超英赶美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工业时代在危机面前以牺牲民工来化解和转嫁危机。
工厂倒闭了,民工最后的一条路,退回农村,至少还有一亩三分地。坊间流传这还不是最艰难的时候,明后两年情况将更加恶化。其实我不懂,但愿这是危言耸听。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喊产业升级,产业转型,可是到头来我们还是牢牢的占据产业链的最末端,制造大国,听起来似乎很美,在危机面前还是首当其冲,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总是撑不起一个民族品牌,世界品牌。大概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一种靠剥削廉价劳动力来获利的增长模式,习惯于任意践踏民工的企业是无法有创造力的,因为这样的企业本质上是粗鲁的;习惯于无视民工权益的地区是无法有竞争力的,因为这样的地区本质上是封闭的;……
的确,应该承认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制造业吸纳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最近一美国人出了一本书叫做《假设没有中国制造?》,在反思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东西越来越依赖,尽管很多美国人都会对中国制造的东西嗤之以鼻,但是在低廉的价格面前还是欲罢不能。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诟病中国制造的种种弊端,没有创造力,大量的环境污染,剥削劳动力等等。我也在想,假设没有中国制造的话,假设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的话,那么我们这么多的民工又该怎么办?他们的路在何方?
三年前的民工荒调研,结论是其实不管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缺的不是普通工人而是技术工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并不是经济危机才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失业,经济危机只是一种催化剂,让问题暴露的更加快,更加明显。于是我开始担心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将会导致更多的农民工失业,从情感上讲我宁愿不要这样的产业升级,可是这是历史的车轮,于是产业的升级转型与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似乎是一种悖论。
很明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是不现实的。首先,大规模的工业化并不能够全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转型已经精简了大量的民工;其次,中国9亿农民,世界上最庞大的群体,有3亿的剩余劳动力,这么庞大数量的农民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需要解决就业,而且需要考虑住房、教育、医疗等等问题。显然城镇化这样的思路是不现实的。个人以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基于农村本身,一定是要走城镇化和农村改革相结合的道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等内容。

该决定意味着“新土改”的启动,酝酿中的土地改革有望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甚至允许宅基地流转。一旦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集约经营便具备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浙江等沿海省市近几年的实践已显示,有偿转包、业主租赁、分季流转、土地入股、土地互换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
看到中央这样的思路,以及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真的很替中国的农民群体感到由衷的欣慰,的确我们难以去预测这样一种改革的结果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方向。就像时下的经济危机,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政府投多少个亿去救市,而是政府的措施是否能够挽回民众的信心,是否能够让民众看到渡过时艰的希望。当然有很多人对土地的自由流转表示担忧,担心由此产生土地的私有化、耕地流失,担心由此产生大量流民,担心农民不能真正的受惠。的确,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制度是一把双刃剑,新土改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农改的目的是要释放数十万亿的土地财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的重要支点。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法》将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来,人民公社把土地收归国有;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分田到户”合法化,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现行制度固然确保土地公有制、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积极性,却未能使农民与土地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亦为一些不法官商勾结、利用建设征地牟取暴利提供可乘之机。
30年前,由小岗村引发的全国土地改革同样有很多怀疑的声音,有很多善意的担忧,今天我们看到了改革是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我们收获了更多,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城乡生活品质提升、经济高速增长、民主文明进步……但时过3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乃至改革全局的推进力已基本释放完毕,一些弊端却日渐凸现。
今天,“新土改”的启动依然伴随着怀疑、担忧,这些都提醒我们改革要谨慎,要系统的考虑。我们深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停止前进的脚步。我真的希望30年后,我们会由衷的说声,我们的改革是对的。真的希望我们的民工不需要每年都像候鸟一样经历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真的希望新的土地改革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不需要外出打工,真正的富裕起来。真的希望“民工”这样的“职业”或是“身份”从此消失,借由产业升级使部分有技术有能力的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借由新土改使不具备成为产业工人的民工以及绝大部分还在农村务农的农民真正的安居乐业,做新时代的中国农民。
在赛立信工作两年的我,有幸借由工作接触了大量的珠三角企业,从只有十几个民工的小作坊式的私营企业到拥有成千上万民工的外资企业,而我也因为身份的不同得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民工,看待民工的问题。以前作为社会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习惯性把民工视为弱势群体;今天当我试图把民工视为一种职业,视为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尽管时间跨越了好几年,尽管我换了一个角度,但是民工的困境依旧是困境,外出务工依然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一段人生经历,而不是出路。毫无疑问,经济危机是一场灾难,但是也是一次契机,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通过“新土改”,民工能够走出困境,寻找到出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