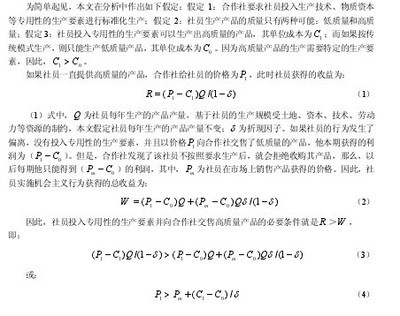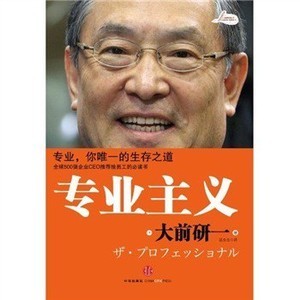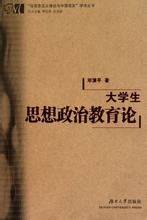我非常支持农夫山泉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来打这场官司。首先要注意法律上的要点。民事诉讼的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不存在因言获罪、进监狱等严重后果。所以,对于不负责任的言论,以民事诽谤诉讼的途径来加以解决是最好的方式。而不要动辄以刑事诽谤、诬告、侮辱以及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42条、第25条的罪名和事由来抓人。 权利、责任是法治社会下的概念,没有法治只讲责任、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宫”。先自由后自律,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没有自由谈责任是先天缺失的。 我觉得要澄清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关于知情权。知情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知情权只涉及政府、公权力,不涉及企业。商品的知情权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5月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针对政府的。所以,可以说知情权在法律上和企业没有关系,这个必须清楚。 而与知情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采访权。“记者特权论”概念下的记者,认为采访权是天经地义的,我要采访你,你就必须接受采访,这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第一,中国记者的采访权不是由人大通过的正式法律承认的权利;第二,企业可不可以拒绝采访?即便是涉及公共利益,从国外案例来看,企业也没有法定义务接受采访。但政府无权拒绝采访,因为这有法律保障。再如舆论监督权,也不是一种法定权利。 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销售额巨高。一篇负面报道,无论准确与否,都会造成企业的受损。如果没有事实依据就发帖说农夫山泉不能喝,就要负法律责任。这种帖子一旦被大家转发,就一定会造成影响。对照美国的法律,如果你针对一般个人、非营利组织的诽谤,索赔金额不会很高。但如果你针对公司老板或者大公司诽谤,那索赔金额可能就会达到多少个亿。举个例子,《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商业组的主编写了一本书《特朗普国:成为唐纳德的艺术》,书中提到大亨特朗普自吹个人资产,夸张数十倍。2009年特朗普起诉编辑个人,索赔金额是50亿美元。 2006年富士康向《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法人以及它的一个编辑、一个记者索赔3000万。提出多少索赔金额是企业的权利,相关的诉讼费可能还会更高,这是基于公司报道给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折合成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金额,但是对于常人就是个大数目。 因此媒体、记者在报道企业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倍加小心,任何一个事实上的差错,可能会导致天价的索赔。

我为什么期待诉讼呢?事件过程的相关事实信息尚未全部透明,通过法庭的调查质证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可靠的东西,就是证据。这种案件没什么好保密的,它会公开审理。我比较担心这个案子会像富士康案一样被法律以外的力量介入,被“和谐”了。富士康案就是前后有两个变化,索赔金额从3000万一下子降到了一块钱,后来双方就和解了。 《京华时报》原来是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两年前划归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最后我有点担心的就是北京方面和浙江方面出来协调,法律以外的因素起作用,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民事案件涉及到大公司的名誉权,就会比较复杂,复杂就在于采访相关证据的获得以及索赔金额。可能,我们现在还不习惯看到3000万、5000万、6000万的索赔,但以后这样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媒体要高度谨慎。王克勤说过,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两种力量逼出来的,一种力量就是官方以打击虚假新闻为名找你的茬。第二个力量就是法律,特别是诽谤法,诽谤法使媒体的不实、虚假报道大量减少,这是健康的。 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就像中国的社会一样,走向法治的轨道。如果脱离了法治的轨道,那就永远在一潭浑水里面乱搅。本来是法律的问题变成了其他问题,本来跟法律无关,最后可能变成一种以法律为名来惩罚你的一种方式。 而对于这个案件如何发展,今天我担心它最后被“和谐”。如此一来,意义就有限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