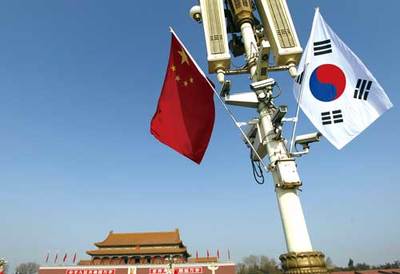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思想被认为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活动。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思考——哲学是思考真理的科学。
思想不仅仅是思想家纯粹的自娱自乐。可以相信,思想有力量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思想并不因为有用才有价值,思想本身就有价值。起码,思想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获得作为人的尊严。约翰.穆勒所说的——“做一个感到不满意的人要比做一头感到满意的猪更好;做不满意的苏格拉底要比做满意的傻瓜更好”[i]——似乎表明了人通过思想才超越了动物性,确立了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身体是灵魂的寓所,所以,关照肉体即物质生活是必须的。但是,物质性显然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尊严不是来自其粗壮的臂膀,矫健的步伐或尖利的牙齿,而是来自其超越肉体的精神,超越现实的理想。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火,而是思想及作为思想成果的尊严和正义。但是,在一个现实的、人的欲望不断成长的世界里,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持久的紧张。在欲望的推动下,在人和猪之间,在苏格拉底和傻瓜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疆界。屈从于欲望,成为物质的奴隶,可能使人离苏格拉底更远,离傻瓜更近;离人更远,离猪更近。
苏格拉底看到了这种危险。面对雅典弄虚作假、奢侈腐化的日下世风,他立志成为一只牛虻,通过持续的叮咬,使雅典人保持警惕,保持人的尊严;通过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在思想混乱之际唤醒人们对真理和至善的信心。成为一个真理的看护人,苏格拉底要求自己保持对世俗生活的疏离,保持对物质欲望的拒绝,体现一个哲学家特有的骄傲。“一辈子忙忙碌碌,无意于多数人所关注的事情,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城邦里喧腾的各种热门活动,诸如宦海浮沉,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等等,一概不闻不问。”[ii]苏格拉底的骄傲基于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信念——“以独立证实其自由,以孤独证实其独立,蔑视理性之外的一切权威”。[iii]
苏格拉底的骄傲、独立、自由、超越、公共意识和终极关怀,就是柏拉图为人类塑造的知识分子人格。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保持对物质的疏离,追求超越世俗的成功,关注真理、正义和和终极价值;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保持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与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的规则和限制保持持续的紧张和怀疑;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保持批评的能力,成为真理的卫士和社会的良心;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成为刘易斯.科塞所说的那一类人——“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iv]。
二、市场进入、思想退出
生活而不是被生活,体现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卓越的超越和勇气。但是,困扰于物质和欲望的人是否真正具有超越的力量?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特质在于过一种超越的生活,如果说物质不仅是灵魂的寓所也是精神的基础,那么,对物质的超越只是一个乌托邦。但是,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实际上并不要求灵魂对肉体的彻底摒弃而成为飘浮于空中的风云。精神的优越性在于其相对于物质的自主性。就像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物质幸福并非不值得,但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从物质中获得满足。物质幸福的条件不过是物质供给能力和物质需求的平衡,而平衡可以通过控制需求实现。物质与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欲望——这赋予幸福极大的弹性。可是,人的欲望是成长的。所以,格老孔[v]不满足于成为“猪的城邦”一员。柏拉图当然知道,自然意味着永恒,意味着永恒的幸福,所以他希望借助于理想国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的水平。但是他很无奈的看到,随着雅典的强盛,随着物质的丰裕,人的贪欲以更快的速度在成长。终究,自然的城邦会发展为“发烧的城邦”。城邦的发展隐喻着人的欲望的成长,当然,欲望的成长也在推动着满足欲望的能力的成长。
在古代世界,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的匮乏,人们被迫通过控制物质欲望实现物质需求与物质供给的平衡,从而使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重要性,使思想及作为思想的生产者和捍卫者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获取物质产品能力的增强,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的成长进一步推动物质欲望的扩张,在物质与精神的对决中,物质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与现代化相伴的理性化的发展,进一步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合理性的标准,理想和信仰逐步退出人们的意识空间。于是,思想的地位下降了,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丧失了。促使思想降格和知识分子退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市场化过程中,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标准和核心的动力。通过实用主义的过滤器,市场所能容纳的只是符合市场标准的有价值的东西,而所谓价值,不过是有用,不过是人们物质欲望的满足。在这里,思想是有意义的,——在乌托邦的意义上有意义,——但没有价值。思想被放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消失了。市场化使思想和知识分子失去了市场,知识分子发现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也很难找到听众。
市场进入了,思想退出了。市场成为现代世界的独裁者。市场以货币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并以此决定一切要素的进入或退出。一切不能体现和实现货币价值的东西被拒之门外。知识分子要立足于世界,只能与市场结盟。知识分子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他们试图保持与商业世界一定的疏离,以维持自己的骄傲、独立、自由、超越、公共意识和终极关怀。在苏格拉底看来,“不管卖的是什么,人其实都已经置身于依赖购买者的境地。要有人付钱,就得为之服务,为之服务就得取悦人。……为了几个钱,有多少个客人就扮演多少种角色,掩盖自己的想法,每次还要装出一种自己未曾有的真诚,这是多么可耻啊!不只是哲学家,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不能同意这种唯利是图的态度或言语。只有奴化的灵魂才能够让他的言语与这样的环境相适应,并用他的思想或者才干服务于雇主的利益。”[vi]但是,当市场成为思想进步及知识分子行使其传统职能的釜底抽薪的力量,知识分子被迫屈服了。市场冲击迫使知识分子从思想阵地撤退,通过介入市场获得安身立命之所。知识分子不再试图劝导人们超越物质,因为他们本身成为物质的俘虏;知识分子不再承担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批评的力量;知识分子不再关心终极价值,因为现在他们只能关心现实。
三、进入庸人时代
市场进入了,思想退出了。除了物质,我们不再关心什么;除了金钱,我们不再追求什么。只有物质利益具有永恒的意义,思想和信仰成为虚妄。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庸人[vii]时代。
市场是一个追求等价交换的世界。当思想被拒斥后,知识分子需要提供一种新的要素以获得收入,这就是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是以思想影响世界,而是以知识进入世界。现代世界成为庸人世界的标志就是知识与商业的媾和而成为一门获取物质利益,实现物质成功的职业。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职能消失了。介入商业世界需要知识分子彻底放弃其固有的清高,放弃其对终极价值和普遍真理的追求,意味着知识分子只有提供能够经受市场检验并被市场接受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获得生存的手段,于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承担着批判现实世界的功能,保持对物质的疏离;而市场化迫使知识分子介入并接受市场标准,通过提供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知识获得收入,于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贩子。以往,作为真理的维护者,知识分子承担检验和校正市场的职能;市场化背景下,职业化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市场的检验,成为市场的同谋甚至奴隶。屈服于市场化背景下的生存压力,知识分子同时失去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能力,被迫接受权威机构的审查以取得进入市场的资格。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彻底丧失。
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的丧失还体现在其公共精神的衰没上。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个体性扩张而公共性萎缩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私人空间的扩展而公共空间的消失。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能之一是通过公共空间引导社会舆论,弘扬公共精神。公共空间的收缩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发挥其传统职能的场所,被迫龟缩到私人空间,经营具有生物必然性的私人利益。当然,知识分子公共性丧失的关键仍然在于个体化和世俗化对人们公共精神的消解。正如福柯所说,既然没有真正普适的真理,知识分子也就无法从事传递普适真理的工作。公共精神衰没的结果,不仅是理想和信仰的隐退,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失去批判力量,其健康发展必然成为一个问题。
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加剧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需要剔出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割裂其与真理的联系,需要赋予其一种肤浅、平庸的特性,使其成为可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商品。在商品世界里,受到重视的不是知识的内容,而是其用途,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知识的世俗化使整个世界在精神意义上呈现出平面的特点,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地位降低了。现代化背景下,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让位给了一个更务实、更讲求实效的人,其工作不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屈从于世俗生活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的特点,对公共事务毫不在意,所关心只是个人利益;为了物质利益的实现和社会地位的升迁,独立、自由可以成为交易的砝码;不再有理想,也不需要信念,金钱具有征服世界的力量。曾经的精英成为实实在在的庸人。
四、是否需要有人站在岸上?
市场化和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商品经济的物欲洪流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传统的观念都被荡涤得干干净净。理性化清理了整个世界,物质取得了对精神的最终胜利。
如果我们承认市场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进步,那么传统知识的降格及知识分子职能的变迁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施蒂格勒对知识分子对待市场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正是市场的发展,正是市场所张扬的盈利动机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为不生产的知识分子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知识分子蔑视利润动机,反对市场暴力不仅是虚伪,简直是忘恩负义。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人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存在不仅需要个体的价值,更需要社会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一个社会的健康成长需要某种持续的引导力量和批判精神。那么,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即使整个世界都卷入了商品洪流中,仍然需要某些人站在岸上。
引导社会思想,提高民众文化,提供社会批评,倡导终极价值,探索普遍真理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没有权力成为庸人。
附:本文以《进入“庸人时代”的知识分子》刊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6辑,总第23辑
[i]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21
[ii] 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44
[iii]尼古拉.格里马尔迪:《巫师苏格拉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17
[iv] 转引自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29
[v] 格老孔,柏拉图的同父异母兄弟
[vi]尼古拉.格里马尔迪:《巫师苏格拉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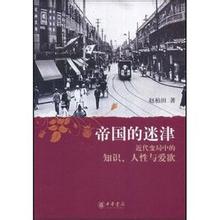
[vii]庸人(philistine):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P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