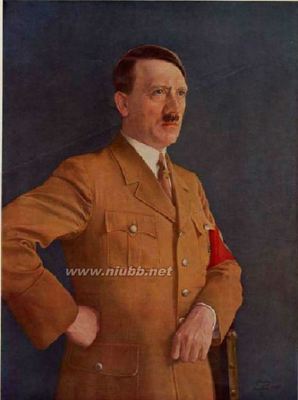“公地悲剧”是经济学历史上一个真正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当然不在于其背景和情节,而在于其揭示的经济学原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人们对同这一故事引发的经济学思考可以形成完全对立的观点,以至这个故事本身既是悲剧也可以理解为喜剧。
一、主流经济学:产权和效率
1968年,哈丁发表了著名论文《公地的悲剧》。在一个公共牧场上,每户人家都尽量增加放牧的数量以获得收益。羊群的扩大增加了私人收益,但羊群对草场的破坏则由全村人共同承担,这就是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牧场退化直至毁灭。哈丁的“公地悲剧”是一个羊吃草并把草吃光的悲剧。羊吃草本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就象人要吃饭一样。问题是在一块有限的公地上,羊的数量太多以至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而羊太多实际上是因为人太多的缘故。所以,悲剧的祸首不在于羊而在于人,在于人口的增加。但是,对人口增长进行谴责可能招致马尔萨斯式的难堪和失败,于是,哈丁将祸首裁定为“公有产权”——由于产权的公有才使草场失去了保护;于是,“公有”作为效率的对立物受到了谴责——“公有产权”成为人口增加的替罪羊。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在于其发展出一系列有效的制度。这些有效制度,如专利制度、私人财产制度等等,由于界定了个人对财产的权能和利益边界,有效克服了外部性,使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从而对个人的生产性努力提供了激励。至于土地私有权的产生,即公共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在诺斯看来,是在人口增长从而土地相对价格提高背景下实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制度选择。在诺斯的故事里,公地向私地的转化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在诺斯的观念里,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相对价格变化并引起人们利益结构变化时,制度的变迁就会自然发生。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演变,不过是市场自发演进的结果。诺斯的故事有喜剧的色彩。由于排他性产权的建立,转化为私有的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因为产权边界确立后,外部性消失了。于是,原来具有正的外部性从而供给小于社会合意需求的产品供给增加了,原来具有负的外部性从而供给大于社会合意需求的产品的供给减少了。公有产权转变为私有产权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喜剧,一个私有产权的喜剧。
哈丁的悲剧和诺斯的喜剧事实上有着相同的涵义。哈丁的悲剧隐喻着公有产权的失败,而诺斯的喜剧则在张扬着私有产权的成功。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里,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能够自发实现资源有效率的配置,因此,批判公有产权和颂扬私有产权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
二、古典经济学:雇佣与人的非人化
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富人的富裕依赖于穷人的贫穷的制度——的基础。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的积累——财富的积累以贫困的积累为前提。如果劳动者能够自给自足,雇佣劳动力就无法产生。因此,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首先需要割断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之间的脐带。
劳动者的顽固是早期资本家最头疼的事情。他们安于粗陋的食物,褴褛的衣服和透风的住房。只要基本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在阳光下散步和在火塘边打盹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远远高于在大棒威胁下在流水线强制下每个小时都能挣到的工资。公地的存在,为农民维持其“惰性”提供了保障。即使公地能够为农民提供的生活资源非常贫乏——一点柴禾,一些蘑菇,一些野味,一些草药——但对于安于贫穷生活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已经构成其生活的重要内容。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知道,农民之所以还梗着脖子拒绝成为雇佣劳动者,只是因为贫穷的锁链还不够紧。尽管自由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难以经受极端贫困的考验,因为,生命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因此,使劳动者自愿加入雇佣行列的有效措施,就是将贫穷的锁链拉得更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伦敦一位警察局长说:“贫困是社会中的一个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缺少了它,国家和社区就不能以一种文明的状态存在。这就是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没有了贫困,就不会有劳动力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不会有文雅,不会有舒适,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就不会有利益。”[1]圈地,消灭公地,也就是断绝农民生活的最后的公共资源。失去最后的依托,农民不得不乖乖就范,于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巨大障碍消除了。
失去自由,雇佣工人不再是完整的人。原始积累不仅要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脐带,也要割断人们与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脐带。因为传统脐带的存在,影响现代理性的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需要将一切都纳入暴虐的市场理性统治之下。这样,圈地运动在割断工人与其生产资料的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工人的社会联系,扼杀了人的合作精神,从而完成了使人成为非人的过程。乔安.瑟斯克在《圈地和独占》中说:“公共土地和牧场,在社区维持了一种向上的合作精神。圈地运动扼杀了这种合作精神。……圈地运动以后,当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一块地围起篱笆,并警告他的邻居离开,与邻居公平分享东西的原则就松懈下来,同时每个家庭都变成一个孤岛。……在这个由圈地运动和变化了的农夫所传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衡量出我们失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意义。”[2]
根据西塞罗,人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人类生活空间因此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财产因此分为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私人财产应用于私人领域以实现效率,公共财产应用于公共领域以体现公平。“公地”,作为一种公共财产或者公共活动领域,使人类基于传统价值的合作得以展开。这种传统价值——在协作生产和协同生活中实现人的社会性——使人成其为自然的真正的人——使人能够在社会存在中实现个体存在。圈地是一个现代理性取代传统理性并成为主导的过程。公共资源的消失,使依托于公地的传统价值失去存在的基础,劳苦大众被挟裹进市场的洪流,抓住金钱的稻草逃命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过于沉重也过于奢侈的传统价值只能被遗留在彼岸。于是,圈地完成了人到非人的转化过程。
通过圈地运动,公地的消失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纽带的断裂,雇佣劳动队伍建立了,劳动者的非人化过程完成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胜利,一场值得狂欢的胜利,一出历史上最激奋人心的喜剧。对于劳动阶级来说,这场胜利有着完全相反的意义。据说,圈地运动使他们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据说,他们分享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长,但他们知道,作为雇佣工人,成为他们财富的工资不过是供资本家进一步剥削自己的手段;据说,自由市场的存在为他们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们发展为完整的人的条件更加成熟了,但他们知道,市场体制给他们提供的只是一条成为雇佣劳动者的单行道,成为一个完整的充分发展的人的道路早已经被堵死。
三、悲剧还是喜剧
悲剧和喜剧的判断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事实本身,而仅仅取决于判断者的意识形态。
哈丁所谓的悲剧,将“公有产权”的存在看成是人类不幸的来源,因为它损害着效率的提高。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化,则实现了悲剧向喜剧的转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似乎更关心没有生命的土地而不是失去尊严的人。羊吃草是一个悲剧,而羊吃人却成了一个喜剧。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伴随着圈地运动,由于人的自主性的丧失,由于人的社会性的隐退,劳动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空间,人在沦为为人的奴隶的同时沦为机器的奴隶。这不仅是劳动者的悲剧,最终,一个割裂的世界带来的整个人类的悲剧。

[1]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文版,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3
[2] 转引自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文版,裴达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P27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