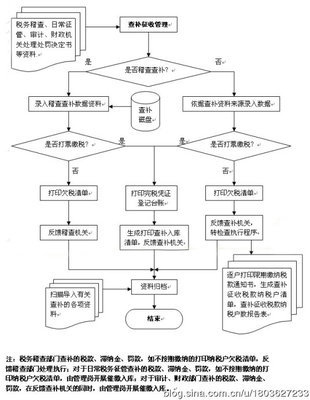本文所称“农地转非”是指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自然增值”是指土地农转非后价格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由于目前我国仅仅通过政府征收的形式将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从而,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合理分配问题,即政府合理补偿问题。不过,本文的基本精神对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也是适用的。而且,今后政府征地宜限制在“最狭义公益需要”的范围内。(1)
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完全按照非农地价格补偿失地者,便意味着遵循“涨价归私(农)”论(制);如果补偿金额虽然高于农地价格,但是大部分自然增值仍归政府所有,便意味遵循“涨价归公”论(制)。本文对于此二者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独创性地提出了“私公兼顾”论(制)——主张优先对于失地农民进行公平合理补偿,剩余部分收归中央政府所有,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并部分地兼顾城市建设。(2)
一、“涨价归私(农)”论与“涨价归公”论之争
方正楷体简体; mso-hansi-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size: 10.5pt">我国农地征收中“涨价归私(农)”论的提出
我国农地转非自然增值的合理分配问题,最初是从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提出的。当人们发现农民收入低、提高慢时,一些人士认定其基本原因之一是政府征收农地的补偿标准太低:“现行的补偿原则规定只是按被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进行补偿…….而与这块土地的未来用途和地价升值毫无关系。……这种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将农民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中土地级差收益的分配之外。”(3) “分享土地增值租金应该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方面,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转得很多,价格涨得很快,但是农民没份。”(4)有人估算,“25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格中转移和积累了9万多亿资产。”(5)据此,这些人士认为应当加以纠正——农地转非的自然增值,应当完全归农民所有。笔者将这种观点称之为“涨价归私(农)”论。顺便应当指出,论者往往以“农民”替换“失地农民”,这是以局部替代全局,是不合逻辑的。
“涨价归私(农)”制已是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存在的。其基本理论支撑是“土地非农开发权(6)补偿”论。此种理论认为,农民应当拥有完整的农地产权——除了拥有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项权利之外,还应当特别列出完整的“土地非农开发权”。这意味着,农地无论以何种方式转变为非农用地,原所有者都应当获得“土地非农开发权价格”即“非农地价格”,只有如此方能称得上“农民土地产权完整”。(7)换言之,农地转非之后的自然增值应当全部归失地农民所有,否则意味着对其进行剥夺或剥削。
“涨价归私(农)”论虽然由来已久,但它却是一种片面的理论;“涨价归公”论就是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
“涨价归公”论的由来及其理论支撑
“涨价归公”论是针对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遵循“涨价归私(农)”论(制)的事实而提出的一种变革性、创新性理论,其思想源远流长。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1806—1873)早就有所论述。美国经济学家H·乔治(1837—1897)则是其最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指出:“土地价值不表示生产的报酬,……它表示垄断的交换价值。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占有土地者个人创造的;而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因此,社会可以把它全部拿过来”。(8)但是,把这一思想归纳为“涨价归公”这四个汉字,却是孙中山">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对其“平均地权”思想进行阐述的产物,是指土地所有者报价之后地价上涨时,政府通过土地增值税将上涨部分收归国有。孙中山认为:“地价高涨,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9)“涨价归公”的理论也适用于土地征收。我国台湾济学家林英彦教授认为:“土地市价……包含庞大的自然增值额,这是应当属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如果按照市价补偿,那无异将自然增值部分也视为个人财产来予补偿,其不合理之情形至为明显。”(10)
“涨价归公”论在土地开发权上的理论支撑,客观上必然是“土地开发权国有”论。尽管H·乔治、孙中山等人没用使用“土地开发权”的字样,但是其理论的本质却与“土地开发权归公”或“土地开发权国有”并无二致。我国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一书中全面地论述了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必要性在于:保护耕地、避免流失,落实土地用途管理,保障农民的耕作权利;并认为非公益性用地,不仅要经过国家批准,向集体经济、农民支付补偿,而且还要“向国家购买发展权”。(11)
“涨价归公”论也是一种片面的理论;将连同“涨价归私(农)”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进行评论。
对于土地自然增值的辫析
无论人们对于土地自然增值的分配持何种态度,但是对其本身究竟如何,总是要搞清楚的。土地的自然增值是指,农地所有者、使用者以外的社会性投资(包括政府、公私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对于土地产生的辐射作用而使其增值。这种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及能源、通讯、环保设施及整个城市的综合性建设。它们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对于非农业部门和城市中的的各行各业以及其职工、居民等,却是作用巨大的。因此,当土地作为耕地时,这些非农建设对于地价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然而,农地一旦由农转非之后,便会接受非农建设的辐射作用,进而出现土地的巨大自然增值——辐射性增值。(12)
有学者认为“‘土地涨价归公’的经济学……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经济学认为,各种资源的市价是由其成本决定的。”(13)这是试图从经济学基础性理论上来彻底否定农地自然增值。然而这却是是对于“土地辐射性增值”这一提法的误读所致。实际上,“辐射论”的实质并非是这些用地以外的各项建设成果的价值转移到该地上面,否则,岂非意味着上述各项建设成果的减值或者是对其价值的重复计算?而这些当然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辐射”的实质是各种非农建设项目的功能,直接改善了新增非农建设用地的使用条件,即交通、供电、货源、客源等等方面的改善,使得用地户获得种种便利。从而,对这些土地的需求量增加,而土地的固定性则决定了位置优良的土地的有限性并造成其价格明显上扬。可见,所谓“辐射性增值”,归根到底是由靠近已有各项建设成果的位置所决定的土地稀缺性增值。所有这些,都属于级差地租与级差地价理论的范畴。而此类理论,整个经济学界都还探索得不够深透。
二、“私公兼顾”论与“全面开发权观”
“私公兼顾”论——私利与公利调和的产物
显然, 以上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既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都具难以成立的一面。
“涨价归农(私)”论的出发点是坚决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但它认定农民拥有取得全部农地自然增值收益权,即只看到失地农民应当享有农地开发权,而根本忽视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其他农民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显然失之于偏颇;尤其是,它根本无视农地转非并非失地农民本身努力的结果,而是由土地位置和政府土地利用规划所决定的。如果完全按照“涨价归农(私)”论进行农地自然增值的分配,则必然既不利于土地被征用可能性较大的城郊及其他交通发达地区农民安心务农,也不利于基本农田的在耕农民坚守岗位。实际上,农地自然增值的归属,应当与其产生的根源相联系,应当顾及社会各个相关方面的贡献与利益,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农(私)”论便是不能成立的。(14)
“涨价归公”论承认农地自然增值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涨价”并非由“成本”所决定。然而,它仅仅认为社会应当拥有整个农地开发权,而不顾失地农民也拥有获得充分补偿的天然权利,从而使其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是不可取的。我国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准则。如果不摈弃这种理论,而仅仅是增加失地农民的补偿,则意味着他们只是受到了额外的恩赐,而非理所应得,从产权上来看便不是名正言顺的。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公”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实例,可作为进行理论分析的佐证。
首先审视英国在“涨价归私(农)”制与“涨价归公”制之间的变换的实例。为了克服长期实行“涨价归私(农)”制之弊,依据“涨价归公”的理论,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1947年—1952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D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15)一分为二地看:“涨价归公”制如果不具有社会公平方面的理想魅力,便不会吸引人们大胆尝试;然而它的极端性却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节拍从而碰壁。其次,在我国,由于长期实际上遵循“涨价归公”准则,大约造成近半数的失地农民在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16)即已产生明显的不良后果。而且,这也是人们呼吁实行“涨价归私(农)”制的基本诱因。
综合而言,英国走过的道路无非是是在“涨价归私(农)——涨价归公——涨价归私(农)”中循环往复。如果我国今后由“涨价归公”制全面转变为“涨价归私(农)”制,便意味着重走1953年以后英国老路,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已。单纯的“涨价归私(农)”论、“涨价归公”论,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片面的、顾此失彼的。那么,出路何在呢?
笔者又参阅了美国实行的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s)的相关资料。它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土地开发权制度,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纽约州一些社区自发地实行,后来扩展到20个州,并在一些地方受到法律规范的支持。其要点是: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农地、林地、开阔地等等)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指标。这意味着,每一块土地都平等地拥有等量的土地开发权指标;如果因规划而使一些土地的实际开发受到限制,便应当由获得实际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给予补偿。在实行这一制度时,又将其土地开发权称之为“可转移的土地开发权”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17)有学者认为,实行这一制度,“保证各个所有权人,所在不同位置的各宗土地,彼此之发展机会均等及权益机会均等,不会有人特别受益,亦不会有人特别受损。”(18)
于是,笔者将“涨价归公”制、“涨价归私(农)”制以及“开发权转移制”三者的实质进行对比分析,提取了三者的合理内核,即“涨价归私(农)”制的“充分补偿失地者”、“涨价归公”制的“土地自然增值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开发权转移制”的“土地开发权益均等”。将此三者有机地综合为一体,笔者提出了“私公兼顾”论(制),其核心为:公平分配农地自然增值——在公平补偿失地者的前提下,将土地自然增值的剩余部分主要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并兼及城镇建设。
进一步从理论上来看,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强调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矛盾,防止顾此失彼;要坚持以人为本,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9)那么,调和矛盾、多方得益、和谐共富便应当是我国土地自然增值合理分配的基本准则,而“私公兼顾”论则是完全符合这一基本精神的。
在土地的市场交易中,政府适度征收土地增值税,在客观上也可不同程度地体现“私公兼顾”的精神。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所实行的土地增值税即是如此:土地涨价幅度小于100%部分之税率为40%,>100%而<200%者为50%,>200%部分为60%;若涨价幅度达到整3倍,则总平均税率为50%。(20)
“私公兼顾”论在产权理论上的升华——全面产权观
从产权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三种补偿制(论)调和的基础上还可抽象出崭新的理论观点——全面开发权观。这意味着,对于农地自然增值的合理分配,应当全面顾及失地农民、在耕农民和中央政府等三方面的土地开发权;也意味着每一个主体仅拥有有限的权利,各个主体不得越限侵权。
首先,整个的农地开发权可分解为两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农地开发权和政府的农地开发权。失地农民的农地开发权是指当农地转为非农地之后有获得“保障性补偿”的权利,即保障其获得相当于当地“小康市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权利。这是由于,仅仅按照现有的规定发给农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绝对不足以持久地保障失地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从而便意味着对于失地农民应得份额的夺。而且,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不应当与土地农转非之后的用途以及相应的非农地的价格挂钩,否则便会出现新的补偿不公。中央政府的农地开发权则是指拥有获得农地自然增值的其余部分的权利,即此部分应当收归社会所有。其根据在于,农地转非之后的自然增值,归根到底是产生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次,“在耕农民”(即仍然从事农业耕作、经营的农民)也同样拥有农地开发权而不可漠然视之。实际上,全国任何一块农地,都天然地拥有非农开发权,只是农地的用途、位置在客观上决定了它是否可能以及在何时实现其非农开发权(如基本农田是受到强制性保护的,不可任意开发为非农用地;位置偏远的农地被开发的机遇较低)。这样,就存在一个“已转非”农地与“未转非”农地所有者之间在开发权实现上的机会不公平的问题。(21)那么,对已经开发的农地自然增值中归公的部分进行再分配,便是顺理成章的。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保有“私利”,其所得归根到底既要用于支援全国“三农”建设(主要包括“对重点在耕农民的支持”和“一般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又要适度用于城镇建设;而后者的最终目的在于吸收失地农民就业。
总之,如果涨价全部归失地农民,意味着其土地开发权“过界”;反之,如果涨价全部归公,则意味着中央政府的土地开发权“过界”;进而,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其所获得的土地自然增值收入,还不仅要进一步通过多种形式公平地惠及各种在耕农民,以便保证他们的土地开发权在实质上得以逐步实现;而且还应适当地用于城镇建设。
三、贯彻公平分配土地自然增值的基本举措
对于失地农民的公平补偿
一般而言,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可分为“市场标准”和“政策标准”两大类。实行“涨价归私(农)”制,意味着遵循“市场标准”即按土地的市场价格补偿失地农民,而实行“涨价归公”制和“私公兼顾”制则意味着按“政策标准”补偿失地农民。(22)下面略述在实行“私公兼顾”论时,究竟如何确定补偿的“政策标准”。
首先是对土地原值的补偿。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具体体现为现有农村人口对于土地的“等额享有”制,从而失地者所拥有的农地产权就是其应摊得的那一份。那么,政府所付出的农地补偿,便表现为该份额农地的价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可从中分得相当于农民每年应交的农地承包费的资本化的部分。显然,前者是基本的而后者则是从属的。
其次,将土地原值的补偿加上“安置性补偿”而形成的补偿总额,才是对失地农民具有实际意义的。这一总额的“政策标准”,笔者认为应充分满足下列项目的要求:安家费(指被迫搬迁时)、转业费(指被迫脱离农业另谋出路时所需)、失业救济金(失地农民尚未重新就业时付给)、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学龄儿童教育保险费等。简言之,总补偿额应当能够使失地农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不只是保持在原来的水平,而是应当能够达到当地“小康市民”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公平合理的——他们对国家做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理应获得足够的回报。(23)此种“安置性补偿”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农地转非自然增值的扣除。而且,此种补偿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包干落实到底;各种保险都应当强制进行,以免落空。“只有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让农民切实得到实惠,才是对农民权利真正意义上的尊重。”(24)
此外,对于因征地而受损的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应当从恢复生产上予以补偿。简言之,对于失地者的“充分补偿”应当做到:农民无后顾之忧,集体经济纯收入不减。显然,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政策标准”较之“市场标准”更加公平:它不可能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崎高、崎低,而是可保障失地者的较高水平的基本需要。(25)从而,当开放农村土地市场而征收土地增值税时,亦可参照此种精神。
对在耕农民的支持及其他
“剩余归公”是指将农地自然增值减去失地农民补偿之后的剩余部分,收归国有。这一提法意味着并不事先限定“归公”的绝对数额或比重,而是强调要保证“充分补偿”,然后将其剩余部分归公。而且,“归公”意味着将其缴入国库作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于地方政府仅返还土地征收、开发成本),以便有效地遏止地方政府追求“以地生财”,避免诸多不良后果。(26)
对于归公的土地自然增值,主要应当用于“支援全国农村”——这一增值额缴入国库之后,应列入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全国农村建设,主要包括对于基本农田在耕农民予以适度补偿;扶植贫困群体;一般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27)对于重点基本农田的在耕农民,应当在补偿上有所倾斜——他们为了保障全国人民对基本农产品的需要而坚守于农地,牺牲了“农转非”而可能获得的机会利益。这样做,在实质上意味着对于这些在耕农民所拥有的非农开发权的一定程度的“购买性补偿”;只要陆陆续续、持之以恒地进行,即可最终实现对其非农开发权的完全购买。而且,对于贫困的在耕农民也应有所照顾,使其也能适当分享全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只有确实实现这最后一步,才算是完全体现了农地自然增值合理分配的“全面开发权”观。
有些学者虽然主张土地开发权国有,但是认为土地开发权“收益(价值)应大部分用于反哺‘三农’,以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城乡及区域间协调发展。”从而此种观点在实质上与“私公兼顾”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8)
对于过去因补偿不到位而在生产、生活上依然存在明显困难的那部分失地农民,应当尽快采取有效举措彻底扫除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适度地用于城镇建设,如前所述,其出发点归根到底还是要吸收失地农民进城。从而,对于投资项目的安排应当进行周全、妥善的考虑。
注:(1)参见周诚:《关于全面开放我国土地市场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8日。
(2)参见2006年2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刊载的周诚:《农地征收宜秉持“全面开发权”论》一文。
(3)蒋省三、刘守英:《海南模式: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15日。
(4)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地政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5)周天勇:《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10日。
(6) 英文的“ development rights”,其另译为“发展权”,笔者认为不妥。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一律使用“开发权”。因为,英文“development”一词,主要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惯例,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显然,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一词方为确切。
(7)见黄祖辉、汪辉:《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与土地发展权补偿》,《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另见注5周天勇文。
(8)亨利8226;乔治:《进步与贫困》,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7页。
(9)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载《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00页。
(10)林英彦著:《土地经济学通论》,(台)文笙书局,1999年版,第174—175页。
(1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387 页。
(12)参见周诚:《论土地增值及其政策取向》,《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13)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10月)。
(14)李元认为:“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归于被征地农民,那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和混乱。”(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2005年第5期《中国土地》。)
(15)苏志超:《比较土地政策》,(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17—522页。
(16)国家统计局2942户失地农民调查资料表明,人均纯收入增加者占43%、持平者占11%、下降者占46%(见《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第35页)。
(17)①T.J.Lawrence,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OHIO STATE UNIVERSITY,CDFS-1264-98。②Rick Pruetz,Putting Groth in its Place with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Planning Commissioners Journal 31#,1998。 ③NEW YORK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LAW ,New York Town Law§261-a。④苏志超:《比较土地政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24—527页。
(18)苏志超:《土地经济学术之开创与发展》,(台)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2000年版,第171页。
(19)杨长春、张明仓:《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人民日报》2006年7月19日。
(20)林英彦:《土地经济学通论》,(台)文笙书局,1999年版,第213-214页。
( 21)李明月、江华:《征地补偿标准的非公平性》,《国土资源》2005年第7期,第28页。
( 22)汪晖、黄祖辉:《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10月)。
(23)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对农民的“生存成本”的补偿(参见陈新锋:《从生存成本看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中国土地》,2005年第5期)。
(24)蒋媛媛:《征地补偿与失地农民保障问题》,《中国土地》2005第12期。
(25)李元认为:“单个农户,根本不可能垄断土地市场。如果政府也不能严格控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数量,土地势必贱卖,……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土地市场失控,农民直接卖地,一亩海边的土地,只有两三千元,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忘记。”(出处同注14)。
(26)毕继业等认为,中央政府应享有来源于社会的土地收益,不应当分成于地方政府,以便消除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不良动机及其所造成的损失(见《政府内部土地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中国土地科学》2003年第2期。)陶然、许志刚指出,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归地方政府作为预算外收入,“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牟利并寻租的情况。”(见《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27)邢思:《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2006年7月14日。
(28)张友安等:《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与流转》,《中国土地科学》2005年第5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