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开始做财经记者。这七年中国继续巨变,继续神话,也为人类社会种种既有经验与理论的检验,带来了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情感。
发生在企业上的事,也很有趣。本来,正常的管理并无新鲜事,伟大的公司静水潜流,让媒体找不到着笔的地方。但时代提供了一大堆新闻“富矿”,随时有公司与人被带到极端状态——
突然的大富大贵,突然的生死存亡,而且它们时常是近在咫尺。世界太浮躁,媒体往往会用“标题党”、大的噱头来刺激人们日益麻木的神经;媒体们也很功利,好企业往往会不断地获得美誉之辞,坏企业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不少报道与分析是概念先行,成败论英雄——成功的企业,可以寻找一百条理由来为它加冕;失败的企业,也可以寻找一百条理由来证伪。
回头看财经刊物的封面人物,真可谓命运无常,许多人风光一时,又黯然退场——传奇太多,反常更多。他们大多受益于中国特色,又受制于中国特色。这把双刃剑干掉了许多人。
看过这么多的大厦建起与坍塌,我已变得多疑,甚至是刻薄。对那些特别伟大、特别标新立异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警觉。有人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商业模式,设计精妙包治百病,利国利民造福人类,我就不由得警惕了,会用常识去倒逼真相。这个商业模式创造价值了吗?结果常是没有。
这种“伟大”的商业模式会有明暗两面,明面光鲜、富丽堂皇;暗面却是无关宏旨,只是在思考如何诱人入瓮,如何赚下家的钱。你会发现,明处丝丝入扣的逻辑,实际上却违反了许多常理,它只是注重价值的分配。没有做大蛋糕,只想在分蛋糕上做花样。
其实,媒体要传播新知,但呼唤常识的归位更加重要。
当下的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高估了自己的独特性,总以为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可以忽略普遍性的人类经验;二是许多人的反常识,用大的帽子去掩住下面的小。
如何识别常识与谬误,王小波这哥们其实说得很“常识”,“无法诉诸常识的文科知识,无法让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理解的文科理论,都是很虚伪的——有那么复杂吗?”
缺乏常识的中国
常识哪里去了?
常识的定义权历来是被争夺的。从标语能读懂中国,因为这就是输出常识的端口。在这里,标语上常是扭曲的常识。比如过去那个最让人胆寒的“一人超生,全家结扎”,现在也有“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得罪投资者是罪人”、“吃透精神早签约,世上没有后悔药,等到强拆梦方醒,流泪懊丧又跺脚”。这是魔幻与荒诞主义吗?
我们还制造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表述:保护性拆除、临时性强奸、激情式杀人、轻度型追尾、和谐式维稳、合约式宰客、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盈利性亏损、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休假式治疗……现实很荒谬,荒谬得那么真实,荒谬得那么合理。
反常识到处输出,最基本的常识却常被人遗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提出一个问题:“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当学生不考场作弊,当学者不抄袭剽窃,当包工头不偷工减料,当商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当官员不贪污腐败。”王缉思先生所言,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甚至是认知的底线,但以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王缉思先生的身份,还有毕业典礼这样的庄重场合,何以如此郑重其事地加以强调?这说明我们的不循常识已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反常识现象被人们习以为常,所以最底线的认知须得升格为规定,不言而喻的道理要三令五申——优秀司乘人员评选标准中有“不夹不甩乘客”,中小学教师职业守则中有“教师不得强奸女学生”,国家机关有“禁止工作人员公费到国外旅游”的规定,公安机关则专门要求“不能刑讯逼供疑犯”。
而在商业的领域,你也能看到许多类似情况。遇到许多看起来很美却很反常识的东西,心中时常有个蠢蠢欲动的小魔鬼,想用针去刺破那些绚丽的泡沫。
比如,电视广告上的牛奶广告,绿草如茵,奶牛肥硕,一家人被奶灌得傻傻的蛮幸福,看得你快忘了三聚氰胺,忘了这些企业刚刚犯过的错。还好,有财报会提醒你,国内三大上市乳业巨头伊利、蒙牛、光明年报显示,2011年三大乳企广告投入全年合计达到69.16亿元,一天就得砸出1900万元。当年蒙牛的利润是15.89亿元,但广告宣传支出却高达28.4亿元。心中的魔鬼弱弱地说,这哪是做乳业,哪里是在比牧场建设,比产品研发,功夫都用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上了。这样猛的推广,哪怕不是牛奶,是牛粪,估计也得热销。
比如,你又听到民生银行的行长洪崎在那里矫情地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心中的魔鬼又说话了,是不是有些东西没考虑进去呢?当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各家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国家财政注资的成本,保守估计也得1000亿美元。一般的企业,有这样的好事吗?
比如,宗庆后先生与达能打架,拉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可有个声音也弱弱地说,宗先生当时都有美国绿卡呢。而遵就科斯的说法,商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契约,商业行为要遵守这种契约精神。
企业家被异化
常识的反面就是被异化。
我感觉,中国的企业家很多被异化了。
我们的商业财经杂志、商学院的MBA教材,都回避了企业家最想知道的东西: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即使讲到了,也太过含蓄。
在中国,做小生意要对付城管;做大一点,要面对工商税务以及更多的形形色色的监管部门;继续做大,许多企业都须得与政府做下交易,与官员、与某一级政府捆绑到一起,从而获得安全与发展的空间。史玉柱就说过,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体系。上一个实体项目,要敲几十个公章,面对几千条“严禁”,几百条“处罚”。如果严格执法,实体企业家全要进监狱里。但是又不能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于是就出现了选择性执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幸存者,依赖政治、依赖政府、依赖政策,夹缝求生。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更像是官员,方法论是政府的、政治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而民营企业家,却如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教授史宗瀚所言,由于法律体制不完善以及出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动机,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进入体制内的意愿,让他们的商业及政治对手没那么容易使他们入狱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
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精力要去应对非商业的事情,这就是反常识的。所以冯仑也谈到,冒险、偏执、想象力甚至古怪的性格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可为何长不出苹果那样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的问题,而是中国企业家这种素质能不能“种出”苹果的问题。关键是需要一个充分竞争、鼓励创新、权益保障、法制完善的环境。
常态下的企业家应当做什么呢?回到常识,张迎维先生说出了企业家的本分:在市场经济里,市场整个的创造和进步实际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创新的过程。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判断政治风向,而是判断市场的风向,判断市场的未来。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他要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哪一个人判断未来的能力高,那个人的企业创造力就高。如果你判断正确,你的创新就创造价值,那你就可以赚钱。反过来说,如果未来判断错了,最后就要亏损,判断错误意味着你没有为别人创造价值。这是一个企业家基本的功能。
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反常识的。市场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家自由地创造。
反常识是怎么来的
何为常识?常识的英文是Common Sense,本意是针对某种常见现象人们达成的共识。所以,常识首先应该是大家认知的底线,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比如,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如果有一天你起来看不到太阳,也不必害怕,因为太阳依然在按着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被云雾遮住了。当然,常识会被注入价值判断,例如,现在我就可以斗胆说,自由比专制好,民主比极权好,法治比人治好,科学比愚昧好,上学比不上学好,吃饱比饿着好,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想来现在应该少有人来争辩了。
社会越复杂,越需要常识。因为越是常识,最简单的往往最深刻。我们需要一些基础性的东西,这是大家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一旦有人违反,大家也会引起警觉。比如司法制度,“依法办案”是常识,但有人说“依上级指示办案、依领导意见办案”才是常识,你就得警觉。
关于常识,王冉还说了“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因为大家的观念都很多,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但
总得有交集吧,那些交集多半就是常识。比如王冉就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法治、公民安全、新闻自由和市场公平就是国民福祉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真的很特别?
一些历史悠久与辉煌的民族,总认为自己很特别,许多在其他地方通用的常识会在他们身上失效。我们是这样,我们的邻居俄罗斯也是如此。
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是特殊的——不适合自由,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中国人也常有中国不适合民主的论调。他们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有这样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有过蜜月,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揪心的痛楚。
当前看起来也是这样。对待普京的连任,他们陷入了一种怪圈,对秩序重建充满渴望,期待铁腕的领导人,但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也会破坏秩序。这是俄罗斯人的困惑,让他们感到迷惘。
我们也一样,我们认为自己也很特殊。但也有那么多人站了出来,通过展现常识来奔走呼喊:跳出自己狭隘的认知吧,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黄亚生教授站了出来,写了一本《中国模式有多独特》,他告诉我们,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特殊,在别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遇到过,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别人的错误。
资中筠女士也很敢言,她到处演讲,告诉我们不能事事都往初级阶段上推。这只是我们用特殊性回避常识,回避问题的借口。
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到,讲常识的书也特别多,比如陈志武写了《金融的逻辑》,张维迎写了《市场的逻辑》,作家阿城也写了《常识与通识》,时评家梁文道写了《常识》,熊培云写了《重新发现社会》。这些书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常识。
有灿烂历史的中国,应该是常识的制造大国。过去,周边的邻国都需要到中国来学习常识。我们应该是最有生活常识的国度,比欧洲早很多年就会使用掘井技术,从而没有遭受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肆虐。中国人还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懂得农作物轮作技术,从而养育了更多的人口。
但是到了1978年,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群贫穷、愤怒、疲惫且面目模糊的人。这中间太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运动,使中国人与传统产生了深重的隔阂,对全球也不了解。众多来历不明的错误的观念与事实塞满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经历了一个痛苦、但很壮丽的苏醒过程,睁开眼看世界,慢慢重回世界。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回归经济学常识的历史,是我们利用国际市场,利用更大规模市场发展我们经济的历史。所以,不要想着我们多独特,而要想着,我们的常识普及还仅仅是开始。
权力抢夺常识
“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说政策;你跟他说政策,他跟你谈民意;你跟他谈民意,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
常识不是一个宁静的领域,它被书写,也被争夺。
总有人在反逻辑而行,不愿接受常识的约束。屁股决定脑袋,常识有时就因为屁股的位置而被异化,在利益面前分崩离析。有些人不是不懂得常识,他们身处常识中,但抢夺或压制了常识的解释权,于是就视常识为玩物或无物。其实常识的对立面非常强大,时常会以高深或高尚的名义包装自己,就像作家连岳说的那样,在现代文明社会,人开始脱离集合名词,以“我”的姿势出现。违背常识的目的,很多都在于让一个人交出他自己,奉献给他人。
常识是如何被遗弃与遮蔽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诽谤木”异化为“华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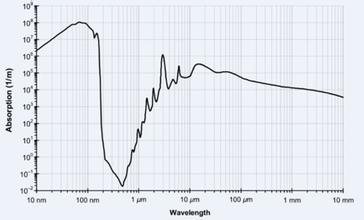
华表是什么,《辞海》是这样解释:“华表,亦称桓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桩。”华表的前身就是“诽谤木”,尧为了推行民主,就设了一根木桩,让臣民来提意见,言者无罪,有木桩为证。古时的“诽”字有批评否定之意,“谤”有勒令、要求、提醒之意,两个字链接起来,是警告、警示的意义。所以“诽谤木”也可称作“警示木”。“诽谤木”是体现尧民主政治的一个常识。
这规矩就立下了,代代相传。其实人都不太真心喜欢听意见,后来的君王就慢慢地改变木头的意思。随着时代的推移,木头变成了石柱,还蟠龙缠绕,竟成了历代帝王皇宫的装饰物和帝王尊严的标志物。原本对统治者的“警示”也就变成了“不得惊扰”——凡经此路段的人员车队等,文官下车,武官落轿,不得喧哗,不得无礼……至此,君主应该接受大臣与民众监督、批评的常识就被完全忘却,“不得惊扰”成为新的常识。而“诽谤”一词后来竟然演变为一种罪名。
所以,常识总是被争夺,被异化,又被重新发现,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陈志武先生认为:“常识”之所以会被异化,主要是因为权力的压力所致。这种“权力”可能是因为宗教,也可能是因为社会道德规范,但在当下的中国,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力,或者说因为国家的强制力。一旦社会的主要资源都掌握在权力手里,“常识”就会让步于权力,长此以往,就会让社会越来越违背“常识”做事。所以,面对权力,得保持警醒。而我们总需要一些人,从权力手中去抢夺常识。
释放常识的力量
常识的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磕磕碰碰,“行人们”进十退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过去,我们还有关于科普知识的十万个为什么。现在,我们还真应该出一个关于经济生活、关于民主生活的十万个什么。我们需要在每个领域,点点滴滴地普及常识,大家先学会做正常的事,说正常的话,做正常的人。正像股市的主人只能是股民、房子首先是用来住的、捐款是用来做慈善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商业模式是从实践总结出来的……回归常识,其实就是把你自己清零,从最简单的认知开始。我们在异化的路上走得太远,恰是因为我们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有时,我们喜欢那个傻傻的阿甘或者许三多,他们能够成功,其实是因为他们就认定寥寥几个自己能懂的简单常识,然后一直坚持。
常识总让我们想到一个牛人,那就是托马斯·潘恩,他那本叫《常识》的书,直接推动了世界头号强国的诞生。1776年,他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发表《常识》,它成为了北美人民明确的战斗纲领。
当时,这本只有50多页的小册子,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而当时北美殖民地也才二百五十万人口。
这本书让北美移民一下子明白了独立的意义,不再纠结自己的“叛乱”。潘恩告诉北美人民: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北美人民没有必要继续接受君主政权统治,解决英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美国独立。他说,美国独立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趋势”,要把“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国家留给后代”。
英国有家报纸评论道:“在一小时前还是一个坚决反对独立思想的人,读了潘恩的书之后,也瞬间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华盛顿也是看了潘恩的《常识》,抛弃了对英国的幻想投身革命。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必须和英国政权一刀两断。”
我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中国的“潘恩”,不要浩如烟海的著作,不要天花乱坠的演讲,只要简单平实的语言,让民众不再囿于种种偏见,逾越“从来如此”的智障。我们要唤醒每个人的力量,让每一个平凡的人能够摆脱被灌输和被催眠的命运,在常识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商人、官员、学者,每个人心里都埋有常识的种子,每个人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能力,且有美好道德行为的公民。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