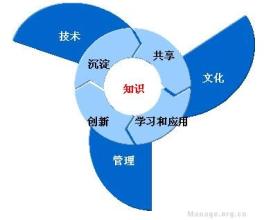所谓“中国式管理”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要创新中国管理,必须在管理学领域中走出“中国式”怪圈,不要瞎贴这些无畏的标签了。
关于中国管理的批判问题。我认为,导致中国管理学从上到下叫嚷“中国式管理”,不在于曾老先生等几个咨询师的倡导,也不完全是经济学家不懂管理,其实就是我在安索夫文章提到的,这是一个结构性落后。落后必然导致畸形的自卑感,就像阿Q怕人提起虱子一样,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人回敬别人说虱子时候的用语。假如说,中国管理确实引起世人称道,我们还在乎别人说我们是什么管理吗?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最有风度、强者最谦虚的。
理解中国管理一定要拓宽视野,要把中国管理放在一百多年开放学习的总体进程中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主线其实就是,逐步地由被动开放学习到今天的主动开放学习。在一个被动开放学习背景下,我们是处于自卑和劣势的,为了民族的自尊心问题,我们只会硬撑着说:谁说我们的管理落后了?你看看我们的周易和孙子兵法,再看看我们的道家权变!殊不知,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根本无法与现代管理对话。怎么对话呢?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立足的是一个专制集权背景下的农业经济,针对的问题是一个王族问题、家族问题,所有管理不是社会治理问题就是家庭治理问题,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驯化子民。就算是谋略,也是军事谋略、个体争斗谋略,总之,背后都离不开武力支持的。
现代管理是什么呢?立足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和信用是两大基点。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组织,是一个市场主体,它的社会边界就是供应商和顾客,企业的内部边界就是所有者和员工。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在这些明确的边界条件下,应用相关的资源,通过创造市场价值来满足自身的价值追求——还不仅仅是利润追求。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管理对象和问题,不仅仅是一些道德、人伦问题,还有非常具体的战略选择和定位问题、计划和控制问题、组织和协调问题、考核和测评问题,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那么,我就像问问曾老先生,这些工作是周易或者孙子兵法所能给予的吗?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凯洛格战略》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MBA教材,这本书的作者明确指出,许多在战略管理课堂上学到的战略概念还不足以使学生进行战略的定位和制定,所以需要研究一套工具和方法,该书就是这样一套程序和方法。连现代战略管理从市场中来、从无数企业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在进行方法传播供其它企业学习复制,都还需要工具和程序的设计,我们传统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就可以用来进行现代管理?荒唐之至!
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民族虚无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表明我的观点:管理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由理念与操作两个部分构成。就像其它的经验科学,如政治、法律一样,有它的法理、法哲学也有民法、商法或者其它法。我把管理学的这种学科构成性质称为“管理的艺术和技术”。很显然,中国式管理、中国式战略以及其它的中国式什么什么或者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关注艺术忽略技术问题,即对待中国文化背景上重艺术忽略技术、对待西方文化方面重技术忽略艺术,最为典型的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瞒你说,我从1987年在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参加“中西比较文化高级研讨班”开始,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西问题的比较思考,所有的问题症结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分离,不仅仅是管理学领域,其它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要打造中国未来的管理就必须彻底打破这种分离的局面。那么,艺术与技术是否可以结合呢?如何才能结合呢?其实,艺术层面人类都是一致或者相通的,不存在根本的对立。老兄不妨看看,不管是西方、欧洲或者美国,也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真主教还是佛教、道教,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不都是人如何达到真善美的工作生活境界、工作境界吗?这怎么会有根本冲突呢?如果说,有冲突那也是行为规范层面的理解不一致以及由这些不同的理解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利益集团的道德伦理规范。就像中国派到美国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一样,后来清政府把他们都召回,原因是他们去那里喝咖啡、跳舞、剪辫子。可是我要问了,这是文化冲突呢?还是意识形态冲突?很显然,这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嘛——清政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留学生”形象或者文化。既然艺术层面的管理不存在根本的文化冲突,那么技术层面呢?那就更加没有冲突了!这点不用我罗索了。
这种没有根本冲突特点,决定了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在艺术和技术完全可以可以互相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我认为,管理的艺术主要回答的是价值范畴问题:好不好?美不美?;管理的技术问题主要回答:对不对?成不成?有效无效?我们做事的原则一般都是先求成后求好的。这决定了中国管理学必然也要走这条路,先求成后求好。可以说,在管理学的研究层面上看,中国管理学经过20多年的开放学习已经走过求成的阶段,现在是要求好。从这样的趋势判断,中国目前流行中国式管理,说明中国管理学人在“求好”。这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管理学的研究者必须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在务虚,还而言之,我们是在务虚的层面上求好。这就需要注意避免两个不良的倾向:

第一,关注中国的管理艺术切莫忘记中国的管理技术。我们说,经过20多年的开放学习,我们经过了技术层面的开放学习阶段,不等于说我们技术层面的学习已经完全到位了。只能说,我们研究者不满足于学习的现状了。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强大,作为有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会满足于一辈子学习,从学生到老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还是管理实践层面的问题,都需要技术。而且,管理技术是管理的基础和存在的理由,没有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技术,那么就没有管理了。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可以解决管理问题了,管理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彼得.德鲁克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需要在这里讨论。实践层面我们还有大堆问题有待解决,迫切需要技术层面学习者不断努力。
第二,关注中国的管理技术。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智慧、管理理念或者管理艺术,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系统化、工具化、程序化和操作化。这才是最考功夫的事情。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丰田模式上面取得成功,除了有效引进全面质量管理之外,就是能够把大和文化充分转换成为可以计划、考评和控制的程序。一方面,达到技术成效,另一方面,不失人性。如果技术不失人性,那么它就不可能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这是根本的一条。我们在对待外国管理技术方面,除了责备“水土不服”之外,是在找不出外国管理技术有什么不是的地方。如果仅仅责备“水土不服”那是很正常的了。为什么?本身就不是针对中国人设计的管理理论怎么可能就服呢?这是任何一位管理学者都做不到的事情呀!如果是技术不适用,你可以研究开发或者改进出新的技术。譬如日本的田口质量管理,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改进。为什么我们的管理学研究者不去做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要跑去鼓噪“中国式管理”呢?如果人家一问: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我还不知道他们如何回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