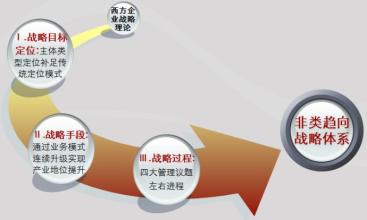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人是“注目礼人”,像“经济人”一样,“注目礼人”也可以用一个两点论概括: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即追求注目礼极高化。“注目礼人”是人的本色,“经济人”是人的殊态,一种特殊的“注目礼人”,是以“金钱竞赛”为游戏的社会形态或文明类型下的“注目礼人”,这种人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表象,底子里仍然是在注目礼上自利。
现在的问题是: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是必要的假设,还是也可以证明,抑或是像人性自利一样不证自明呢?人在注目礼上自利,没有哪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尊重和赞赏,这一点的确是每个人扪心自问就能够体识到的,可以说完全符合经验的事实。亦正如凡勃伦曾写到的,只有性格反常的人,才能长期地受人白眼而不影响到他的自尊心。18经济学之父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却证明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可用以证明的东西;证明不是自说自话,它必须依赖别的东西。那是不是就不证自明呢?非也,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没有任何自明感;前面也已经指出,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惟一不证自明的也就是人性自利:“我”就是“我”!别无选择,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能且只能作为必要的假设。
有意思的是,凡勃伦认为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这一点是来自人的本能,他把这种本能叫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名字——“作业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19我们不敢随便地假设像本能这样的奢侈品,宁可假设必须的假设,也不假设必须的本能。
不管是假设还是本能,人在注目礼上自利是人类社会形成的钥匙。即是说,要是人不是“注目礼人”,就不会有人类社会这么回事。或者说,没有注目礼这一把钥匙,就不能真正解开人类社会形成之谜。正因为人是“注目礼人”,在注目礼上自利,人与人才走到一块,进行形成团队,乃至社会。
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本是一个人类学的重大问题,需要进行详细的考证。但长期以来,对这一重大问题最流行的解释是:大自然是贫瘠的,甚至是险恶的,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有且只有团结在一起,就这样,人类社会形成了。
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状态说”就包含这样的解释,霍布斯是最先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人,有“政治学之父”之誉。在霍布斯的眼中,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20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人类必须订立社会契约,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用社会大生产来改造大自然,从而创造人间天国。
把霍布斯这一思想发扬光大的人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尽管休谟在总体上并不苟同“自然状态说”,更着力反对霍布斯由此而引发出的社会契约论。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形成是由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的区别带来的,与人类的内部矛盾无关。人类个体与动物相比,有三个不利的条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21
那怎么办呢?“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22正可谓“一个人是只猪,三个人是一条龙”,“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23
初一看,无论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还是休谟的“社会补救说”,都言之有理。但问题是在于:“自然状态说”是假设的,它假设大自然是贫瘠的,乃至险恶的;“社会补救说”也是假设的,不但假设了大自然的贫瘠和险恶,还进一步假设了人欲和人手的不对称,怨天尤人的,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24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与霍布斯、休谟大异其趣,提出了与“自然状态说”和“社会补救说”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果天然肥沃的大地照原始状态那样存在着,覆盖着大地的无边森林不曾受到任何刀斧的砍伐,那么,这样的大地到处都会供给各种动物以食物仓库和避难所。分散于各种动物之中的人们,观察了而且模拟了它们的技巧,因而逐渐具有了禽兽的本能。此外,人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各种禽兽只有它自己所固有的本能,人本身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固有的本能,但却能逐渐取得各种禽兽的本能,同样地,其他动物分别享受的种种食料大部分也可以作为人的食物,因此人比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更容易觅取食物。”25在卢梭笔下,大自然简直是洞天福地。
卢梭并进一步描绘了人最初在大自然中的生活:“我便可以看到人这种动物,并不如某些动物强壮,也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总起来说,他的构造却比一切动物都要完善。我看到他在橡树下饱餐,在随便遇到的一条河沟里饮水,在供给他食物的树下找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的需要便完全满足了。”26倒是与《旧约·创世记》暗合,完全是一派“伊甸园”风光。

孰对孰错呢?我们不是人类学家,似乎不应该在这里手起刀落。幸运的是,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没有被人类文明彻底“格式化”,偌小的地球村还多少有所保留。从被保留的自然状态来看,应该说卢梭是对的,霍布斯和休谟有点胡说八道。特别是按休谟的逻辑,地球上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似乎所有的动物都必须社会化才能得保小命,这与事实根本不符。如果真如休谟所说的那样,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即使诞生,也不可能保存,谈何社会!古人有句话叫“为赋新词强说愁”,休谟存在严重的“为创新说强说苦”的嫌疑。
尤其是,休谟强调所谓“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大可阙疑。从表面看,人类的确有无数的欲望和需要,“骑着毛驴思骏马,官封宰相望王侯”,可这无数的欲望和需要究竟是自然赋予的,还是注目礼“捣鬼作祟”的,抑或是别的什么因素造成的?诚如经济学之父和后来的制度经济学之父所共同指出的,人们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提供,额外的欲望都是注目礼“捣鬼作祟”的结果。
休谟所探讨的其实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成,而是已经在社会状态下的人为什么会一起合作。霍布斯也是这样,把社会状态当成了是自然状态。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不惜浓墨重彩来纠正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卢梭并不是抽象地反对霍布斯,他参考了许多欧洲旅行家游访美洲的记述。27
我们毫不隐瞒自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信念,那就是:天地既生人,天地自养人,这应该没什么疑问!人们肉体生活的必需品,大自然完全能够担当,人类用不着为吃喝住穿而社会化做社会人。要不然,大自然中那么多的动物特别是那么多比人的消耗要大得多的动物都怎么办呢?!凡勃伦倒是干脆,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学家们动不动就把所谓的“生存竞争”挂在嘴上,好像生存竞争真的就那么回事。28
——促成人类社会之兴起和形成的正是注目礼!因为注目礼不像吃喝住穿,大自然不能够提供,蚂蚁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老虎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向日葵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蜡烛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太阳不会向“我”注目致礼,万物都不会向“我”注目致礼,注目礼只能够来自于人,而人则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我”必须步入社会,做一个社会人。说白了就是,没有注目礼这玩意儿,人与人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即使一时因某事——比如说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困难——走到一块,也不可能长久呆在一块,就像一个人不会与蚂蚁或任何一种非人的东西真正长久交往一样。
卢梭当年事实上已经提出这一问题,只是提出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他问的不是人与人为什么会走到一块,而是问一个野蛮人为什么会依赖或是能奴役另一个野蛮人:天地广阔,物产丰富,你住山脚下,我住河岸边,你吃你的瓜,我吃我的果,你走你的路,我跳我的舞,作为自然人,这两个人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可他们为什么要走到一起,乃至于有可能一个依赖另一个,或是一个奴役另一个呢?卢梭提出了非常天才式的思考:
一些人使用暴力来统治另一些人,后者呻吟于前者为所欲为的奴役之下,这正是在我们之间我所观察到的情形;但是我不理解如何能据此推断野蛮人也是这样,因为甚至使他们了解什么是奴役和统治都颇有困难。一个人很可能夺取别人摘到的果实,打死的禽兽,或者侵占别人用作躲蔽风雨的洞穴;但他怎样能够作到强使别人服从他呢?在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从属关系的锁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有人要从一颗树上把我赶走,我可以离开这颗树到另一颗树上去;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有人搅扰我,谁会阻挡我到别处去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一个意外的声音会不会使他回一下头呢?我走进树林二十步远,我的束缚就解除了,他一生再也不会看见我了。这些细节,无须再加以赘述。每个人都会理解,奴役的关系,只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因此,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那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不受任何束缚,最强者的权力也不发生作用。29
卢梭明明白白地摆出了问题,但他没有旗帜鲜明地作出回答。但通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我们可以确凿地感觉到,卢梭的回答就是注目礼!他在书中曾写道:“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30
人是注目礼人,而注目礼是需要别人来提供的,就这样,野蛮人走到了一块,变成了社会人,进而也就使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成为可能。这也就像任何一场竞赛,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风光无限,为着这一点,每个参与者都不得不接受规范,付出辛劳,甚至有可能为这里的明争暗斗而耗掉一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