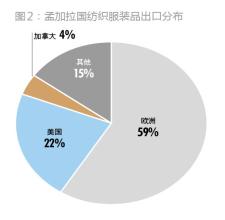“经济人”是什么人
“经济人”虽然是西方经济学最基础的一个设定,但它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并不是来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虽然有对“经济人”的精到描述,但的确找不到“经济人”这个说法。

据考证,真正作出“经济人”这一假设并进行界定的是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在1836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一文可以算作是“经济人”的最初出典。穆勒在这篇论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10
这似乎也谈不上是对“经济人”的严格定义,但穆勒这句话的确道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内涵,这就是一提起“经济人”就能够想到的:自利、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要对“经济人”进行严格的描述,我们认为一个两点论就行: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即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两点就写尽了“经济人”,一点也不能少,也用不着再多一点。比方讲,已经说经济人自利,就不必再说经济人理性,因为理性的含意完全可以被涵盖在自利的含意当中。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正如经济学之父在《道德情操论》中写到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1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人性自利是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惟一有的不证自明。
如果的确需要一个证明,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定有“我”,必须自利,而这与他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相矛盾。
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但这样一批人最后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都被生存竞争无情地淘汰了。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利。即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自利——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利自己,因为这样成本更低。
人是自利的,有人往往就以这一点来概括“经济人”,把自利等同于“经济人”。其实,这只是“经济人”的第一点,“经济人”真正区别于人的特质是在于第二点,这就是“经济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穆勒对“经济人”的定义其重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这样做,穆勒解释说,“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的公认目的就是获取财富”。12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泛滥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原因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皆成为“经济人”,不得不追求财富最大化。
人性自利不证自明,人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也不证自明呢?否!“经济人之父”穆勒在他那篇最初提出“经济人”的论文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13即是说,人在财富上自利只是一个假设,如此而已。
人为什么要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乃至大搞“商品拜物教”、甚至不惜为财利而赴汤蹈火呢?穆勒似乎并没有深思,反而把人在财富上自利当成是所谓“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作为一种社会表象,这似乎也并不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司马迁当年也是这样说的。
但事实上,追求财富最大化仅只是人自利的手段之一,经济学之父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14拥有更多的财富,就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就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最大化,“经济人”并不是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的。
《国富论》主要是经济学之父阐明经济发展的思想,目的是“富国裕民”。作为其前奏的《道德情操论》,斯密先生则主要是阐明其伦理道德思想,目的是“公民的幸福生活”。正因为此,《道德情操论》费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论证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动机不是在别的,而就是别人和社会的认可——我们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
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先生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15
不是为了生活必需,那是为着什么呢?斯密先生再一次直截了当地问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16原来是注目礼在这里面“捣鬼作祟”。
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遇上注目礼,自由也让道!斯密先生写道:“尽管这(即为注目礼而辛劳而奔波而操累——笔者注)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17对注目礼而言,自由算个什么鸟!
遗憾的是,经济学之父的这一些洞见和真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注意。或许是因为现实富国裕民的需要,人们更多地是盯住了《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但金子总是会闪光的,斯密先生所提出的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的思想后来还是被人发扬光大了,这就是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本德·凡勃伦。
在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非常系统地分析了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他所谓的“金钱竞赛”——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别人和社会的注目礼——他所谓的“歧视性对比”。不过,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凡勃伦的这部大作问世时已经是十九世纪最后一年,这是不是反映了西方思想界的迟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