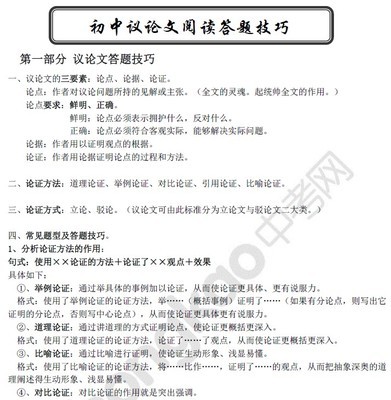引言:关于旧事重提等问题
2006年5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发表了杜业明先生的《关于农地征用补偿问题的再思考》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写到,这篇文章是对于我于2004年4月在《中国土地》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他在同年3月在《中国土地》杂志上发表的同我进行商榷的文章的简答,感到“依旧疑窦丛生”“不敢苟同”等等而写的。而杜先生2004年3月的文章,则是针对我在2003年3月25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是是非非》一文所进行的商榷。
旧事相隔两年而重提,当然并无不可。但是,时过境迁,事物变换,观点发展,如果依然在不同程度上针对原来的观点而进行商榷,就难免出现南辕北辙、文不对题的问题了;特别是,一般读者更容易感到“如坠五里雾中”了。从而,笔者便不得不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而从容应对。此外,请恕我直言,杜文在某些方面联想过过于广泛而间接,往往也使人难以针锋相对地一概予以具体回应。
在这里顺便要谈到,由于相关法规已经修改,而一些作者却置之不理,于是在行文中就出现了专业性用语明显不规范的问题。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作了修改,将原来的第二条第四款中的“征用”改为“征收或者征用”,
并将有关建设用地的条文中的“征用”改为“征收”。而有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包括郑振源、杜业明等专业人士在内的文章,却依然使用着修改前的概念,即把“征收”(涉及所有权易主)依然说成“征用”(仅涉及使用权转移),不能不令人遗憾。
关于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与农民土地补偿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到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和农民各自拥有的土地产权的性质、份额及其对国家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等问题。在论及杜文与拙文的分歧之前,有必要先将本人观点演变的过程,简约地陈述如下:
我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的观点主要是: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本质为‘共同共有制’,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拥有一份土地权利。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其成员所拥有的土地权却利与‘按份共有制’不同——前者的土地所有权是不能按份分割的而后者却是能够按份分割的。从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国家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自然是归作为农地的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计入公积金,而不应当平均分配给集体经济的全体成员或失去承包土地的农民。换言之,失地农民只能是获得安置补助费(参见《现阶段我国农地征用中的是是非非》,载2003年3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

在第二个阶段,我的主要观点是: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为“综合共有制”。这意味着,从所有权方面来看,属于“共同共有制”——全体成员对于土地共同享有所有权而不可分割;而从使用权方面来看,则又属于“按份共有制——每个农民平等地拥有一份承包地;而且,农民“拥有对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权——可出让、出租、赠送。”(参见2004年2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所载《健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思考》一文)。
第三阶段即2005年10月17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一文以后至今。该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的按份共有制,具体体现为社区人口的“等额享有“制。从而,当农民的承包地被国家征收时,国家所付出的土地本身的补偿,便体现为按照农民所拥有的那份承包地的价格所进行的一次性补偿。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失地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金中,分得相当于农民每年应交的土地承包费的资本化的部分,也是顺理成章的。”按照这一观点,则失地农民所获得的整个土地补偿费的份额,便自然而然地占绝大部分,而集体经济所获得的,便只能是极少部分。
我的第三阶段的认识,不管在理论依据、求证路径等方面是否与杜文具有根本性分歧,但其结论却与杜文不谋而合。然而,严重的问题在于,杜文只是紧紧抓住我的第一阶段的观点不放而进行反复不断地批评,而根本不提我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观点,其道理何在?如果说是视而不见,未免武断而不公;但是至少可以说是缺乏调研,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形成无的放矢。即使如此,也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此外,对此不得不加以补充的是: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给被安置人员个人”(见《中国国土资源年年鉴》【1999】,第539页)。我的第一阶段的观点,正是以这一政策规定为素材的;尽管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然而却并非笔者闭门造车的产物。
关于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及土地市场问题
有关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及土地市场等问题,笔者将杜文的陈述性观点去粗取精、高度归纳为如下四点:①将农村土地开发权直接赋予农民,以便从根本上避免寻租行为的发生;②让农民在土地市场上进行公平交易以便保障其土地权益;③通过税收调节国家与农民的利益,更加规范、避免暗箱操作;④政府部门、官员不介入土地市场,以免滋生“分利”行为(这四点系笔者姑妄言之,读者务必以原文为准)。杜文关于“分利集团”问题的论述的核心思想,也可溶入以上四点之中。
作为对照,下面将笔者在2004年3月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题为《关于全面开放我国土地市场问题》的文章归纳为如下六点:①国家通过征地、国有土地经营公司通过收购,可把集体所有土地变为国有;由国有土地经营公司取代政府进行土地所有权垄断经营;②一级市场的土地使用权,可进一步通过抵押、转租等等形式,进入土地二级市场。③农村集体经济可向土地市场提供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与国有土地批租相仿,也包括入股分红制等)和短期使用权;农民可向土地市场提供承包期以内的土地使用权。④为扩大市场交易范围,把国家征地严格控制在“最狭义公益需要”的范围内。⑤强化土地市场开放度,既意味着更充分地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也意味着“有形之手”的作用也要相应地加强,以便完善市场秩序,抑制土地投机等等。⑥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形式将部分土地自然增值收归国有。
通过以上对比,除了国有土地公司进行土地所有权垄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也要强化“有形之手”的作用这两条以外,看来双方的分歧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
其 他
除了探讨理论问题本身之外,笔者利用这一机会顺便谈谈学术讨轮中涉及的“文弊”和文风问题。
例如,下面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周诚先生主张只有在‘最狭义公共利益’条件下,国家才能行使土地征用权;那么将农用地转变为经营性、营利性建设用地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确保,‘涨价归公’呢?笔者认为,只能将农村土地发展权赋予农民,同时对土地发展权收益征税。”(原文如此,一字未改)如果说,这段话是杜文针对我的观点而进行的分析,那么,我已放弃了“涨价归公”论而改为主张“私公兼顾”论;而且,我早已提到了增值税问题(我在《关于全面开放我国土地市场问题》一文中说过:“首先应当考虑对于集体经济和农民的合理补偿,其剩余部分则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形式收归国有”。)如果说,上面所引的杜先生的话是完全是作者陈述自己主张的,那怎么会以“确保‘涨价归公’”为目标呢?这类词不达意的陈述,越少越好。
近年来,在农地征收补偿问题的讨论中,笔者对于某些人不以平等待人,已经有所领教。最轻的算是被奉送一句“不敢苟同”了。此语看起来似乎轻描淡写,但按习惯极少用于朋友之间的平等探讨,因为一个极具贬义的“苟”字,便使自己与讨论对手拉开了距离!其他如“闭门造车”“振振有词”“胡言乱语”“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等等,就更是不说自明了!笔者认为,在学术论战的文章中,应当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文风,避免使用贬低性、刺激性语言,否则于理无补并显得自己缺乏风度。(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爱华网
爱华网